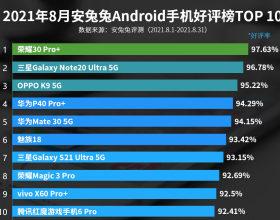這是我自己的故事。我和玉珍是再婚夫妻,我們的組合受到了很大的壓力。首先我子女極力反對,雖然我盡心盡力伺候了腦梗老伴八年半,到現在去世已三年,他們說我這把年紀再婚,是老不入調。而她前夫(已病故)的親屬也一致反對,她的兄弟也都不看好,認為去嫁一個大十歲的老頭子,那不是明擺著去做保姆。她是看重我的人品,我是欽佩她的過去,我是八十,她是七十,我們頂著壓力,堅決地走到了一起。
她僅靠一己之力,一個知青——從工廠裡走出來的媽媽,能把女兒培養成博士,其中的艱辛可想而知,也落下了一身病,我深深地知道她是累了,她是想找一個可以依靠的人,在他懷裡歇息。
在料理好她前夫喪事以後,女兒要把媽媽帶到自己的身邊去,她就是不肯去,篤信“滿堂親生子,不如床角癟老子”,到女兒身邊養老未必是好事。鑑於母親身體狀況,女兒一定要替她物色老伴,大概也是緣分吧,我與她是八竿子也打不到一起的,居然月老的紅線會纏到我的頭上。我們的相親很有趣,她來接我時,手裡還拿著保鮮袋,裡面裝了粽子和熟玉米。後來才知道,假如不成功的話,連飯都不要吃我的,是個勤儉正宗的女人。
經過幾天的聊天,到了這些年紀我們推心置腹談了很多,於是我們走到了一起。她家在常熟農村,是典型的農家模樣,四周
沒有鄰居,經常受到騷擾,迫切需要找一個可以託付的男人。聽她講了身世以後,知道她是一個性格倔強,勤勞能幹的人。從小就會體貼父母掙錢貼補家用,只要有機會,可以沒日沒夜去做。特別是自己開了小吃店,一直是清早忙到深半夜,連吃飯也顧不上,基本沒吃過一個正頓,熬出了嚴重的痔瘡,也不就醫,直到現在還留下一個大大的疤痕。女兒也沒有辜負媽媽的期望,除了媽媽的大力資助,自己也努力打工完成了博士學業。於是,我對她的敬意油然而生。我要用餘生來撫慰她身體的傷痛和心靈的創傷。
我們非常珍惜再婚生活。虧得我是一個回鄉青年,農村的活我都稍懂一點。於是她上灶,我燒火;她洗衣服我拎水,相互配合默契。凡是家裡的活,我都想方設法去做好,她這個人的愛好就是窮怕了,現在儘量節省每一個銅板,我也只能投其所好。記得當年的陳立夫曾說過:對待妻子儘可能包容一點,不必要分清是非,否則會傷心的。所以房客的分表,包括電錶和水錶都是我安裝的。牆面的漏風,水泥地面的修補也是我和她一起搞的。
她知道她的身體一直是亞健康狀態,體表多年來一直是冷的,且只會打嗝,不會放屁,也是多年的毛病。她就是諱疾忌醫,勸她進醫院,就會發火,大概對醫院負面新聞聽得太多了,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她媽媽受外婆影響對孩子們小毛小病總是用推拿來治療,她耳濡目染自己也會一點,所以只相信推拿。
別無他法,我就翻閱吳清忠的“人體使用手冊”,中裡巴人的“求人不如求己”,現炒現賣,臨床實驗,也許是心靈的相通,上蒼的眷顧,她的亞健康狀況大有好轉,體表不再冰涼,放屁有所出現。肌膚相親的愉悅,情感交流的歡笑,我們彷彿進入了人生第二個春天。
我們倆都是喪偶組成的家庭,對彼此的前夫前妻都可以毫不避諱講述他們之間各自的故事。她說前夫在她坐月子時周到伺候,晚年後,家裡家外重活輕活都是他大包大攬。我講前妻勤勞節儉,待人厚道,特別是對我弟弟知道他再婚後家庭包袱比較重,十分體諒。對來蘇讀書的兩個小的,小學和初中都在我家上學和生活,視如己出,親熱得很。我侄兒外出成家,也是她一手操辦。幾十年的夫妻總有割不斷的情感,我陪她到安息堂憑弔前夫,在我的家裡擺桌祭奠前夫;她也跟我一起上山掃墓,並在我前妻墓碑前,雙手合十祈禱。我們都非常尊重對方的情感。
歲月晴好,一起唱歌,我向她學打太極拳,一起在後山的林間小道漫步,我們沉浸在幸福中。人生苦短,誰知病魔已悄然降臨。她每天要出虛汗,服用中藥止住了虛汗,身體馬上出現浮腫,消化也不好,怕風。多次勸她進醫院,她就是不聽。當然進醫院,也不能一定能治好病,但至少能減少我心頭內疚的壓力。
她固執地和我一起翻閱中草藥,看到蒲公英和車前草能利尿消腫。我冒著炎炎烈日,騎著電瓶車四處尋找,這是等米下鍋,心中有多焦急!十多天下來,蒲公英,車前草也不見效。我們只能去我中醫朋友處就診。健康狀態每況愈下,女兒與她影片中看著母親病態的面容,帶著哭聲哀求媽媽馬上去醫院檢查,這才讓我陪她到醫院。大醫院人滿為患,超聲檢查等都要預約,只得打道回府。第二天到社群醫院進行超聲檢查和血樣分析,提示肝硬化,肝功能失常,腹內有不明原因的團塊。醫生建議要儘快做癌症確定。她又拒絕進一步治療。
疾病發展得異常迅速,大小便已不能自理,不斷有血便排出。還好,正好是大熱天,大小便可以直接用手來清理,然後再用熱水來清洗。有時睡著時,突然聽見放屁聲,睜眼一看,又是血便,立馬清洗,家裡僅有我和她兩人,我實在無法應付了,這才同意請她弟弟前來幫忙。去年七月三十一日,我和她弟弟把她送到社群醫院就診,醫生一看,建議我們立刻轉附二院治療。到達醫院門口,我第一次見識了這種場景,在這裡,根本沒有人性可言。我們就像趕進屠宰場的豬呼么喝六,隨意推搡。我從來沒有遭遇過如此境地,想死的念頭都有,為了老伴,我只能忍。從中午到晚間,總算進入了急診室。做了CT,直到深夜才拿到報告書,好心的女醫生對我說,多發性癌擴散,無法醫治了。我們在病房裡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八十多歲的我拖著傷痛的腿,忙前忙後辦理出院手續,在護工的幫助下,叫了救護車,直飛家中。
病來如山倒,病情的發展使你簡直無法擁有思考的餘地,和她弟弟商量決定到木瀆醫院去住院治療,在親戚的幫助下,總算順利地住進了腫瘤科病房。她弟弟白天來照看,我午後睡一下,其他都是我和護工負責,我主要是餵飯,喂藥,喂水,觀察好生命監護儀的變化。在彌留之時,她喊喝水,我含著淚喝了一大口水,然後一點一點地滴入她的口中,防止嗆入肺部。從八月五日中午到八月八日凌晨,老伴闔然長逝。
是八十多歲的我為七十多歲老伴前後左右的陪伴,為她送上了最後一程。我們相遇是一種緣分,我們只是想相互陪伴,一路扶持。再婚夫妻要且行且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