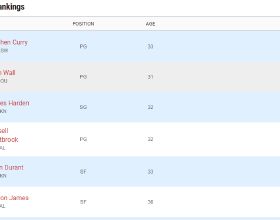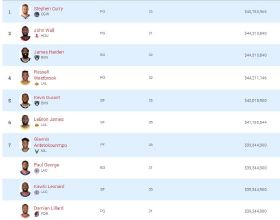一九三六年冬季,我們西路軍進入甘肅境內以後,成天遭遇馬家軍匪兵的襲擊。
我們是步兵,敵人是馬隊,武器裝備都比我們好,這樣,我們白天要阻擊敵人的襲擊,晚上要行軍,而敵人晚上可以休息,天亮後找到我們進行攻擊,把我們越發弄得人困馬乏。
記得過了甘肅張掖以後,有一夜,北風呼嘯,天寒地凍,我們走了一程,當時我是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的警衛員,在臨澤縣西北角的沙河堡宿營,還沒等把馬肚上的帶子鬆開,西路軍一局的潘局長就命令我和紅30軍89師267團的偵察人員繼續偵察前進的道路。
我們偵察隊一行二十來個人,由一個參謀長率領,騎著馬出發了,道路偵察好了,就往回返。
為了讓馬歇歇氣,我們牽著它走。到了距沙河堡只有二十多里路的一個村莊,我們想,應該不會發生什麼問題了,就打算休息會兒,弄點來水喝,把馬也喂喂吧。
但是,太陽已經出來很高了,太陽就是時鐘,但當時我們因為太累了,沒有去注意。這個時候,正是敵人猖狂的時候,所以得趁早趕回宿營地,於是又立即牽著馬,出了莊子。
才走出不遠,只見右前方一溜濃煙遮住了天,幾百名馬家軍的騎兵像群豺狼向我們衝過來了。
雙方都看得很清楚,來不及隱蔽了,那只有和敵人幹,但總部今晚的行動,全靠我們的偵察,總部不知道前方的敵情怎麼樣,更不知首長的安全如何,我們勢單力薄,不能和敵人硬拼下去的,要保護好首長的安全,就必須從敵騎中衝過去!
尤其是我,當時是徐向前總指揮的警衛員,安排我們出來偵察,就是為了在行軍時更好地保衛首長,現在敵人衝來了,我心裡恨不得馬上就跑到首長身邊去,哪怕敵人騎兵再多。
“上馬!”參謀長一聲令下,我們就像箭一樣向敵人心臟穿去,於是,混戰開始了。
敵人使的是麻雀戰術,沒有個戰鬥隊形,匪兵們蜂擁地嚎叫著,放著槍,揮動大刀衝過來。槍聲混合著廝殺聲,戰馬騰起的塵土攪得烏煙瘴氣。我們左衝右突地衝殺了一陣,便分散了。
突然,一個頭戴黑羊毛大帽子、滿臉黑鬍子的傢伙,騎匹長鬃黑馬殺氣騰騰的躍馬衝向我,企圖把我攔住;我回頭一看,後面還有好多匹馬同時也追過來了。
情急之下,想到總部首長的安全,我覺得我不能戀戰,得趕快衝回宿營地,我知道我的馬跑起來很快,就拼命地打馬向前衝。
那個黑鬍子的匪兵見我這樣,仗著同夥人馬多,更加拼命地追趕,看樣子是企圖想把我捉活的,於是兩匹馬齊頭奔跑,誰也不相讓。
我見敵人這樣死命地追,不管敵人再多也決心幹掉他!我時而用刀砍,時而用槍射擊。這樣互相廝殺,拼了好幾千米,敵人的馬跑得白沫飛濺,我乘那個黑鬍子傢伙剛衝上來沒注意,朝著他的腦袋就是一刀,把他砍下馬去了。
這時,我見前面有片棗樹林,就直奔樹林而去,想擺脫敵人,我一提馬鬃,跳過一道壕溝,又從一匹死馬身上蹦過去,進了棗樹林子。
忽然,聽到有個傷員在喊叫,恍然之間看到右邊不到一百米的地方,又有兩個匪兵傢伙在向我射擊,我當時也顧不得死活了,只想救起傷員,我們都是爬雪山、過草地、同生共死的階級兄弟啊!長征以來,好多戰友都被拖垮了,現在戰友就是寶貝。我連忙抽出駁殼槍,瞄準馬匪還擊,幸好,那兩個傢伙都被我打倒了。
我跳下馬來一看,原來傷員是陳學品同志,他右腳負了傷,身上、臉上蒙滿了塵土,衣服褲子都撕得稀爛,顯然是他在負傷後又爬了一段路啊!我趕忙扶他上了馬,就一手拿槍,一手牽著馬走。
馬累得就像雨淋過一樣。我們在彈雨裡,在廝殺聲中,在敵騎的追擊下,藉著樹林的隱蔽,邊戰邊走,終於擺脫了敵人,艱難的回到了沙河堡。
進了沙河堡不久,追擊的敵人就從四面八方圍攏起來,漸漸地人群越圍越厚,頓時,沙河堡周圍塵土蔽日,到處是揮動著馬刀的敵騎,據說,是敵旅長馬彪的一個騎兵旅全部趕到了。
估計敵人已經知道這裡住的是西路軍指揮部,便瘋狂地展開了攻擊。沙河堡四周有四尺來厚三丈多高的圍牆,門又大又厚,用鐵皮包著,活像座古城。我們依仗著圍牆,用有限的槍彈還擊著敵人。
雖然有高大、堅實的圍牆,但總部淨是些機關幹部,警衛部隊又少,敵眾我寡,不可能堅持到後續部隊來增援,所以,首長決定當晚突圍。
大門又被敵人封鎖了,要突圍,就必須挖牆洞子。天慢慢黑下來了,首長、機關幹部、女同志、戰士都開始動手挖洞了。工具不夠,有的用刺刀,老百姓也用門板、竹筐幫助抬磚土。
突圍前,每個人都準備塊白布或者白手巾,圍在左胳膊上,以便黑夜識別。
我們警衛員怕馬在突圍中被驚跑,都上了“馬嚼子”,並研究了保衛首長的方法:分左右兩路,讓首長在中間,敵人只要不全砍倒我們,馬匪就休想接近首長。
我們當時都清楚,不死拼是難以突出重圍的,因此,都下了“誓死保衛首長”的決心。
大概是晚上九點來鍾,突圍開始了。
首長們分散著和總部人員從各個牆洞一起往外衝,四面開花,把敵人衝了個矇頭轉向。
我們這些警衛員,把韁繩纏在胳膊上,腰裡彆著上了膛的駁殼槍,手提著大刀,分左右兩路,保衛著徐向前總指揮,乘敵人混亂之際衝出了大門。
密集的敵兵,被我們這一衝,像劈開的波浪一樣往兩邊閃開,接著步槍,機槍,手槍一齊開火了,喊殺聲震天動地。
我們的腳前腳後,馬蹄子的前後淨是槍彈發出的火星子,我們就好像是踏著火星子向前衝擊。
這時,我的心特別緊張,生怕首長髮生意外,不時回過頭去看,同時,我的眼睛一點也不敢鬆懈,緊緊地搜尋著混亂人群的前後左右。
剛衝出來的時候,敵人像窩蜂一樣緊緊地包圍追隨著我們,我們有時用刀砍,有時用手槍射擊,迫使敵人無法接近。
漸漸地夜深天黑,對面辨不清人,我們就乘機高喊:“衝!抓活的,殺!”來矇蔽敵人,使他們弄不清楚我們是誰。
就這樣衝殺了二十來裡地,敵人漸漸地終於被我們甩掉了。槍聲、廝殺聲也慢慢落在了後面,我們終於把徐總指揮安全地突出了重圍。
鄧忠國(1917—1989年),安徽金寨人,曾任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的警衛員,解放後曾擔任遼寧阜新軍分割槽司令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