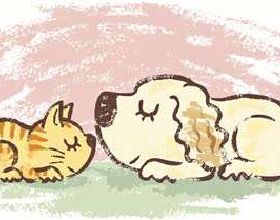“飛”的輕盈自由,“狗”的笨拙和略帶自貶的戲謔;心在嚮往天空,脖頸卻被項圈繩索牢牢拴住。誰能說清楚,這究竟是不是趕在60歲關口前推出第七張專輯《飛狗》的崔健的心境?
至少在搖滾老兵的這次新創作中,自我矛盾和掙扎,是貫穿始終的最明晰旋律。
A面:作繭自縛
闊別六年之後,崔健再次歸來。與單曲時長動輒達到七八分鐘的前作《光凍》相比,《飛狗》的八首歌,總時長只有37分鐘,然而聽感卻並不輕鬆。
在緊跟主打歌而來的次曲《時間的B面》中,帶有濃重布魯斯味道的吉他樂段,配上音色沙啞卻情緒鬆弛的薩克斯,和引人搖擺腰臀的鼓點,令人彷彿置身於滾石樂隊上世紀70年代初的錄音室,或是新奧爾良地區瀰漫著酒精、汗水和荷爾蒙味道的小酒館。
但老崔的聲音一上線,歌曲的氛圍立刻有變。不論是開篇處的假音,還是副歌部分的嘶吼,崔健的唱腔都與樂隊的演奏風格不同,過於緊繃,太像是在向某個假想的朋友或敵人證明著什麼。
崔健已經跟著他的樂隊成員(薩克斯手劉元、吉他手艾迪、貝斯手劉玥和鼓手魯超)們玩了多年爵士樂。他說這幫合作伙伴“看不起我這種玩搖滾的”,雖然只是句言重了的玩笑話,但其中也隱藏著某種真相。在吸納了多年爵士樂養分後,老崔似乎依然沒能真正消化掉爵士樂的本質——它不強制要求思想性,不強制要求觀點的輸出。它向聽者索取的,只是在身體與心靈層面的完整投入,一旦做到了這點,在樂手的手中或口中躍動震盪的樂器,和聽者同樣在躍動震盪的身體,便可以合二為一。
歸根結底,老崔還是個搖滾樂手。他不怎麼熱衷“搖滾教父”之類的浮名,但與“搖滾”二字相關的種種狹義內涵,以及80年代精神為他賦予的責任感使命感,依然是他無法也或許不願卸下的重擔。於是我們看到,在《飛狗》整張專輯中,崔健依然像幾十年前一樣批評、戳刺著現狀。
“如雷貫耳的嘲笑”,
“滿地打滾的鮮肉”……
這些或隱晦或直接的意象,都在試圖讓《飛狗》成為一個透視當下的萬花筒。
即便如此,老崔的嘗試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無效的。畢竟,他試圖召喚的物件,要麼忙於為生活奔波,要麼已躺平,很少有人願意費力解讀那些他精心炮製的海市蜃樓般的意象。所以當他如飛狗般向宇宙咆哮,向世人發出“咱倆一起淪陷”、“咱們來個互相摧毀”之類的邀約時,卻不一定能得到迴音。搖滾改變世界的年代早已過去,與崔健在國內地歷史位相仿的傳奇們,要麼將目光投向更寬廣的維度,要麼創作愈發走向內心,要麼早在青春期就已放逐了自己。崔健所堅守的,是搖滾精神當中最“重”的一面,這個由他自己選擇的十字架,也註定會阻礙他飛翔。
B面:困獸猶鬥
身陷於不可解的困境並不要命,要命的是對這種困境有著充分的自覺。崔健顯然對戰場的變遷甚至消失有著清醒的認識,正如他對自身體力與荷爾蒙的衰退也有著足夠的體認。
所以,儘管在《時間的B面》裡如愣頭青般叫囂著“老子根本沒變”,儘管在《半邊兒天》裡還是那個用鼓點和高音撩撥美人兒的北方爺們兒,在更多的曲目中,崔健所表達出的,卻是老兵凋零的遺憾,和心有餘而力不足的落寞。他時而流露出“想吼卻沒吼,血氣還是不夠”的怯懦(《留守者》),時而感嘆自己已無法像年輕時一般恣意張狂:“一頭牛走上兔子的路……野性在溫情中迷路”(《兔子牛》)。至於昔日疆場的面目全非,更是讓心有猛虎的老崔無所適從,他唱著“昨日的追求已不再明確”,唱著“畫地為牢”與“畫天為牢”,唱著“我初心到底,沒有目的”(《繼續》)。烈士暮年,壯心猶在,卻未想到與他對壘多年的老敵人,早已變成了風車。沒有人能不被時代改變。
所以,在時代變遷的大浪中該何去何從?老崔給出的答案很明確,他選擇“留守”,選擇“繼續”,哪怕這會讓他顯得荒謬可笑、不合時宜。這種與自己較勁的鬥爭,有時的確顯得糾結擰巴,它讓老崔的聲音時常與樂隊的伴奏相對抗,讓歌曲在內耗中流失了許多能量。但老崔的自我掙扎,也為整張專輯帶來了那些最動人的時刻。它們全都來自於當老崔接受自己的荒誕、不再試圖贏下這場戰爭、只是甘願成為整個壯懷畫卷的一份子時。
當老崔在《留守者》中嘶吼自己的堅守時,他似乎很明白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道理。於是隨著他的嘶吼,小號聲在臨近歌曲結尾處洪亮地出現,強勢卻溫柔地將歌曲帶回過去,帶回那個老崔帽子上的五角星閃閃發光的年代。
當老崔在《繼續》中將音調驟然提高八度時,吉他和女聲合唱所組成的音牆,卻如海水般將他的嚎叫淹沒,對應著歌詞中“天空壓下來,考驗我的耐力”的畫面。這首含義曖昧的曲目像《一塊紅布》一樣,塑造著一個負重前行的“我”,和一個以溫柔與愛作為武器的“你”。而崔健已經不再想贏得較量,甚至不再知道自己究竟在和誰較量。他開始允許自己被擊敗、被淹沒,但他還沒有允許自己落荒而逃。
若是已經無力逆天行走,
那麼像條灰狗一樣在泥濘中繼續打滾,
對一位老戰士來說,
也並不是一個不理想的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