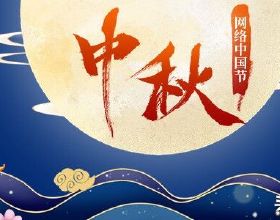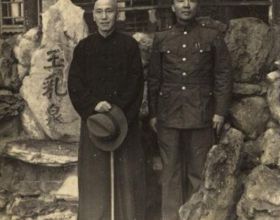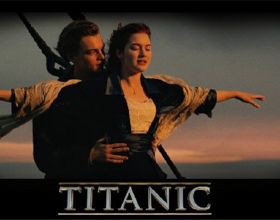作者:王宏超
我們印象中的歷史,總是充滿了轟轟烈烈的事件、標誌性的日期、載入史冊的名人英雄,然而當我們深入到歷史的脈絡中,就會發現,古人的日常生活也是一座寶藏。
所以,對日常生活的關注,並非對宏大主題的排斥和迴避,而是觀察歷史視角的轉換。
對於日常生活來說,時間因素最為重要。自然時間系統給人們的生活建立了一個基本的秩序:一年四季十二個月,每月三十天,每天日起日落,一日之中有十二時辰,形成了系統嚴密的時序系統。
古代的休閒生活,多以自然時間系統為主要的依據。
此外,人文時間的劃分,讓人類的時間具有了文化內涵,如節日,因為承載了許多文化內容,而使得休閒活動有了豐富多彩的文化意蘊。
古代也有完善的休假制度
空餘的時間是人們進行休閒活動的基本前提,就如現代社會中有很多法定節假日一樣,古代也有完善的休假制度。
古代的官方休假時間可分為三類:一是各種節日,如一些傳統的宗教、祭祀和民俗類節日;二是假日,即法定休息日;三是臨時性假日。
但需要指出的是,古代的休沐制度,主要針對的是官僚階層,且並沒有被嚴格執行,對於農民、手工業者及商人來說,其作息並無定例,有些勞動者終年勞作,長年無休,也是常有的情況。
古代的重要日子,如元日、元宵節、端午節、清明節、夏至、伏日、中秋節、臘日、冬至等,都要放假休息。
如元宵節起源於西漢文帝時期,漢代放一天假,唐代放三天假,宋代放五天假,到了明代放十天假。民間認為伏日有鬼出行,不便外出,“伏日萬鬼行,故盡日閉,不干它事”(《漢官舊儀》),所以只能放假休息。
冬至是陰陽二氣轉換的時節,要以靜養為主,“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後漢書·禮儀志》),也要放假休息。
臨時假期是特別的福利
官員的法定作息制度稱為“休沐”,這一制度起源於西漢:“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初學記》引漢律)
沐,最早的意思是洗頭髮,後來泛指洗浴、洗滌,這裡指代的是休息。上面的話即是說,官員每五天可以有一天的沐浴、休息時間。
唐代把五日休沐改為十日休沐,也就是旬休,“九日馳驅一日閒”,工作九天休息一天。上、中、下旬各休息一天,這三天分別叫作上浣、中浣、下浣。
為何唐代較之漢代假日有所減少?
漢代官員一般住在官署內,而不是住在家裡,辦公時間就比較充裕,所以可以五日回家休沐一次。唐代之後,官員一般就住在家裡,來回上班,效率降低,休息時間也隨之減少。明清時期官方假日在旬休基礎上又進一步減少,一方面是因為政務增加,另一方面也是皇帝加強集權的一種體現。(《國史探微》)
有些官員會在假日中勞作,如東漢時的尚子平,“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供食飲”(《文選》李善注引《英雄記》)。大概是做官收入不高,就在休息日上山砍柴,以貼補家用。也有人在這天加班,以處理未完成的公務。
一些特殊的日子,比如皇帝誕辰,也會放假幾天,以示慶賀。
唐玄宗把自己的生日定為“千秋節”,放假三天。此後的帝王多沿襲這種做法,在生日時給官民放假。
唐代尊奉老子,把老子誕辰稱為“降聖節”,放假一天。還有一些忌日,也是上下“廢務”,不上班。家庭成員中,近親的婚喪,官方規定可以回家休假。
如父母去世,必須丁憂去職,服喪三年,如果是軍職,則為一百天;離開父母三千里之外,每隔三年有三十日定省假(不包括路上的時間),父母在五百里之外,每隔五年有十五日定省假;兒子行冠禮(即成年禮),有三天假期;兒女婚禮,有九天假期;授業老師去世,有三天假期,等等。
這些臨時性的假期,有些是許多朝代一貫的制度,有的只是某個時期的規定,這些假期多涉及政治管理、家庭關係以及個人交往等因素,算是古代官員們的特別福利。
一派笙歌夜未央
古代社會中夜晚的生活是簡單的,一般人睡得都很早,對於這種現象有幾種解釋:一是認為農民勤勞,形成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作息方式;二是從養生的角度說,晝起夜伏符合自然規律;三是從社會管理的角度,認為政府為了強化社會的秩序,採用宵禁制度,除了一些特殊的節日,如元宵節外,其他日子晚上不允許活動;四是照明效果有限,現代的照明技術還沒有出現。
社會學家李景漢在《北平郊外之鄉村家庭》一書中,還提出了另外一個解釋,那就是照明的成本。此書調查的物件是民國時期的北京,但其中反映出來的一些情況對於中國古代社會來說也是基本適用的。
書中談到民國時期農民家庭的照明,一般使用煤油。“在夏季,晝長夜短,許多貧家不用燈火,只在冬季天短時每晚用油少許,每月少者約用一斤,多者約用二斤,每斤價約八分。普通人家在暖季每月約用一斤,在冷季每月約用三斤。”
在對一個村莊的調查中,平均每家一年花費二元。而這個村莊的收入情況,每家年收入在一百元上下,照明費用佔年收入的百分之二;全村一百多戶人家,蔬菜消費未滿五元的有三十六家,佔三分之一多,所以兩元的煤油費用,也算是一筆不大不小的開支了。
古代官方在一些節假日中張燈結綵,要求百姓掛燈,許多百姓都難以承擔這筆對他們來說很高昂的費用。
古人晝起夜伏的生活方式受到了自然的限制,在照明條件落後的情況下,晚上無法做更多的事。同時,時間的安排除了遵照自然規律以外,還受到社會管控因素的影響。
對於時間秩序的管理,是社會管理的重要內容,尤其是對於夜晚,歷代官方都有嚴格的管理制度,這稱為夜禁制度。
“禁民夜行”,夜間人們不能隨意出行,行為方式受到了很大的約束。
白天的世界如果說是光明的、理性的、有秩序的,那麼黑夜則代表著黑暗、非理性、混亂與罪惡。
《大元聖政國朝典章》中就規定:“其夜禁之法,一更三點鐘聲絕,禁人行,五更三點鐘聲動,聽人行……違者笞二十七下,有官者笞一下,準贖元寶鈔一貫。”
晝伏夜出,夜聚曉散,是對晝出夜伏秩序的打破,在官方看來,就代表著罪惡、奸盜之事。
宵禁制度也與城市防火有關。古代建築多用木材,而城市中人口密集,房屋距離很近,一旦失火,局面往往容易失控。
儘管古代的城市建立了在當時來說比較完備的消防系統,比如南宋時的杭州城,城內有消防軍卒2000多人,城外有1200多人,配備有水桶、繩索、旗號、斧頭、鋸子、燈籠、防火衣等裝備,但城市防火的壓力還是非常大的。
馬可·波羅對於杭州城的燈火管制印象深刻,他專門記錄說:“守望者們的職責是,在法定禁火的時刻到來之後,看看還有誰家露出任何火燭之光。如果他們發現到了,就會在其門上標上記號,而一大早房主便會被傳喚到官吏面前,如舉不出正當理由,便會受到懲處。同樣,在法令禁止的時間內如果他們發現有任何人在街頭亂走,亦會將其拘捕,並於次日清晨將其押送給官吏。”(〔法〕謝和耐著,劉東譯《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
星期制有助勞逸結合
隨著近代中西之間的交流,中國人注意到了西方的七天星期制。
許多人對此表示贊同,認為一則可以勞逸結合,利於養生;一則可使“中西一律”,符合世界通例。但也有抵制者,他們認為中國人遵從西俗,有違傳統,且不符合中國人的生活習慣。而且星期制有宗教的根源,更是讓人無法接受。
如張之洞就曾規定兩湖書院的學生,只能按原來的慣例休息,不能採用星期制。
1902年,清政府開始全面推行星期制,之後星期制逐漸成為中國人新的作息制度。在城市中,星期天成為人們最重要的休閒時間,多種娛樂專案也多在星期天進行。星期制的引入,更為重要的意義是改變了中國人,尤其是勞動階層的生活觀念。
中國是傳統的農業國家,在古代社會中,由於技術和工具落後,農業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人力,由此也逐漸形成了多勞動少休息的作息方式,勤勞一直被視為中國人的傳統美德。純粹的娛樂消遣,一直被中國人看作是不務正業。
現代作息觀念讓普通人意識到張弛有度、勞逸結合的重要性,透過休息娛樂來恢復體力和精力,從而讓工作更有效率。
如梁啟超所說,中國人雖然投入了很多時間去工作,但效率反而不如善於休息的西方人:
西人每日只操作八點鐘,每來復日(即星期天)則休息。中國商店每日晨七點開門,十一二點始歇,終日危坐店中,且來復日亦無休,而不能富於西人也,且其所操作之工,亦不能如西人之多。何也?凡人做事,最不可有倦氣,終日終歲而操作焉,則必厭,厭則必倦,倦則萬事墮落矣。休息者,實人生之一要件也。中國人所以不能有高尚之目的者,亦無休息實屍其咎。美國學校,每歲平均只讀百四十日書,每日平均只讀五六點鐘書,而西人學業優尚華人,亦同此理。(《新大陸游記》)
梁啟超把星期制及作息安排,看作影響中西文化強弱的關鍵因素,雖有誇大之嫌,但也不無道理。
(摘自《古人的生活世界》,王宏超著,中華書局,有刪節)
來源: 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