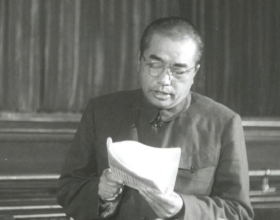高林
沈昌文先生是一位編輯、一代出版家,終其一生,他始終活躍在編輯出版界,但他的朋友圈以及影響力卻遠遠超出了編輯和出版,遍及思想文化各界。我是沈先生的一位圈外的後輩,和沈先生交往迄今已有三十五年,在我看來沈先生和其他的出版家似乎有著一些不同,他的這些“不同”,給我留下了許多印象深刻而又值得回憶的東西。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沈先生。我初次見到沈先生的時候,他就是這個樣子。
一
沈先生總是稱自己是“知道分子”,他的口述自傳也定名為“知道”。“知道分子”語出王朔,其本意多少有點貶義,但沈先生對這個稱呼卻樂此不疲,有些時候還引以為豪。這除了他個性中的自謙和詼諧之外,與他所理解的編輯出版工作者的性質和地位有直接的關係。
在沈先生看來,編輯出版是一種中介和服務工作。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他在某期《讀書》的編後語中針對有讀者提出的《讀書》應當歸入“精英文化”時說,《讀書》的任務也只在介紹、引導、汲取,它的主要工作不是在學術上進行創立和建樹。如果還可以另立一個名詞來表達《讀書》的性質,也許可以勉強稱它為“橋樑文化”,即人們也許可以透過它而到達“精英文化”之彼岸,但它本身卻不是彼岸。
編輯出版工作者應該做“知道分子”,而不是像作者和一些讀者那樣去成為“知識分子”。要做好編輯出版工作,就應當把自身定位為“橋樑文化”的實踐者,踏踏實實地去對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做比較全面的瞭解和相當程度的觀察研究,雖不以主要精力去追求精神方面的創造,但卻致力於把精神方面有所創造的“知識分子”的境界和思想(“知識”)傳遞給讀者。這個“知道分子”和以前所說的“雜家”有幾分相似,但卻也不大相同。其中重要的一個不同就是,“知道分子”要具有相當的辨別能力。如果不“知道”,就無法很好的加工和傳遞“知識分子”的“知識”,有時甚至都很難區分真假“知識分子”。
由此看來,編輯出版工作者不僅要懂得文字語法和相關專業知識,懂得“齊、清、定”,更重要的是要“知道”,成為“知道分子”。沈先生自居的這個“知道分子”,也和新聞記者的光榮稱號一樣,是個無冕之王。他借用了王記“知道分子”的名稱和部分內涵,賦予了具有自身特點的不同含義。
要做好這個“知道分子”,首先要處理好和讀者的關係。沈先生在《讀書》雜誌的編後語中就提出過“知道分子”編輯的兩條“禁忌”,這可以說是兩條基本的底線或“紅線”。一條是,編者同讀者、作者之間,絕不是什麼“專政與被專政”的關係,而要真誠相見,平等相待。《讀書》這種刊物的編輯,沒有權利教訓讀者“應當”如何。這種在文章中動輒用七八個“應當”來指示讀者的口吻,今後在《讀書》的篇幅中倒是“應當”絕跡。另一條是,即使人事滄桑,《讀書》還是力圖追求一種境界,同作者同讀者有一種平等的交往、人情的聯絡。編輯同讀者之間的合理的有人情的關係,首先無疑是指編輯要盡最大的努力為讀者提供最佳產品,而不要為一己之私,汙染讀者的心靈。
編輯要為讀者提供最佳的產品,讀者又應該怎樣對待呢?沈先生認為,讀者有權抉擇,有權選剔;有權不相信作者、編者說得天花亂墜的漂亮詞句,也有權讚賞使自己稱心愜意的任何文字。不自由的閱讀,既違背讀者個人的意願,強制性的被灌輸,被迫的尋章摘句,徒勞地尋求文章背後實際不存在的“微言大義”,無論是出於習慣,還是由於本能,恐怕都已過時了。
這樣的讀者,也許是不那麼容易滿足的,這就要求編輯要更加地“知道”,更全面地“知道”。編輯或許不直接參與精神領域的某種創造,但卻要致力於推進這種創造。沈先生稱之為“再創造”,他說,寫作和閱讀存在著辯證關係,作者和讀者必須相互依靠。讀書不是消極被動地接受,而是讀者在作者引導下的一種再創造。我們想要追求的境界,倒正是薩特拈出的那個“讀者的再創造”。作為幫助讀者讀書的刊物的編輯,責任就是幫助自己的讀者進行這種“再創造”,影響他,作用他,使他產生“再創造”的欲求,完成“再創造”的過程。
促成讀者的“再創造”,三聯書店在過去一個時期內出版的書和《讀書》雜誌,可以說是一個理想的實踐專案,這已被讀者、作者和業界所公認。沈先生和一代編輯出版人為了這種“再創造”而做出的種種努力,可以說有口皆碑。
但沈先生所偏愛的做法,也許別具一格。對此,沈先生曾引經據典地說,維特根斯坦說有可說的語言,也有不可說的只可“顯示”之事,當編輯的天天同語言打交道,本身卻不說話,只是將作者的雋語妙言加以顯示,以備讀者選擇而已。在談到具體做法時,他說,言在書中,亦在書外,這也許就是我們經常採用的一種激勵再創造的辦法,讀了一本書,浮想聯翩,往往看的是書內,想的是書外。沈先生說,“有一度我也自問:這言外之意人家看得懂嗎?後來我就領教了,這讀者真是厲害!特別是那些沒有名聲的、遠在一個偏僻小城市的、某縣城一所中學裡的老師,他們有見解,寫信沒有顧忌,一針見血,說到要害處。你的話後邊的意思,他們一眼就看穿了”。這想必不是個案吧,讀過那個時期《讀書》的讀者,應該都有這種“不言而喻”的感覺。
沈先生的另一個偏愛的做法,似乎更有自己的個性。他認為,為學也往往有別徑,那就是不拘形式,不限格局,只求心神領會,不在背誦記憶,更不要什麼教條陳規了。所以,他一直在嘗試或努力推進這樣的做法,假如我們設想的讀者是橫靠在躺椅上,信手拿起刊物,從自己喜歡的那一篇文章隨便讀下去,或者是把刊物揣在口袋裡,什麼時候乏了掏出來翻翻——那麼這刊物又該是一種編法。他一直都說,《讀書》應該可以讓讀者來“臥讀”。在他看來,文章不夠深入淺出,內容不夠多樣豐富,形式不夠生動活潑,要說這些缺點是作者的文章,原就如此,似乎也無不可,但是老實說來他們的責任是要編輯部負的。
什麼是沈先生所向往的編輯出版“知道”呢?他說,編刊物要是能到這程度,才可叫“絕”。編輯不是一味迎合地去研究市場的需要,並不總是挖空心思地考慮如何打好“擦邊球”,使刊物惹人注目,而是同讀者在精神、思想、心境上自然契合,“想到一塊兒去”。他又說,它(《讀書》雜誌)顯然要有更多的對文化的終極的關懷,使自己更加具有深度——一種明白曉暢而非深奧費解的深度。我想這兩句話,可能就代表他的“知道”。
“知道”,是沈先生的一個標誌,一個代名詞
二
沈先生的個人風格亦莊亦諧。常有人說他“頑”“老不正經”,而且是“越老越頑”“越老越不正經”。還有許多人熱衷於談論他的各種“糗事”,以及各類“妙論”,往往令人捧腹大笑。
沈先生寫文章和說話時,特別是在公開場合時,“自謙”之詞就比較多,習慣於說“無能”“不才”“不足”等,姿態都是比較低的。到了一定程度,就有了“正話反說”或是“正理歪說”,這似乎已成為他的風格,寫了許多字說了許多話,總要流露出來這樣的幾段幾句。作為一個文人,他有別於傳統的文人,也有別於許多三聯前輩。
其實,對沈先生察其言,觀其行,就不難體會到他這種“反說”“歪說”背後的“正話”和“正理”。他時常自稱“我是三聯下崗職工沈昌文,我在三聯掃地”,退休二十多年,又在其他出版單位“混”得風生水起,在“江湖”上聲名日隆,卻還念念不忘他的“出身”和“老東家”。我們很少能夠看到,一個退休的“一把手”,像一個普通員工二十多年來幾乎天天到原單位去,默默地做和書有關的事。他一生只從事過一個行業,就是和“三聯”相關的編輯出版行業,他只受到過一種影響,就是“三聯”的影響,他對三聯的愛,是無法抹去的。
沈先生還說,自己是個“三無掌櫃”,帶了個“三無”編輯部。“三無”者,有人總結是“無學歷、無職稱、無閱歷”,言外之意似乎是“有能力”。但沈先生自己的解釋是,“無為、無我、無能”,一個十足的“三無世界”。沈先生最早說的是“無能”,經過吳彬大姐的總結和細化,才有了這個“三無”。沈先生寫過一篇回憶《讀書》雜誌的自述,題為《出於無能》。但其中有一句話,就不認為無能者必然無為,“現在世多英雄,遂使無能者有效力之地了”。如前所述,這個“三無”正是他對編輯出版工作的深刻理解和認識,只是表達方式不同而已,這正是他的別具一格之處。
沈先生和“三無”編輯部成員吳彬、楊麗華、趙麗雅、賈寶蘭、郝德華。這是一段令人心生敬意的歷史,最讓人留戀的《讀書》就是這幾個人在這個院子的地下室裡編出來的。
沈先生常說“廢紙我買”。他的“名片”本身就是用名副其實的廢紙裁成的一方小紙,上面漫畫了一個平頭憨笑的老頭拎著一捆書,上寫“廢紙我買”。“廢紙”者,就是用了一面的影印紙,他用來貼上或再次列印新的資料。他的個人資料絕大部分都是用這種方式整理和儲存的,直到去世前幾天,他還在整理資料,說要交給在美國的女兒。他的一生都在做編輯工作。“廢紙”的另一所指,是舊書,有時是影印、複製或“復刻”的舊書。沈先生的一大愛好,就是逛舊書攤、淘舊書。無論在北京上海,甚至美國、香港和臺灣,他都一如既往。他非常熟悉許多書的每一個細節,他也時常把這種對書的愛傳遞給別人。相比起書的開本和裝幀設計,他最愛的是書的內容,特別是書中那些與眾不同、別具一格的觀點。他蒐羅的舊書都要這種特點。許多朋友都經歷過這樣的事,沈先生說起一本書,對方沒有又想讀,沈先生就會想方設法淘到一本,實在淘不到他就會複製一本相送。所以,有人藉此評價他,圓融之中未失真淳,待人接物仍循常理。
“廢紙我買”,這是沈帆眼裡的沈先生。沈帆是一位平面設計師,也是沈從文先生的孫女,她曾有一段時間和沈先生共事。
有人批評沈先生,說他主持出版的引進著作中刪削過多,且未做說明。對此,沈先生總是一笑了之,似乎並不在意。平心而論,刪書對最溫和的批評者來說也是不可接受的。但沈先生在當時的情況下,也確有難言之隱,他可能比所有的人都更不願意這樣做。以後的很多年裡,每當談起此類的書,他總會說某本書的原文版或海外版和內地版有些什麼異同。有時候他送給朋友的書中,還會把被刪的內容一一補上、被改的內容一一復原。
有人問沈先生,最近您在忙什麼?他總會毫不猶豫地說,什麼也不幹,吃喝玩樂呢!他說的“吃喝玩樂”其實都是在餐桌上,他主持三聯書店工作時,就以經常組織飯局而聞名,他還說過,要想征服作者的心,就要先征服作者的胃。沈先生不是美食家,他所組的飯局也多在價廉味美有特色的小餐館。他只是用這種方式來和作者以及出版相關的人溝通。他還把退休後的生活稱為“幫閒”,進而總結了二十個字的“工作流程”,即:“吃喝玩樂、談情說愛、貪汙盜竊、出賣情報、坐以待幣。”透過這些亦莊亦諧的話,我們也許可以更深刻地體會到他對編輯出版行業的熱愛和執著。
飯局上的沈先生。大約是1988年的一天,海內外朋友歡聚一堂,前面三位是徐友漁、楊渡和鄭培凱,沈先生旁邊的背影是倪樂。
有人問沈先生,您最近在看什麼書?他會說,紅的和黃的,這當然也是亦莊亦諧的話。但有一點卻不是玩笑,在鄧麗君的歌曲還被稱為“靡靡之音”的時候,他就深深地喜歡上了鄧麗君,多年來,他聽過並收藏有鄧麗君所唱的全部歌曲,還曾買了數十盤《十億個掌聲》送給朋友。在為沈先生移靈送別的時候,他的女婿播放了鄧麗君唱的《甜蜜蜜》,“在哪裡,在哪裡見過你,你的笑容這樣熟悉……”
魯迅曾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沈先生就出身在老上海的這樣一個家庭裡,未成年就輟了學到一家金店去當學徒。“我從五六歲的時候就在板縫裡看外面的這個世界,一直看到了現在。”1949年,他的命運也發生了改變。沈先生進入人民出版社時,確實是一個“無功勞、無革命經歷、無前輩領導”的年輕人,他從秘書(勤雜)、校對等最基層的工作做起,能做什麼就做什麼,從不敢有任何怠慢。1986年,沈先生受命主持新組建的三聯書店工作,他不無感慨地說,我是第一名“新三聯”。可以說,出身、經歷的不同,造就了沈先生的個人風格,也使他與眾不同。
讀了《知道》和沈先生的其他一些自述類著作,就會對沈先生的個人風格和這些“不同”有更多的體察和感悟。沈先生晚年,把他和部分《讀書》雜誌作者的通訊編成《師承集》,在其序言《我的老師》中有一句夫子自道的話,“現在,我居然可以自由出入任何一個大教授的家,彼此暢談一切!現在人們老誇沈某人當年編《讀書》雜誌多帶勁。其實,這勁兒全來自改革開放那個好年代,可並不是沈某人的個人能耐”。
要說沈先生的哪一張照片最傳神,我看是這就算一張。
三
記得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有一次沈先生講起鄒韜奮先生為生活書店定下的店訓,“竭誠為讀者服務”,我當時覺得這似乎很平常,所有的服務行業不都是竭誠為顧客服務嗎?沈先生說,這其實不然,編輯出版是一個很特殊的服務行業,韜奮先生的話,好就好在那個“誠”字。這個“誠”字具體而言是什麼呢?沈先生沒有明確說明。但他接著講了陳翰伯、陳原、範用和史枚等幾位前輩的故事,我聽下來這幾位前輩都是一心一意的熱愛出書和讀書的人,無論在什麼樣的條件和環境下,都一心一意地追求把自己認為最好的書奉獻給讀者。什麼樣的書才是體現了竭“誠”為讀者服務的好書呢?這應該和幾位前輩各自的胸襟和見識有關。
沈先生還特意講到過丁聰先生對三聯和《讀書》的貢獻。他說,丁老喜歡《讀書》,喜歡《讀書》前輩開創的思想解放風格,願意為《讀書》奉獻,做“無名英雄”。我每次見到丁老的版式樣,總是想到這點,從而產生動力。
沈先生說的四位前輩中,我見過其中兩位。陳原先生在席間推杯換盞、海闊天空之際,口若懸河、妙語連珠,但卻句句不離出書,時時談到要出有思想的好書。範用先生是那種一聽說好書就眼睛放光的人,每每說起有好的作者,好的作品,他都會精神為之一振。沈先生曾說,最有資格得韜奮圖書獎的就是範用。前些時候,我看到一封陳翰伯先生在1981年寫給友人的信,他說,看了電影《沙鷗》以後,感到自己就像女主人公從骨子裡熱愛排球一樣,熱愛出書,一刻也離不開出書。他還說,出版貴在堅持,堅持不但是長久,更重要的是堅持信念,新聞出版工作者不可不弘毅。沈先生說,史枚先生捐介耿直,特立獨行,在編輯出版中堅持原則,不懼各種壓力,直至生命最後一刻。
沈先生曾講過,生活、讀書、新知三家書店在成為“三聯書店”之前有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機關。解放以後這個功能不再需要了,但三聯書店的名號為什麼還要儲存下來,而且現在還要恢復建制呢?這就是因為這三家書店有一批有堅持有信念的前輩,在那個年代都出版了一批留下過歷史痕跡、引導過時代潮流的好書。一個出版機構,其實不需要人來寫其歷史,它所出版過的書就記錄了自己的歷史,這就好像魏文帝說文學家不需要別人來寫傳記,他寫出的作品就是自己的傳記。
1979年《讀書》雜誌創辦的時候,三聯書店的前輩們就確定了這本雜誌的宗旨——“以書為中心的思想評論刊物”。這有其歷史的傳統,抗戰勝利後,陳翰伯和陳原等前輩就在上海把原來主要刊登書目的《讀書與出版》改成一個以書籍為中心的思想評論綜合性雜誌。這個雜誌後來因為1948年底三家書店受到政治壓力遷往香港而停辦。對思想文化的評論和關注,把思想文化作為出版方向,可以說是三聯前輩們的一個夙願。對此,沈先生也說過,《讀書》不是學術、時論雜誌,它以書為中心,圍繞書說話。為什麼要以書為中心,圍繞書說話呢?因為書是思想文化的載體,是文明的傳承,書的壽命是人的壽命無法相比的。圍繞書說什麼話呢?就是說對思想有貢獻,對文化有終極關懷的話。
“向後看”,基本構成了沈先生數十年來編書、出版書、策劃書的主要方向。這是沈先生和幾位“向後看”的前輩在一起。
沈先生在主持三聯書店工作的時候,有一個很重要的出版方向,就是大量引進海外和臺港的著作。這在當時可以說是一種“新知”,他曾這樣理解“新知”,新知不只是存在於海外的,也不只是介紹進來大家知道一下就算了事,就像馬克思主義這種新知必須與中國的革命實踐相結合一樣,任何稱得上新知的東西都要從中國的立場來考察同中國的事物相結合。他還認為,兩制究竟是在一國之中,大家多年來所讀、所見、所聞都是一個祖先傳下來的文化,因而也不能不有許多方面的共識。因此他在作翻譯和引進的時候,首先關注的還是國內的形勢和國內讀者的需要。
在引進和翻譯的海外著作中,有許多是“老書”,比如《寬容》《存在與虛無》以及茨威格的著作等。沈先生則說這是“向後看”。“向後看”,其實就是補課,要學習和研究在我們以前走過現代化道路的那些國家,要補上某些曾經缺失的課。因此要研究和出版在那些國家和地區曾經發生過重要影響的“老書”,對比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找到可以借鑑和啟發的東西。“人家經歷過的東西,我們無法一步跨過去,要老老實實地去體會和學習”。這是“龜兔賽跑”的邏輯,是“直道超車”的智慧,同時也不能不說是一個比較前衛的思路,其終極目的還是要在思想文化方面對社會對讀者有所貢獻。
沈先生曾回憶,他相當多次的到上級機關和有關部門去解釋、彙報和檢討,不勝其苦,有時甚至感覺到走投無路,這也是編輯出版工作中的風險之一。交涉的結果,他總是說,“心誠則靈”。“誠”在何處呢?他說,年輕的時候他反覆學習過列寧和毛澤東關於編輯出版工作的論述,深知“階級鬥爭工具論”的內涵,也在不斷的工作實踐中逐漸體會到了需要把握的邊界。但對這些似乎也並不必悲觀,他說他曾從一位研究古典文學的教授的話裡獲得過啟發,有人把寫近體詩比作是“帶著鐐銬跳舞”,但能把這個“舞”跳好的詩人有那麼多,當編輯的為什麼不能把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呢?所以,沈先生就感悟到,無限制的編輯自由是不存在的,但是目前一個編輯的首要社會責任應當是解放知識生產力而不是限制。一個編輯應該更多的在這方面做好文章。
沈先生主持三聯書店工作時的一個重要創意,就是舉辦“《讀書》服務日”活動。要做好“思想評論”,要突破自身的侷限,沈先生想到,這就需要多向社會請教,從作者和讀者那裡去開發資源。受某廠家“售後服務”的啟發,他想到了以“《讀書》服務日”之名來舉辦編者、讀者和作者以及社會各界的交流活動。結果,“《讀書》服務日”成了京城文化界的一道風景,三聯書店和《讀書》編輯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資源。雖然是“無主題、無主持、無主講”漫談式聚會,卻從不缺乏思想文化方面的高見和各種觀念思想的交鋒。“服務日裡跨禁區,如放舟學海訪天下名師益友”,說的就是當時的盛況。沈先生回憶說,“服務日”過後,夠我們編輯部消化好長一個時候,大家兜情況,想選題,深入組稿,所有這些這事都有了動力。當然“《讀書》服務日”最受益的群體還是讀者,除了廣大讀者能夠陸續讀到更多的三聯版好書之外,更有許多讀者親臨現場,和作者編者面對面交流,獲取各類新書出版的資訊並且買到了書。今天這個成功已再難複製,但不能不說服務日活動是“竭誠為讀者服務”的一個重要實踐。
“《讀書》服務日”的一個瞬間。和沈先生同桌的應該是王世襄先生(右)和陳四益先生吧。
沈先生主編《讀書》雜誌十五年多,這是一段令人心生敬意的歷史,使無數的人留戀和懷念。那個時代的《讀書》雜誌,可以說歷史已經做出了評價,並且還將進一步做出評價。這裡有改革開放的大形勢和三聯前輩們的開創擘畫,沈先生則是那個把這些天時地利人和因素創造性地付諸現實的人。
沈先生主持三聯書店工作五年多,在三聯書店的歷史上他是一個繼承者,在當時的情況下,他更是一位開創者。作為獨立建制後的第一位掌門人,他身兼編務、內務、外聯於一身,在“繼承、生存、發展”中走出了一條有三聯特色的路,上述許多開創性的工作塑造了“三聯”的品牌,也為後來打下了基礎。大約2000年前後,有人恭維沈先生說,您領導了三聯書店的“康乾盛世”。沈先生回答說,我只是開了頭,我希望三聯書店的“康乾盛世”早日到來。
回想起來,什麼是三聯精神呢?從沈先生作為一任三聯書店領導人的編輯出版理念和實踐上來看,這種精神就是長期堅持開拓思想文化領域,引領時代潮流。沈先生和諸多三聯前輩都有一點共識或共同之處,這用沈先生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書籍主要的文化功能,是積累文化,是對人們精神生活的潛移默化,所有這些都屬於所謂長期效應,寫書、編書、出書、評書的人都應當有這種長遠觀點。他們終其一生的努力,就是堅守這種長期效益和長遠觀點,也可以說是堅持了“竭誠為讀者服務”中的這個“誠”字。和其他三聯前輩相比,沈先生只是其中別具風格的一位。
到三聯書店去,常常會看到沈先生的背影。2020年11月,沈先生剛出院幾個小時,在三聯書店裡又看到了他的背影……
記得沈先生曾說過,他寫的《讀書》編後語,也就是《閣樓人語》中,有一篇自己比較得意,同時也別具特色的《擬作〈洗澡〉又一篇》。沈先生自稱這是為了“推銷”楊絳的《洗澡》一書而“擅作續集”,楊先生自然也“無法阻擋”,何況沈先生的“擬作”和楊先生後來寫的《洗澡之後》還有許多“暗合”之處呢。
沈先生“擬作”的最後,《洗澡》主人公許彥成的那一聲感嘆,在今天也還是一句“感嘆”。依照沈先生的思路,許彥成大概也像楊絳先生一樣高壽,或許還名滿天下。此刻,許彥成一定在想,又過了三十多年,《讀書》的女編輯也都退休了,只有沈昌文這個三聯“下崗職工”還時常和我聯絡,請我吃飯,給我寄書,不打電話了,就發郵件說各種新鮮事兒。如今他也走了……,我要寫點什麼呢?“真要自己寫紀念文章,怕還不是那麼一層意思”!
2021年8月初稿,2021年12月修改補充
(感謝沈雙女士、吳彬女士提供照片)
責任編輯:鄭詩亮
校對:張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