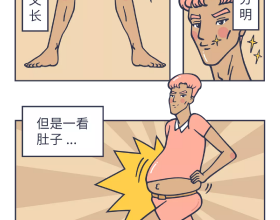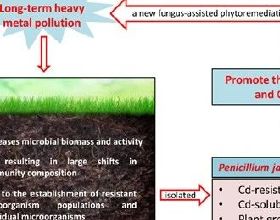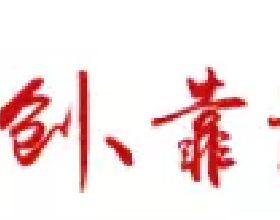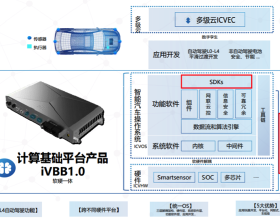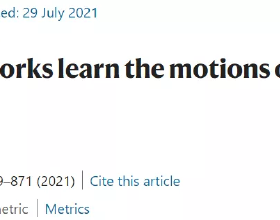長篇散文
沼蛙、蟻群、獅虎獸、兔子……這些陸地上的動物會以怎樣的方式生存,“我”又如何感知和看待它們?周曉楓的散文,無論視角、題材還是文字,總是別出心裁、獨樹一幟。這篇新作,她以獨特的方式為我們呈現出神秘多彩的動物世界,對動物界乃至生物界,以及人與動物的關係和生物發展史均不乏新鮮的觀察與思考,值得一讀。
幻獸之吻
文 / 周曉楓
幻獸之吻裡,
有致命的愛,致死的美,致殘的深情,
有致意的問候,致歉的告別,致敬或致哀的命運……
1
海南三亞,下過小雨。晚餐後,我下樓散步。
小區道路的光線漸漸暗淡,透過路燈的映照,能看到一條反光而溼黑的路。我沿著這條混沌的小路向前,突然地上的什麼東西動了一下,像個被風吹得滾落的果子。我嚇了一跳。低頭看,原來是個小傢伙。
我沒有立即判斷出到底是青蛙還是蛤蟆,像是兩者的混血兒。我蹲下來觀察,它坐姿端正,表情莊嚴,雕塑似的一動不動。個頭不大,大概只有我的拇指那樣的長度。它像揉過的紙巾,乍看鬆垮地團在一起,仔細看各部分的銜接又是緊湊的,雙腿併攏在體側,融成的整體不容縫隙。哦,這是遍佈中國南方的常見品種:沼蛙。
它長久蹲坐,彷彿在思考何去何從。溪流在另一側,而它正朝著人類的院落瞻望。這種迷失可能導致喪命。我想幫助它抵達正確的方向,又很怕兩棲類鼓起的眼睛。猶豫之後,我放棄了,決定繼續向前散步,它自己會作出選擇的。我想,等我折返的時候,如果它還在這兒,無論如何,我將克服恐懼,回家去拿長柄的掃帚和簸箕,把它拯救到彼岸。
這條路有一二百米,走到頭,我看了一會兒月亮,再返回來。返程只到半途,遠未到剛才見到沼蛙的地點,可我驚訝地發現,它停在大路中間,依然保持著剛才的姿態。這隻懂得魔法的青蛙,它怎麼不動聲色地跟了我這麼遠?像童年那個遊戲:我們都是木頭人——在你蒙起眼睛的時候,他們不知不覺地靠近你,並在你睜開眼睛的瞬間,凝固動作。我低下視線,看它,它不動;離得再近些,它還是不動。我靠得太近了!毫無徵兆,它的動作如此之快,幾乎是侵犯式地向我衝過來,帶著惱怒,帶著超過挑釁的絕殺態度。我嚇得連連後退兩步,才保持了距離。它沒有善罷甘休,直勾勾地盯著我,餘怒未消。我不明白這隻沼蛙的矛盾態度,為什麼如此厭惡我靠近,又執意地追蹤我?
我很快得知了謎底。我見到了它的孿生兄弟,不,是兄弟們。就在我看月亮那會兒,它們有許多隻,個頭幾乎一致,偶爾有兩三隻能目測出有體積差。隔上數十米,就有這麼一位佇立的“小矮人”……小得像不起眼的土塊或捲起一半的落葉。這是一條人類鋪設的步道,雖然夜晚人跡寥落,但依然危險,幾十公斤的體重可能隨時從天而降,而沼蛙的個頭兒不過是一小攤墊腳的溼泥。我有一次險些踩中,即使鞋底與沼蛙差之毫釐,但它巋然不動。
我終於發現,它們為什麼有如此表現。
我見到一對沉浸愛慾的情侶,雄性比雌性壯碩,卻由弱者揹負著蹦跳,發出很大的鳴聲。我不知道這是正在進行的歡情時刻,還僅僅是前戲中的儀式,總之被我的唐突打擾,兩隻抱團的蛤蟆分開,各奔東西——雄性不忘衝著我的方向示威性地叫了幾聲。
原來,這麼多沼蛙聚集,因為這是雨後的求偶時刻。體內的生物鐘精確催促,它們如約趕往聚合地點,參加盛大的集體婚禮。
可惜,相遇似乎並非易事。多數時候,為了等待心儀者,它們就像抱柱的尾生那樣漫長到無望地各自等候。似乎一直在傾聽和分辨,眾生喧譁的合唱中,會有一個歌喉,讓它怦然心動。它那麼凝神,那麼專注,長久得彷彿忘了時間和等待的目的。每一隻都堅決地壓在自己的影子上,只有以極低的角度觀察,才能在某個特別的角度,看見草地上的地燈把它的影子斜斜地拉長,像個小型的埃菲爾鐵塔。我把手電筒的光源打在它身上,上下移動,它的影子一上一下地跳躍,但除了明顯外凸的眼睛裡反射出的光點,它絲毫不受影響,你看不到它有任何變化。頭顱的角度沒變,坐姿紋絲不動,像個古代人盤腿在蒲團上。是的,它的腿摺疊得多麼好,貼合完美,隱藏著飽滿而彈力十足的肌肉線條。它的內肘微彎,形成空置的弧形,像是隨時抱攏伴侶。它自己是個多麼有耐心的愛人啊,像思戀或失戀到了絕望那樣,停在那裡,沒有任何表情與動作,不知道能夠等多久。
我對兩棲動物的臉,一貫懷有恐懼。但此時這些痴情者,使我產生好奇和興趣。我再次靠近,觀察另外一隻沼蛙,它好像剛剛和愛侶分開。這隻沼蛙沒有脖子和腰窩,從頭到胯骨,幾乎可以拉成筆直的斜線。無論從正面,還是上方,都會發現它有個簡直是符合嚴格幾何學的三角臉。它也沒有下巴,它的嘴是一道如此深的切痕,把它的臉一劈兩半。這使它的頭,由兩個部分組合而成:像個淺盒子,帶著隆重的盔蓋。它誇張而有些老齡化的雙眼皮,給人以複雜的感受,說不清更靠近天真者還是縱慾者。這回,它不叫了,呼吸似乎很輕,我看見它似乎潮溼的鼻孔像兩個既不擴張也不收縮的針眼。也許,它是靠隔夜茶色或鏽鐵皮色的面板呼吸的,可以不動聲色。我的鼻子快貼到地面了,才發現它的喉結部分快速抽動,頻繁鼓起和收縮,像個正在漱口或吃藥的老人。似乎一場歡愛過後,它已耗盡體能。
這場盛大的婚宴裡,每一個它,都是冷靜的、耐心的、剋制的;每一個它,都是痴情如水、激情似火的愛人,迎接著身體的狂歡節……未來的每一個蝌蚪,都是它長著一條尾巴的美人魚孩子,繼承著基因裡的遺傳:隨時為愛等待,隨時為愛枯竭,為愛赴死。
2
還是在三亞。早晨六點五十分,我下樓晨練,遇到行動中的蟻群。
它們體只極小,蟻流保持一釐米左右的寬度,數蟻並行,速度很快,像攝影機下六車道的高速公路。奇怪,隊伍中每隔幾釐米,就有一隻體型碩大的螞蟻,以同樣的速度,奔行在“車流”裡,但一定是隔離帶般出現在隊形中間的位置。它們大得像屬於另外的種群和部落,但左右都有小螞蟻隨行,我不能判斷這是戰俘、指揮官還是隊伍裡的籃球巨人。這些大傢伙,就是所謂的兵蟻嗎?兵蟻在蟻類社會中具有特殊職能,個頭大,它們的顎部發達,可以粉碎堅硬食物,也是保衛群體或發動攻擊時的戰鬥武器。
我發現這條蟻流中有條醒目的肉蟲,呈現半透明的焦金色,它作為螞蟻的獵物在進行轉運,就像一節儲備糧食的車皮。除了小螞蟻們,幾隻巨蟻先是出現在“車頭”的位置,縴夫般承受著吃重的壓力;後來,它們改變策略,均勻分佈在肉蟲的各個位置,就像是出現在長條箱子的角鐵部位……乍一看,像是隆重的抬棺隊伍,不過速度一點都不慢。
被高高抬起,肉蟲始終保持僵硬的弦月般的弧度;在翻越一個溝坎時,它突然流暢地翻轉了一下身體,像活了似的——可見蟻群完美的團隊配合能力,能夠克服路途上的坎坷,而不摔落它們的獵物。再仔細看,那條肉蟲好像真的還活著。它只是渾渾噩噩的,任由大大小小的螞蟻把它搬到新的家園或倉庫。
螞蟻的隊伍很長,竟有四五十米之遠,直至它們的行蹤隱入繁密的草叢。我在距它們的終點十釐米左右的地方,發現一隻不知死活的紫褐色蝸牛,上面攀爬著稀疏的偵察兵,似乎是瞭望和接應。這肯定不是螞蟻傾巢搬遷的原因,因為從蝸牛這點硬殼裡掏取的肉,根本不值得興師動眾地移動整個龐大的軍團。我抬頭看天,好像說今天有雨,這意味著多少千帕的滾滾雷聲,此時就隱藏在透光的雪山般巍峨的雲層後面。微不足道的螞蟻,它們生活在地下的黑暗裡,卻遠比自以為是的人類更敏感於天上的發生。它們預知,所以它們行動。
等那隻金黃髮光的肉蟲被一路運輸,消失在地層之下,我才突然醒悟:也許並非食材,那正是它們至為尊貴的蟻后!它不動,並非因為麻木或受傷,而是它正被自己的奴隸們舒適地抬起、小心地呵護、安全地轉移。它幾乎是以半睡眠的狀態,統治著自己子孫眾多的世界。
最不像螞蟻的,是它們的蟻后。
王所催生的,是不像自己的兵;兵也長得不像自己的王,像是毫無基因的傳遞——它們之間不是有些不像,它們之間是一點兒也不像。而這,或許正是統治的秘密。
3
如果有什麼是美、暴力與王權的融合,就是虎。斑斕的皮毛,沉著的眼神,生殺予奪。老虎同時可以做到非常低調,野外捕獵時,這頭體重達兩百公斤的貓科動物可以潛行於半人高的枯草間,絲毫不會引起注意……直到,獵物細狹的瞳孔突然放大,善於彈跳的四肢被死死拖住,帶血的喉嚨被吻到窒息,身體轟然倒下,陷入比地球引力更無法擺脫的死亡深淵。
我看到過一隻流浪貓捕食,看到它在好奇心和食慾之間猶豫了一會兒,才上去咬碎了獵物的臉。貓科動物大多如此,天真又殘暴,簡單又華麗。老虎也許由於體型的緣故似乎沒有那麼頑皮,除了捕獵和進食,老虎多數時候處於厭世般的懶散中。無論是在紀錄片裡看到的在荒野巡行的虎,還是動物園裡隔著柵欄看到的——鐵條和虎皮自身的紋路,它像被砍下很多刀、尚還連綴為一體的活刺身——虎總是步態懶散,神情遊離,目光蒼茫,它像是很難聚焦於某個目標。虎不像豹那麼線條清晰而肌肉緊緻,鬆懈的步態,總讓人誤以為老虎是乏力的——然而,王的凜然,也許必須保持在這種不屑一顧的倦意裡。
有個朋友熱衷探險,他給我講過年輕時的一次相遇。那時少年得志,他十幾歲時得了全國作文競賽的金獎。為了紀念榮譽和獎勵自己,他與銀獎獲得者乘興從頒獎現場直接去了神農架尋找野人。莽撞的激情,他們貿然進入森林深處,卻沒有隨身攜帶基礎裝備。他們迷路,幾乎彈盡糧絕,食物只剩一個蘋果。黃昏時分,不安的他們突然聽到一聲環繞著的低吼——回頭,正看到一頭老虎那張密佈條紋的臉,憂悶又焦躁地凝視著他們。朋友說,他們在感到恐懼之前腿已經開始飛奔,狂瀉千里地跑下山去。唯一的蘋果飛快滾落,像他們的腦袋一樣躲過了被啃咬的命運。他長大以後堅信,虎的閒散給他帶來的震懾勝於狼的攻擊。
我近距離接觸過的,只有動物園的小老虎。泰國動物園裡,不耐煩的它們被驚喜而陌生的遊客輪番抱住合影,這種熱愛獨居的動物被迫裹入它們不擅長並且反感的親暱。我作為志願者飼養過動物園裡的小老虎、小狼和小獅子,三個小傢伙生活在一起。小老虎憨直,玩起來不管不顧;小狼非常像小狗,激動起來會失禁;相比之下,小獅子害羞得多,面對面的時候它總是躲避著眼神和身體;等你回過頭去,它會在你身後磨爪子……磨刀霍霍準備撲向你毫無防範的後背。它們與人建立信任之前,要經過謹慎的試探;等熟悉以後,三個小傢伙就像撒嬌的嬰兒那樣叫喚,歡呼著進食與玩耍。無論多麼兇殘的掠食者,在幼弱時期都是讓人憐愛的,因為它們要保護自身潛藏著的破壞力,使之不受損地成長為殺傷力。
我倒是有過一次與獅散步的經歷,還是在模里西斯,那是當地著名的旅遊專案。我站在一片很大的空場中間,向四周瞭望。到處是雜生的高高低低的植叢。這片土地面積很大,我看不到周遭的鐵絲圍欄。只是越過等同膝蓋高度的灌木雜叢,隱約遙望到園區的一個鐵門,提示這裡只是仿造的自然,並非真正的曠野。我們這組遊客大約十人,一起站在那裡等待獅子,每人手握所謂用以自衛的武器——一根比柺杖還要細短的小木棍。等了許久,什麼也沒有,但空氣中的不安氣息越來越強烈。
遠處的鐵門開啟。幾個非洲裔園區工作人員的形影靠近,然後在隱約的草莽之間,我看到一前一後兩條微浪般起伏的脊線——那是和馴養者走在一起的兩頭獅子。一頭褐色雄獅,鬃毛披覆,它邊走邊舔舌,嚥下馴獸者手裡的肉塊。另一頭是神話般的白色母獅,保持著冷漠的悠閒和微妙而傲慢的抗拒。獅子們靠近……僅有一頭獅子,都給人以複數的錯覺。我捏緊木棍,即使知道徒勞無功。遊客們都不由自主繃緊脊柱和四肢,側目注視走過的巨獸。我們被提示:不要走在獅子的前面,以免被當作獵物撲倒。所以站得筆直的遊客,看起來像在接受獅子王的檢閱;只不過,獅子漠視我們,保持著緩步的懶散。
大家很快就放鬆了,兩頭獅子在我們眼裡漸漸成了兩頭可以接近的哺乳動物。我貼上去嗅它們的皮毛,沒有任何體味。我想象的那種濃烈而生猛的腥羶在它們身上蕩然無存,它們似乎有著毛絨玩具的化學性乾燥,像剛剛被浴液和吹風筒處理過。也許,這些獅子從來沒有直接處理過獵物,像人類一樣,它們的食物都是從類似廚師那裡獲得的。沒有殺伐之氣,它們被安置在介乎王者和寵物之間的某個奇怪位置上。
遊客與獅子合影,來顯示虛彰的勇氣。那些馴養者手裡也拿著和我們類似的小木棍,這個道具必是獅子曾經的教鞭,才會讓它畏怯,以至於他們把木棍抵在獅子腋下,獅子就能始終面向前方,從不回頭張望。剛才獅子在草叢間跳躍,跳過溪澗,輕捷得令人驚詫,龐大的體重絲毫沒有形成阻礙,它依然擁有殺伐者的果斷與矯健——然而,微不足道的木棍對它竟然構成威脅,以及包裹在人類肌肉後面細若木棍的骨骼。它安詳而沉靜,配合著鏡頭。除了打哈欠,獅子不會張開它氣吞山河的嘴,它像個失憶老人似的忘了撕扯和咀嚼。它們嘴裡的肉塊,切得像點心,更符合被豢養者的教養。
生命,不僅被未來引領,更重要的是被記憶所統治。一根木棍,是獅子關於權力的記憶,如同馴養者在獅子面前輕馳的自信同樣來自記憶。馴養者以暱稱呼喚他們的猛獸奴隸,而獅子奴隸抬起掛有隱約淚腺的面龐——被顛倒的等級,被置換的能量。獅子和人類遊離了各自的領域,他們和它們都靠記憶和想象存活,遺忘了自己的能力與限制。
關於虎和獅子,我有個恍若幻覺的記憶——童年見到的獅虎獸。
那是一個動物園裡的春天。獅虎獸獨自佇立樹下,大得詭異,彷彿幻覺中的動物。巨獸一動不動,混凝土製成的雕塑般,它被樹冠投下的密如織網的陰影所籠罩。春天開始發亮的葉柄被風晃動,每片樹葉的齒緣都精湛而一絲不苟,展現了神的縫紉工藝,它們將醞釀花朵、果實和種粒。春天開始發情的器官逐漸腫脹,動物們帶著暴躁而激烈的情慾交配——這是性別之間的盟約,幼崽將由此誕生。春天的空氣,瀰漫花粉與某種暖腥的氣息,這是一個混沌而充滿秩序的難以解釋的神秘世界。那頭獅虎獸厚闊的爪子踩在地上,卻看似與這個世界毫無瓜葛。
獅子生活在草原,老虎生活在叢林,自然環境下相遇機率極低;但在動物園的環境,在人工獵奇心理的驅使下,兩者交媾產下混血的巨嬰:獅虎獸或虎獅獸。陸地上體型最大的食肉動物是北極熊,然後才輪到老虎和獅子;但獅虎獸的體內沒有抑制成長的基因,所以它會一直生長。蛇是終身成長的,它不斷複製自己;獅虎獸是越來越重地負載自己,直到無法承受自身的體積。獅子和虎都是各自領域的王者,但權力的疊加未能使獅虎獸更為強大——它被自身壓垮和摧毀。尤其,獅虎獸不僅沒有成皇成帝,成為王權的象徵,反而成為被奴役的屈辱象徵——它的角色,相當於食肉動物裡的騾子。我們習慣騾子,出於實用功能——作為馬和驢的後代,它高大有力,兼具父母的優勢。騾子擅長負重,只是不會生育繁殖自己的後代——“騾”,這個字拆解下來,完美提示了它的悲劇,它是“更累的馬”和“失戶的驢”。然而,獅虎獸呢?它的存在何用之有?
神話傳說中的靈獸與妖怪多是拼貼之物,像為人熟知的龍、麒麟、貔貅、鳳凰,或者更為冷僻的畢方、帝江、陸吾、鹿蜀、贏魚等,不外是蛇的身子貼有魚的鱗片,魚的身子粘了鳥的翅膀,或者是狗的身子長了牛的角,虎的身子長了狐狸的尾巴。它們是應該停留在傳說而不應顯形的動物,唯此才能維護神秘的能量。自然界也有天生具有拼貼感的動物,比如“四不像”的麋鹿,說它頭臉像馬、角像鹿、蹄子像牛、尾像驢;比如貘,體形有點像豬;幼麋鹿身上有鹿那樣的花斑,臉有點像去掉了長鼻子的小象。也許因為麋鹿或貘等都是素食者,所以即使顯形,也不具備可怖的法力。素食的拼貼動物即使進入傳說,也帶有美妙的色彩。比如說麋鹿,原產於中國,但百年前就在本土幾近絕跡,後來一個英國公爵重金將飼養在巴黎、柏林、科隆等地動物園中的十八頭麋鹿悉數買下,放養在莊園,竟然復活了整個種群——十八頭麋鹿,是今天地球上所有麋鹿的祖先。比如說貘,它在中國和日本傳說裡,說它會在月夜走出幽深的森林,來到人們枕邊,因為貘以夢為食。它害羞又溫柔,怕驚醒入睡者,所以會發出搖籃曲一樣的哼唱,吞下夢境之後,它又悄無聲息地隱居叢林。我們知道動物有擬態行為,它們常常模仿自然環境,為了隱蔽自己;其實擬態不僅是模仿環境,動物之間也相互模仿,比如無毒動物會模仿有毒動物來保全自己——動物之間的這種擬態,既是相互的形象抄襲,也算是相互讚美的證據吧。
然而,獅虎獸是吃肉的、拼貼的、顯形的真實動物,它既與傳說中的龍鳳,又與現實中的麋鹿與貘都不同——它的產生沒有什麼實用之功,是一次被蓄意安排的雜交,是一場源於孤獨並去往孤獨的悲劇,只為證明人的自大。
我們把獅虎豺豹描述為殘忍,因為它們有破腹的利爪、碎骨的牙,因為它們從洶湧的血泊中撕扯肉塊。其實這些食肉動物算不得殘忍,因為種種作為乃是生存所需。之所以說人類最為殘忍,因為他們是精神上的食肉動物——他們的暴力出自快感,他們的作惡出自享樂。人類之所以創造獅虎獸,他們扭曲、控制和決定並非簡單出自畸形的審美,也許隱藏著並未被自己清晰認識的潛心理。活生生的獅虎獸,這頭從幻想中直接誕生為現實的巨物,有如一個成真的噩夢,給人帶來無以名狀的雙重歡樂。獅虎獸,是成功僭越的證明,是瀆神的典範,它的存在,是因為人類既篡奪了造物主的王權,又剝奪獸王的王權……由此,人類由智力上的弱者和體力上的侏儒,躍升為超能的巨人——不,巨神。
地球存在了億萬斯年,像腔棘魚、鋸鰩、鱷龜、鱟、鴨嘴獸,從古老的時代延續到現在,但更多的動物加速度地消失和滅絕,像旅鴿、斑驢、袋狼、袋狸、巴釐虎等,人類甚至來不及觀察和了解,它們就消失在地層之下。我們每個人的短短一生裡,都目睹或聽聞數種動物成為遺蹟與傳說。但,獅虎獸的滅亡,卻是令我欣喜的——我願,那種動盪而危險的美,永遠消失在它原本就不應該出現的地方。
那個童年的春天,我第一次看到獅虎獸。看到它長久呆立。看到它進食——不像老虎或獅子,獅虎獸吃東西時吞嚥得特別慢,像掉牙的老人那樣。看到它死了般的睡眠。在壯觀的骨架下面,它像是中空的,顯得特別脆弱。獅虎獸來自一場跨越物種的愛情,我迷惑——它的樣子,到底更靠近雜交最佳化基因帶來的勇猛,還是更像近親繁殖帶來的愚痴?
孤獨的獅虎獸。
某個瞬間,我看到那個來去匆匆的短暫訪客——一隻不知從哪裡冒出來的老鼠,左探探,右探探,路過可能被它視作老虎的龐然大物。也許由於體量的落差根本看不見,也許由於老鼠小到根本不配成為巨獸的食屑,獅虎獸無動於衷,任憑老鼠在自己的領地裡躥動。也許獅虎獸缺乏匹配的領地意識,那是捕獵和求偶才能喚醒的競爭——它根本用不到。獅虎獸被關在這裡,將被豢養至死。動物園關著的,多是平時罕見的珍貴動物。所有高貴、獨特與稀有的生命,都是人類的囚禁之物——他們關押,他們製造,他們展覽,他們剿殺。像老鼠麻雀一類庸常之物,無人在意,它們隨意來去,擁有為所欲為的權利。跑來偷竊食物的老鼠,銜起一粒殘渣,然後奔向它生來齷齪的自由。
4
蜻蜓的形態至為優美,但它們彷彿先天經過風乾處理,彷彿沒有體液,彷彿是夏天的金屬鎢絲——我記得那年以前的夏天,蟬聲如瀑,蜻蜓如織,到處通電般的發燙。小孩子沒有什麼同情心,我童年捕捉過很多隻蜻蜓,它們在我的掌心裡痙攣般顫抖……這麼多年,也許是因為愧悔,我才沒有忘記它們的掙扎,沒有忘記它們的翅脈如何被禁鎖在我的掌紋裡。但我想說的,是豆娘。
豆娘的體形嬌小纖細,看似袖珍版的蜻蜓,但它不是蜻蜓——如同有樸素的蝴蝶,也有豔麗的蛾子,但它們不一樣。一隻弱不禁風的豆娘,讓我認識到,幫助幼小也並非易事。
我在樓體的牆角看到它:一隻豆娘,大約兩釐米長。它不斷彎曲身體,以頭部碰觸尾尖,像是在嘗試瑜伽動作,又像是模擬一個交配結。蜻蜓或豆娘交配時,雌雄會完美配合,銜接身體,兩兩組成一個“心”形的閉合環。不過,這回它所締結的,是與死神的婚姻。這隻豆娘被蛛絲捕獲了,它幾條黃綠色的腿細如絲線,也被纏縛。
我把豆娘從繚繞的蛛網上摘取下來,除去它軀幹和胸腔之間的絲縷。蜻蜓的後翅寬於前翅,而豆娘有四片幾乎同等大小的複製般的翅膀,停棲時它們疊合在一起,看似一個單片,像刃口斜切入案板的刀那樣聳立在背部。豆娘飛行時,翅膀分成左右兩組,猶如音樂指揮那樣在空氣中美妙划動。被解救下來的豆娘,翅膀近乎透明,但它不飛。
我發現,它的兩隻右翅沒問題,它左側的兩隻翅膀牢牢貼合,末端那裡更是有個小米粒大的白斑,像鈣化或者膠粘似的。我試了試,根本分不開。豆娘的身體和腿都纖細得失真,它的翅膀太薄太透太弱,精緻而如若無物。我的手太笨,它的翅膀太靈巧,我難以處理兩片已經融合為一體的翅膀。稍不小心,一場拯救,就容易變成即刻的殺戮。避開它的指爪,我用一根食指抵住它的袖珍頭顱,用另一根食指尖觸及傷翅的末端,極其小心地控制著位置、方向和推力,終於使嚴密閉合的膜翅裂開細如髮絲的一線。我重複這個動作,依然無法分離黏合的末端。
我從隨身背裡找到一袋零食,因為裡面裝的豆粒富含油脂,所以這類食物的包裝會在內層使用鋁箔,這種材質有種超出預期的硬挺。撕開包裝,取邊角,用單層。鋁箔反射出銀光,這角斜裁的薄片就像把簡易手術刀——我終於把它探入豆娘兩翼的一線縫隙中。對我這樣眼花手笨的人來說,分開豆娘又薄又小又透明到幾乎不存在的膜翅,這項工作堪比一個鐘錶匠學徒修理複雜精密的發條,甚至更難。因為袖珍金屬元件具有足夠的硬度,豆娘細弱得讓人不敢設想它針尖般的心臟。響晴的正午,陽光灼烈,我花了遠比預期更長的時間,在懷疑到絕望的心理中,終於使這隻豆娘獲得新生。
我由此猜測,那法力無邊的造物之神,也許他解救每個陷入困境的掙扎中的生命,都絕非易事;也許並非因他無能,一切,乃是由於我們的脆弱。
5
昆蟲環繞著我們,豐富、喧嚷又無聲。隨時隨地,它們在我們身邊,密集地,愛恨生死。我喜歡觀察各種昆蟲,它們呈現著一個袖珍而真實的魔法世界。
比如螳螂。螳螂抬起前肢,像太極高手那樣拉開攪動風雲的陣勢。很多螳螂是擬態高手,擅長易容,穿著華麗的戲裝,煞有介事地虛張聲勢——其實,螳螂是個狠角色,爪子堪比猛禽,何況部分雌螳螂還有殺夫的嗜好。
比如獨角仙。獨角仙舉著鹿叉般的角,它的個頭巨大,殼體厚且油亮,走起來的步伐沉重,孔武有力,簡直相當於昆蟲裡的公牛。它的肌肉太有力了,竟然能夠支撐這麼沉笨的身體從容起飛。
只是蜣螂,在我視力下降的情況下,它的只形看起來就像螳螂,它的外形看起來就像小體的獨角仙——其實,它都不是。奇怪,我總是難以清晰記住蜣螂的樣子,它長得太混沌了。也許作為人類的我們太過勢利,因蜣螂的食性而忽略它,把它僅僅當作用來嘲笑的符號。
學名蜣螂,聽起來似乎有幾分書卷的雅氣,但它俗稱屎殼郎。我覺得它的存在,體現出上帝的幽默感。有一次,我看一部關於環境保護的科普紀錄片,注意到一些有趣的畫面。蜣螂把人類觀念裡骯髒不堪的屈辱工作,當作畢生熱愛的事業。在搬運糞球的過程中,我發現蜣螂有些似無必要的動作,滑稽而令人迷惑。比如,它一邊滾著糞球,一邊忽然向上伸起空置的前肢,不知這個舉重運動員是在熱身、休息,還是慶祝。它間或表演體操,向前推動糞團時,突然倒置身體,改為蹬踏——雖然蜣螂缺少表情豐富的五官,但它依然像個登臺的雜技演員一樣,傳遞著興高采烈的表演氛圍。
蜣螂如獲至寶,它抱住糞團的狂喜,與女明星戴上珠寶的陶醉,別無二致。蜣螂滾動屎球的喜悅,與人類獲得財富的興奮,彷彿強度等值。它是如此的知足、歡樂與感恩,即使得到的只是一團骯髒的穢物,一粒散發臭味的屎球。除了標明領地的作用,多數動物往往會嫌棄自己的排洩物,儘量讓屎尿遠離自己的巢穴和活動區域。弄蝶在毛毛蟲形態的時候,可以把糞球射到一米五的空中,相當於一個成年人把屎甩到七十多米的高空。即使不嫌棄自己的排洩物,也會厭惡別人的,只有摯愛者才能克服障礙。比如羚羊的母親會吃掉自己孩子的屎尿,這樣做是為了防止給飢餓的肉食動物留下追蹤的氣味;一旦孩子長大,母親就不再這麼做,因為它的孩子已經能夠透過快速奔跑的方式來保護自己了。然而,蜣螂,小而密佈世界的大自然清道夫,它竟憑本性做到了觀念上的平等與行為上的犧牲。它的行為,體現了某種超越物種和立場的公正,曲折的公正,易被忽略的公正……竟然,近乎造物主那種道德意義之外的冷淡到寧靜的公正。
說不出是令人啼笑皆非還是肅然起敬,這卑微又神聖的蜣螂,全世界據說有兩萬多種,分佈在南極洲以外的任何一塊大陸。
……未完,原文見《北京文學》(精彩閱讀)2021年第4期
創作談
鳥羽、魚鱗和獸皮
周曉楓
我的散文集前面兩本名為《巨鯨歌唱》和《有如候鳥》,分別獲得魯迅文學獎和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當2021年準備出版新的散文集,我貪婪地想延續某種好運。突然發現,巨鯨是在海洋裡,候鳥是在天空裡……它們湊巧完成呼應。那就還要取四個字的題目,寫陸地上的走獸,這樣可以湊成我個人的“海陸空三部曲”。
多數時候,我是先有了內容再想標題;這次情況相反,《幻獸之吻》名字在前,然後我才想怎麼去填充。一旦開始,那些關於動物的回憶蜂擁而至。
我的生活相對簡單,沒有那麼多閱歷的積累,所以特別珍惜能夠觸及的素材,哪怕是片段,比如動物題材。我從小迷戀動物,可惜養寵物多以悲劇收場。前幾年,我的一對黑尾土撥鼠左左和右右意外離世——我至今每天都在抖音上花費時間看看別人家的毛孩子。黑尾土撥鼠長相酷似,讓我在錯覺中,感覺左左右右它們還在,而不是埋在我窗前的玉蘭樹下。我一直猶豫要不要養只約克夏犬,可隱痛未消,心懷畏怯;不過,喂喂每天前來報道的流浪貓,也讓我有所慰藉——它們毛絲晶亮,自帶光芒。
為了觀察,我曾經到動物園當過飼養員,也曾前去觀看場面壯闊的動物遷徙。動物所蘊藏的智慧與美,在我看來,就是可以被目睹的奇蹟。僅僅是一隻孔雀開啟尾屏,就讓我感到交響樂般的輝煌;成噸的暴雨傾瀉著,而非洲草原上的角馬們一動不動,等待暴雨之後同樣傾瀉而下的陽光。蜂鳥的心臟只有豆粒大小,鯨魚的心臟大得像輛汽車……這個到處充滿怦怦心跳的世界,是多麼激動人心啊。假如沒有動物,人類就是這個世界的孤兒……不,是棄兒。
連最常見的普通寵物,也令我震撼。一隻小乳貓或小奶狗,很快就能融入人類的家庭生活。換位設想,如果把一個人單獨放在高樓大廈般的生物中間,我們能否迅速建立同樣的信任,能否被巨物託舉半空,而不瑟瑟發抖?動物以非凡的勇氣陪伴著我們,安慰著我們,養育著我們。
是的,從古至今,更多時候是動物養育我們,而不是我們養育它們。從前愛斯基摩人用鳥皮製作一種內衣,在冰屋裡只脫連帽的毛皮外套,裡面這件貼身之物是不脫的。據說,製作這樣一件鳥皮內衣,工藝極其繁複,以至於需要縫上細密的幾千針。縫衣線用馴鹿背骨上多筋的肌腱製成,它們經過風乾和磨平的處理,被扭成一條粗拙的線。優點是遇水膨脹,因此衣縫基本不透水;此外,它們常含有一小層脂肪,沒有食物的極端條件下,人類可以依靠吮吸縫衣線,短暫地延命。
哪怕動物的慷慨,是被人類強制劫掠而造就的美德,我們依然要對動物致以感恩。這種感恩,一方面是物質意義的,一方面是審美意義的。動物為我們提供食物和溫暖,提供知識和審美的教育。它們的美,它們的暴力,它們身上無窮無盡的謎……因為超出想象而幾近幻覺。
周曉楓,散文作家,兒童文學作家。出版有散文集《斑紋一一獸皮上的地圖》《收藏一一時間的魔法書》《你的身體是個仙境》《聾天使》《巨鯨歌唱》《有如候鳥》等,曾獲魯迅文學獎、朱自清散文獎、人民文學獎、十月文學獎、鐘山文學獎、花地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等獎項。出版有童話《小翅膀》《星魚》《你的好心看起來像個壞主意》,曾獲中國好書、桂冠童書、中國童書榜年度最佳童書等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