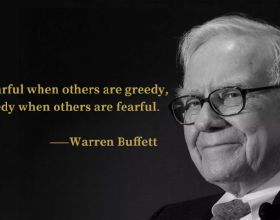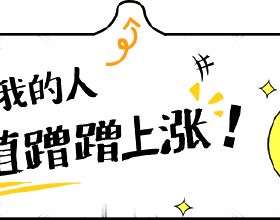韓寒入戲太深,《四海》難免生“寒”
《四海》為家沒有“家”,只有摩托,韓寒喜歡的摩托。
作為正式投放前宣傳賣點的沈騰不是主角,不僅戲份少,戲的分量也輕,明顯比不上男主角阿耀的摩托車;作為頭號主角的劉昊然也不是主角,他完全被摩托車的“光芒”所掩蓋,成為摩托車的配角;作為女主角的劉浩存也不是主角,也完全被摩托車所掩蓋,成為摩托車的配角不說,最後還停格於阿耀的摩托車上。其他的主角、配角,就更不是主角,都是摩托車的附屬品。
因為,韓寒實在太喜歡摩托車了,太酷愛賽車了。於是,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編出了這樣一則故事,而且是散裝故事,最終的結果,就是為他喜歡的摩托車服務。生於摩托車、死於摩托車,成於摩托車、傷於摩托車,歡於摩托車、痛於摩托車,離開摩托車,《四海》就會成為“死海”。用一些地方的土話來說,就是“死蟹(讀嗨)”一隻。
把結構原本就不太完整,故事原本就很散亂,特別是邏輯不夠嚴密的故事,再用摩托車去橫衝直撞,這樣的電影,縱然演員們再賣力,演員的陣容再強大,要想產生良好的效果,也是非常難的。《四海》從原本很受期待,甚至認為票房會僅次於《水門橋》的好影片,掉落到票房第四、第五的位置,豆瓣評分更是隻有5.6分,口碑落水,可能令多數人沒有想到,卻又只能是這樣的結果。
韓寒把自己當成《四海》的主角,導演的個人慾望佔領了所有角色的激情,讓每個演員的戲份,都變成了導演的化身,口碑落水,也就很好理解了。如果此時的《四海》仍然口碑很好,票房很高,就已經不是影片的力量,而是韓寒的個人魅力。而今天的韓寒,早已沒有過去那麼熱門,年輕觀眾們也早已不需要“韓寒式深沉”,他們更希望直接表達感情、直接傳遞情感、直接抒發愛戀。
《四海》為家,需要把“家”刻畫得更精緻、更有情調、更有想象力,而不是被摩托車綁架。即便摩托車是生活的一部分,也只能是配角,而不能凌駕於人之上。《四海》帶給人的,就是摩托車至上,人已經不重要。為了摩托車,可以不顧一切,可以違法,可以負債累累,可以冒著生命危險,可以造假,可以不要自己的生命,最後,讓兩名原本可以過著平淡幸福生活的年輕人,只能在夢裡回想曾經在一起,只能在奈何橋上相會相知。這種為了摩托車而殘忍地將感情、將人性、將道德,甚至將法律都踩在腳下的行為,顯然是很難得到觀眾的共鳴的。
年輕人不易,普通人不易,生活不易,原本是可以很火的話題,也是可以引起共鳴的話題。特別是“外漂”的年輕人,會很容易地投入到角色之中,讓自己成為其中的一員。可是,《四海》沒有,《四海》把戲份全部讓位給了摩托車,就差抬著摩托車飛行,抬著摩托車走街塞巷,抬著摩托車生活。於是,年輕人的不易,普通人的不易,生活的不易,就變成了一個簡單的摩托車玩家,無法讓年輕人、普通人融入其中。《四海》的感染力,也就戛然而止。
今天的人們,尤其是在疫情影響下的人們,對“家”的感覺會更深,更希望感受“家”的溫暖,享受“家”的幸福。不然,不會有那麼多人寧可被隔離也要回“家”,也要把回“家”過年當作最為幸福的事。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四海》不把“家”當作核心來描述和刻畫,不把“家”寫得更溫馨、更浪漫、更具吸引力,而從頭到尾都在寫摩托車,就必然會被拋棄。要不是很多觀眾是衝著沈騰去的,衝著影片投放市場前把沈騰當作賣點的宣傳去的,《四海》的票房會更差。《四海》的票房在快速下滑,印證的也是這種結果。
從充滿期待到大失所望,《四海》也成為今年春節檔一個比較有趣的現象,這也進一步說明,電影市場的開放度已經很高很高,觀眾的欣賞能力已經不只是對個別演員、導演和編劇的崇拜,更希望被影片展示出來的精神力量感染和鼓勵,能夠從影片中汲取精神營養。恰恰是,《四海》在這方面表現得是非常差的。與賈玲導演的《你好,李煥英》相比,韓寒有點不懂生活、不懂觀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