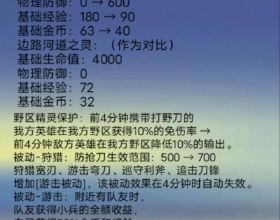南昌起義後,起義軍經過瑞金壬田戰鬥進入瑞金城以後,在瑞金截獲敵人許多檔案,得知敵人錢大鈞、黃紹閎兩部,約計十幾個團的兵力集中在會昌。有這樣大股敵人集中在側背,對於我軍繼續南進自然是十分危險的,我軍隨時可因腹背受敵而致失敗,因此,總指揮部決定:先攻破會昌之敵,再折回瑞金,轉道汀州、上杭,進取廣東潮汕。
部隊繼續分兩路向會昌疾進。十一軍為右縱隊,二十軍為左縱隊。二十軍部隊由我們第三師擔任主攻,由九軍副軍長朱德同志指揮;一、二兩師因剛剛經過壬田戰鬥,留作預備隊。從瑞金到會昌行程八十里,部隊經過一夜急行軍,九月一日拂曉,到達會昌城東北十餘里處的一帶高地上停下來。從這裡直到會昌城邊,是一片連亙不絕的高地,構成了會昌城的天然屏障;敵人派出重兵,扼守著這些山頭。我們的任務就是從這裡發起攻擊。
根據指揮部的命令,我們六團在從河邊到山腰約兩千米的寬正面展開;在我們的右前方有一座高聳的古塔,那便是我們團與教導團的分界線,他們緊接著第十一軍的右翼,構成了對會昌城的包圍。當時,我在六團任副團長。我們這個團是整個南昌起義軍中最新的一個團隊,它是南昌起義前半個月才建成的。
當時,共產黨幫助二十軍建立了這個學兵團,在大冶附近的石灰窯經過整訓正式建團,之後,即開赴南昌參加了起義。這個團除了黨派來的一些骨幹,絕大部分都是新兵,沒有經受過戰鬥鍛鍊,就是在南昌起義時,也只是擔任警戒,沒有參加什麼戰鬥,現在這支剛剛誕生的軍隊卻要經受這樣一個大戰鬥的洗禮了。
我檢查完陣地,剛返回指揮所,就看見團長傅維鈺同志正在和一位面生的人談話。那個人個子不高,穿身退了色的灰軍裝,著雙草鞋,背頂斗笠,很隨便地站在那裡。經過介紹,原來他就是朱德同志。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朱德同志,在這以前早就聽說過他,知道他是南昌公安局長,又是軍官教育團團長,是個有名的軍事家;這次聽說我們由他指揮,原想他一定是個很威風、很嚴厲的人,誰知卻是這樣穿戴樸素、平易近人。他很熱情地向我打了招呼,問了問部隊情況,便對我們說:“這一仗是很要緊的,不打贏就不能往前走,我們一定要打勝仗才行。這次要我來指揮,可是主要還要靠大家……”他的話講得很慢,還有點客氣,但我們卻都覺得出他是充滿信心的。他講完話,右手隨便向前面一揮說:“走,我們到前面看看去。”我們團部的一些人員跟隨著朱德同志,走上古塔左邊的一個高山,山下面就是敵人了。
這時,晨霧已經散去,太陽昇起很高了,山下的景物清晰地擺在眼前。只見山腳下的平壩子裡,敵人東一堆,西一簇,看樣子正在集合。朱德同志觀察了一下,轉回頭對傅團長說:“這麼好的目標,為什麼不打呀?”這旬問話等於向我們下達了戰鬥命令。
團長向我望了一眼,我立即傳下命令,讓團的重機槍連上來,並命令各營準備投入戰鬥。重機槍連上來了,六挺重機槍架在山頂上,一聲令下,機槍“嗒嗒嗒”向密集的敵人開火了。敵人遭到這突然的打擊,一下子亂了營,扔下滿地的屍體四散奔逃,我們部隊乘勢向左延伸追擊。
戰鬥就這樣開始了。遭到打擊的敵人很快就集合起來,配合著後面增援來的部隊,向我們的陣地反撲。我們各營的部隊當即迎頭擋住,一場激烈的爭奪戰便在這重重的山頭上展開。
因為右翼十一軍還沒有打響,戰鬥一開始,敵人的壓力便全部集中到我們三師這方面來。敵人整連整營地向我們陣地衝鋒,打垮一批,又上來一批。我真想不到,原來讓我一直擔心的、我們這個新建的團隊作戰竟是這樣的勇敢,戰士們都頑強地堅持,和一次次衝上來的敵人死拼。但是,畢竟敵人太多了,特別是因為我們部隊當時都沒有配備構築工事的器具,連把鐵鍁都沒有,不能構築工事,只好在平地上臥倒射擊,戰士們傷亡很大。我們把僅有的一點預備隊都拿上去了,連團部甚至師部的人員都投入了戰鬥。營裡一次次派人來請求增援,我們只好回答:“沒有兵。”
這時,朱德同志還在我們陣地上,我們對當時的情勢都有些發急,忙向他請示。朱德同志正忙著指揮教導團和我們團進行戰鬥。當我們向他談起團的傷亡情形和各營的要求時,他慢慢地看了我們一會兒,搖了搖頭說:“教導團也是一樣,打得也很苦。可是,我們這邊吃力些,把敵人背到身上,十一軍那邊就好辦了!”這句話使我們一下子醒悟過來,是啊,戰鬥是一個整體,我們應該為整個戰鬥著想啊!我們按照朱副軍長的指示,繼續動員和組織部隊頑強抗擊。
這時已近中午,八月底正是最熱的時候,太陽曬得人簡直喘不過氣來。敵人仍在不停地進攻,我們的處境更困難了。師參謀處長袁策夷(又名袁仲賢)同志負傷了;師軍需主任蔣作舟同志犧牲了;營連幹部傷亡也不小,一營陳賡營長就在這時負了重傷。前沿有幾處陣地已經被敵人攻佔了。正在這時,一股敵人突破了前沿,徑直向指揮所猛衝過來,要調部隊已經來不及了,形勢十分危急。
我和傅維鈺同志一邊組織指揮所的人員抵抗,一邊十分擔心朱副軍長的安全,連忙走到他的身邊。傅團長說:“副軍長,敵人衝過來了,請你轉移一下吧!”“不要慌嘛!”朱副軍長還是那麼不慌不忙地說,“來了就打一下子!”說著,他就走到一位犧牲的戰士身邊,撿起一支步槍,從容地拉開槍栓向彈槽裡看了一眼,“刷”地推上一發子彈,臥倒身,就向敵人射擊起來。我們都被他這鎮定自若的態度所感染,覺得心裡頓時安定了許多,而且知道勸說也無用,便都臥倒在他的身邊射擊起來。
敵人越衝越近,子彈打在我們近旁的山石上,四處亂迸,濺起一股股煙塵。我一面打,一面不斷看朱德同志,只見他像個老戰士一樣,從容不迫地一槍一槍在打,子彈打完了,他就爬到烈士身邊,從子彈袋裡抽出幾排子彈,裝進槍裡再打。經過我們這一通打,敵人的來勢被壓制住了;接著各連從側面對我們展開支援,衝到指揮所跟前的這股敵人終於被打退了。
正在這時,通訊員帶來了訊息:師部經理處長郭德紹同志在教導團陣地上犧牲了;教導團方面打得也十分艱苦,有的單位因為支援不住,被迫後撤了。朱軍長聽完了報告,把手裡的步槍一扔,搓著手上的汗漬,對我和傅團長說:“好,我到教導團那邊去看看。十一軍很快就要打響了,你們這裡要全力堅持住!”說完,他又交代了一些堅守陣地的注意事項,便弓著身子冒著密密的彈雨向教導團陣地跑去。
朱軍長走後不久,左翼又有一大股敵人衝向我們陣地。因為這次敵人的兵力過多,又來得突然,前沿的部隊大概傷亡過大,零落地響了幾槍便沉寂了。敵人大搖大擺地向指揮所陣地衝來。我打了幾槍,突然發現子彈沒有了。我連忙招呼傅維鈺同志:“壞了,沒有子彈了!”一看,他正在那裡向槍上裝刺刀,看來子彈也光了。他匆忙地向我擺擺手,壓低聲音向周圍的幾個同志下命令:“不要亂動!準備好,敵人上來了就拼刺刀!”只有這樣了!我把刺刀上上,緊握著槍托,向敵人衝來的方向注視著。
只見一隊敵兵正向我們走來。因為我們這裡已經停止了射擊,他們都挺直了腰板,走得很慢。敵兵越來越近,看得更清了,走在頭裡的是一個軍官模樣的人,握著駁殼槍,在離我約三四十步遠的地方停下來,把手罩在眼上四下看了一看說:“這是我們自己人嘛!”說完,競扭轉身向右後方走了。我緊張地目送這夥敵兵走遠了,才鬆了一口氣,不由得暗暗好笑,原來當時我們的軍裝和敵人一樣,是一色的灰軍裝,我們這些軍官身上都還扎著武裝帶。這身軍裝把敵人迷惑了。
敵人這愚蠢的舉動,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發。我和團長簡單交談了幾句,決定趁這個機會整理一下部隊,調整一下彈藥。我們團的傷亡的確很重,當我們把四散在這長達兩千米的陣地上的戰士們集合起來一看,活著的不到半數了。同志們一個個疲憊不堪但情緒卻都仍然很好。我們把部隊整理好,已是下午一點多鐘了。
我們剛要重新區分戰鬥任務,突然一陣激烈的槍炮聲在敵人的背後爆響起來——十一軍的部隊打上了!這個打擊對於敵人是這樣突然。被我們吸引過來的敵人迅速將兵力轉向後方,我們陣地前面,頓時呈現出一片混亂。正在這時,接到朱軍長的命令:向敵人出擊!敵人潰退了,我們尾隨著潰亂的敵人,向會昌城衝去。會昌戰鬥和壬田戰鬥兩役,起義軍共殲滅錢大鈞部六千人,繳獲槍支兩千五百餘支(挺)。
起義軍取得了勝利。而朱副軍長在戰鬥中那種臨危不懼、鎮定自若的大將風範,更是給我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回憶!
李奇中(1901—1989),又名奇忠,湖南資興人;父親從教,有薄田40餘畝。資興東鄉高等小學、湖南省立第三中學、長沙廣雅英數專門學校畢業。湖南公立工業專門學校修業年半,中央訓練團黨政班第八期、陸軍大學特別班第二期畢業。
1924年春由湖南省出席國民黨一大代表林祖涵(林伯渠)、鄒永成保薦投考黃埔軍校。同年5月到廣州,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第二隊學習。
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黃埔軍校第三、四期區隊附,黨軍第一旅連指導員、第三團黨代表辦公室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九軍第三師少校營附。
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任第二十軍第三師五團團副,隨軍南下參加會昌戰鬥,潮汕失利後隨朱德等轉戰贛南,大庾整編時任營長兼教導大隊大隊長,後參加湘南起義。
1928年春,所率湖南資興農民武裝改編為工農革命軍資興獨立團,任團長。同年5月任紅軍第四軍第十二師三十六團團長,不久因戰事失利,部隊潰散,於1929年脫離中共組織關係;後任廬山中央軍官訓練團教官,軍訓部上校參謀。
1937年8月畢業於陸軍大學特別班第二期,任軍訓部兵役研究班少將副主任;1948年任第十六綏靖區(咸陽)少將副司令。
1949年後,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專員,著有《黃埔精神永存》、《棉湖戰役一鱗半爪》、《會昌城邊》、《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等;1950年任政務院參事,1954年任國務院參事;1986年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1989年9月28日在北京逝世,終年8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