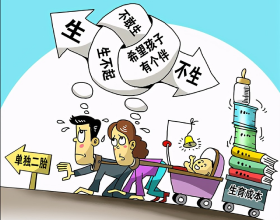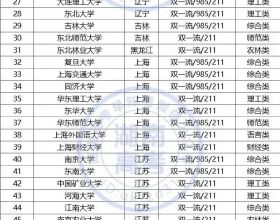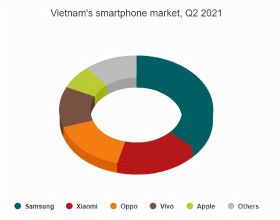隨看隨想
休謨的《人性論》涉及人性方方面面複雜的情況,選文談論的是想象對情感的影響。休謨告訴我們,一般的觀念會影響想象,讓想象模糊,從而使情感不會生起波瀾,進而影響判斷。生動具體的想象則會引起生動的情感。在教育中,大道理為什麼常常沒有效果,恐怕也是因為這個吧。(楊贏)
想象和感情有一種密切的結合,任何影響想象的東西,對感情總不能是完全無關的:這一點是可以注意的。每當我們的禍福觀念獲得一種新的活潑性時,情感就變得更加猛烈,並且隨著想象的各種變化而變化。這種情形是否由於上述“任何伴隨的情緒都容易轉入於主導的情感”的那個原則而來,我將不加斷定。我們有許多例子可以證實想象對情感的這種影響,這對於我現在的目的來說,就已經夠了。
我們所熟悉的任何快樂,比起我們雖認為是高一級的、但完全不知其本性的其他任何快樂來,更能影響我們。對於前者,我們能夠形成一個具體而確定的觀念;對於後者,我們只是在一般的快樂概念下加以想象;我們的任何觀念越是一般的和普遍的,它對想象的影響便一定就越小。一個一般觀念,雖然只是在某種觀點下被考慮的一個特殊觀念,可是通常是較為模糊的;這是因為我們用以表象一個一般觀念的特殊觀念,永不是固定的或確定的,而是容易被其他同樣地能夠加以表象的特殊觀念所代替的。
希臘史中有一段著名的史實,可以說明我們現在的目的。泰米托克里斯向雅典人說,他擬就一個計劃,那個計劃對公眾非常有利,但是他如果把這個計劃告訴他們,那就必然要破壞那個計劃的執行,因為那個計劃的成功完全依靠於它的秘密執行。雅典人不授予他以便宜行事的全權,而卻命令他把他的計劃告訴阿雷司提狄斯,他們完全信賴阿雷司提狄斯的機智,並且決心盲目地遵從他的意見。泰米托克里斯的計劃是秘密地縱火燒燬結集在鄰港中的希臘各邦全部艦隊,這個艦隊一經消滅,就會使雅典人稱霸海上,沒有敵手。阿雷司提狄斯返回大會,並對他們說,泰米托克里斯的計劃是最為有利的,但同時也是最為不義的:人民一聽這話就一致否決了那個計劃。
一位已故的著名歷史家非常讚美古史中的這一段史實,以為是極少遇到的一段獨特的記載。他說,這裡,他們不是哲學家,哲學家們是容易在他們的學院中確立最精美的準則和最崇高的道德規則,並且斷定利益是不應該先於正義的。這裡是全體人民對於向他們所提出的提議都感到關心,他們認為那個提議對於公益有重大的關係,可是他們卻僅僅由於它違反正義而毫不遲疑地一致予以否決了。在我看來,我看不到雅典人這次舉動有什麼奇特之點。使哲學家們易於建立這些崇高準則的那些理由,同樣也趨向於部分地減少了希臘人那種行為的美德。哲學家們從不在利益與正直之間有所權衡,因為他們的判斷是一般的,他們的情感和想象都不關心於物件。在現在的情形下,利益雖然對雅典人是直接的,可是因為它只是在一般的利益概念下被認知的,而並不藉著任何特殊的觀念被想到的,所以這種利益對於他們想象的影響必然沒有那麼大,因而也不會成為那麼猛烈的誘惑,就像他們先已知道它的一切情況時那樣。否則我們難以設想,那樣一批正像人們通常那樣地是不公正而暴烈的全體人民如何竟會一致堅持正義,而拋棄任何重大的利益。
任何新近享受而記憶猶新的快樂,比起痕跡雕殘、幾乎消滅的另外一種快樂,在意志上的作用要較為猛烈。這種情形的發生,豈不是因為在第一種情形下,記憶幫助想象,並給予它的概念一種附加的強力和活力麼?關於過去快樂的意象如果是強烈和猛烈的,它就把這些性質加於將來的快樂觀念上,因為將來的快樂是由類似關係與過去的快樂聯絡起來的。
一個適合於我們生活方式的快樂比起對我們的生活方式是陌生的快樂來,更能刺激起我們的慾望和愛好。這個現象可以由同一原則加以說明。
最能把任何情感灌注於心靈中的,就是雄辯,雄辯能夠以最強烈的和最生動的色彩把物件表象出來。我們自己也可以承認那樣一個物件是有價值的,那樣一個物件是可憎的;但是在一位演說家刺激起想象並給這些觀念增添力量之前,這些觀念對於意志或感情也許只有一種微弱的影響。
但是雄辯並非總是必需的。別人的單純意見,尤其是在情感增添它的勢力時,會使一個關於禍福的觀念對我們發生影響,那種影響在其他情形下是會完全被忽略掉的。這是發生於同情或傳導原則;而同情正如我前面所說,只是一個觀念借想象之力向一個印象的轉化。
值得注意的是:生動的情感通常伴隨著生動的想象。在這一方面,正像在其他方面一樣,情感的力量一方面決定於物件的本性或情況,一方面也決定於人的性情。
我已經說過,信念只是與現前印象相關的生動的觀念。這種活躍性對於刺激我們的全部情感,不論平靜的或猛烈的,都是一個必要的條件;至於想象的單純虛構,則對於兩者並沒有任何重大影響。虛構過於微弱,不能把握心靈,或引起任何情緒。
(選自休謨《人性論》,關文運譯,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
《中國教師報》2021年11月10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