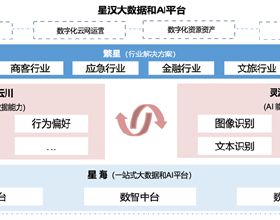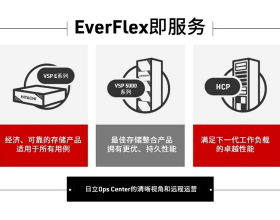數字鴻溝是指現代資訊工具擁有者與未擁有者之間,在資訊可及性上存在巨大差異,具體表現為資訊科技帶來的益處在社會中的不平均分配。這一概念首先出現於1995年的美國,此後不久傳播到歐洲及世界其他地區。到2000年,學界就數字鴻溝的具體概念及涵蓋的相關問題基本達成共識。近年來,數字技術本身的發展及其對社會的價值和影響成為各界共同關注的重大議題,相關討論不斷深入,相關學術研究的視角和方法也日益豐富多樣。數字鴻溝一直是學界頗為關注的問題,特別是針對弱勢群體如何跨越數字鴻溝的問題,各國政府紛紛進行了政策嘗試。
數字鴻溝研究逐級深入
據荷蘭特文特大學傳播學系榮休教授簡·凡·迪克(Jan A. G. M. Van Dijk)介紹,數字鴻溝及相關研究可分為三個層面,對應三個時期。
第一個是物理訪問層面,從1995年至2003年。1995年,美國《洛杉磯時報》首次使用“數字鴻溝”一詞。隨後,美國國家電信和資訊管理局釋出報告《“漏網之魚”:針對美國農村和城市中資訊窮人的一項調查》,描述了美國農村和主要城市中無法享受到國家資訊基礎設施的人群特徵,包括低收入家庭、原住民和少數族裔、受教育程度較低者。報告中多次提及“數字鴻溝”,讓這一概念在媒體和美國政界流行起來。2001年,英國政治學家皮帕·諾里斯(Pippa Norris)出版的《數字鴻溝:世界範圍內的公民參與、資訊貧窮與網際網路》一書,成為首部被經常引用的關於數字鴻溝的學術著作。諾里斯主要討論了數字鴻溝的物理訪問層面,即是否擁有計算機、是否可以接入網際網路,並區分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全球鴻溝、一國內部富人與窮人之間的社會鴻溝、是否將網際網路資源用於社群參與的民主鴻溝。
1995—2001年,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的計算機擁有率和網際網路接入率大幅上升,人們對新的資訊通訊技術總體上抱有積極樂觀態度。但在2001年前後開始出現另一種聲音。有學者提出,數字鴻溝並不存在,這一概念本身就是偽命題。不少民眾也認為,數字裝置和服務與廣播、電視、電話等一樣,也會出現“涓滴效應”,最終會普及每一個人。2000—2005年,關於數字鴻溝的研究成果發表數量達到高峰。這些研究和討論由經濟學家、電信學研究人員、政策制定者或商業領導人主導,而且這些主導者幾乎都是美國人。他們持技術決定論觀點,認為新技術的傳播充滿機遇且不可避免,市場力量被啟動後,數字裝置和服務將會全面普及。
第二個是技能和使用層面,從2004年起延續至今。這一時期,學者和政策制定者開始跨出物理訪問的討論範疇,社會科學家首先提出“數字鴻溝是一個複雜的動態現象”。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社會學教授保羅·阿特維爾(Paul Attewell)、瑞士蘇黎世大學網際網路使用與社會研究教授埃斯特·哈吉泰(Eszter Hargittai)等人強調了資訊科技使用和數字素養的不平等。他們的核心觀點是:如果沒有必要的技能、知識、對有效使用的支援,擁有物理訪問是無用的。數字鴻溝問題首先是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問題,而非技術問題。
這一時期,計算機體積越來越小、運算速度越來越快、價格越來越低,網際網路接入率和計算機購買量迅速上升。2004—2014年,網際網路使用者在世界總人口中的佔比從不足15%上升至接近45%。2004年以來,社交媒體和智慧手機行業蓬勃發展,極大地改善了使用者體驗。21世紀第一個十年,網際網路成為發達國家70%以上人口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過,在發展中國家,接入並使用網際網路的人口比例遠低於發達國家。各國政府機構和教育機構逐漸意識到,只有讓網際網路新使用者獲得技能和相關應用程式,才能支援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
因此,隨著網際網路的快速普及,數字鴻溝研究的焦點轉向新使用者技能,研究範圍大幅擴充套件,並將機會和不平等話題納入進來。2004年以來,“數字鴻溝”一詞在學術出版物中越來越少見,關鍵詞轉變為“網際網路/社交媒體使用”“數字/資訊素養”“數字技能”等有關機會、不平等和應用的概念。2004—2012年,關於數字素養和網際網路使用型別學的新的概念框架和操作性定義不斷湧現,一些研究人員開始在實驗室、田野實驗和調查中測試數字技能。這個階段數字鴻溝研究的另一個焦點是使用者群體,許多學者注意到與知識鴻溝相似的“使用鴻溝”開始出現——一些人主要使用有助於其獲取資訊、接受教育或增強職業競爭力的網際網路產品,另一些人則主要使用娛樂以及簡單的商業和交際用途的網際網路產品。2004年以來,大部分數字鴻溝研究聚焦於計算機和網際網路使用的差異和不平等。這些研究雖然仍以美國為主,但英國、荷蘭、西班牙、巴西、智利、墨西哥、韓國、新加坡、中國的研究更加豐富並受到關注,說明這一領域變得日益國際化。
第三個是結果層面,從2012年延續至今。隨著計算機和網際網路的普及,一些學者和政策制定者開始思考數字鴻溝對公民、機構和社會的影響。2012年,西班牙馬德里自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克里斯托巴爾·託雷斯·阿爾貝羅(Cristóbal Torres Albero)和馬德里康普頓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講師何塞·曼努埃爾·羅布雷斯·莫拉萊斯(José Manuel Robles Morales)開展了一項網際網路訪問和使用調查並提出,未接入網際網路且不具備必要技能的人將無法受益於越來越多的無線下替代品的網路服務。同年,簡·凡·迪克和荷蘭特文特大學傳播學教授亞歷山大·凡·德爾森(Alexander J. A. M. Van Deursen)調查並發現,數字技能缺乏和數字技術故障導致荷蘭勞動者生產率降低。同時,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年輕人受益於網際網路的程度遠高於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老年人。
過去5年裡,網際網路及終端裝置進一步普及。“數字落後者”在發達國家人口中佔比為10%—33%,但在發展中國家仍高達50%—90%。研究人員和政策制定者都開始關注網際網路和數字媒體使用的結果。有人對數字鴻溝的特殊性發出疑問——畢竟在每個時代都有新的技術問世。在簡·凡·迪克看來,新興資訊通訊技術的訪問和使用比印刷媒體、廣播、電視、電話更重要,因為前者是通用型技術。傳統技術雖然對知識獲取、娛樂、通訊起著重要作用,但網際網路和數字媒體是當代社會中每個人在扮演任何角色時都需要的。數字鴻溝影響著個體在教育、工作、市場、社群、政治和文化等領域的參與度,決定著個體是融入社會還是被排除在外。
批判性資料研究興起
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和應用加速,大資料、人工智慧技術迅猛發展,物聯網快速興起。網際網路和資料對社會的作用和影響與日俱增,許多重大問題隨之產生。例如,大規模研究資料將幫助我們創造更好的工具、服務和公共物品,還是掀起隱私侵犯和侵入性市場營銷的新浪潮?資料分析學是否有助於理解網路社群和政治運動,是否將改變我們研究人類交際和文化的方式?於是,批判性資料研究領域應運而生。
2012年,美國微軟研究院研究員達納·博伊德(Danah Boyd)和高階首席研究員凱特·克勞福德(Kate Crawford)發表文章《大資料的批判性問題》稱,大資料的崛起既是技術現象,也是社會現象,因此有必要批判性地質疑相關假設和偏見。她們將大資料視為一個以技術、分析、神話的相互作用為基礎的文化、技術和學術現象。技術指的是將計算能力和演算法準確性最大化,以收集、分析、聯絡和比較大型資料組;分析指的是基於大型資料組來識別模式,以提出經濟、社會、技術和法律規範;神話指的是大型資料組提供了更高階的智慧和知識形式,由此產生以往不可能獲得的見解,並帶有真理性、客觀性、準確性的光環。博伊德和克勞福德提出了六個論點,以期激發各領域關於大資料的討論:大資料改變了知識的定義;宣稱大資料絕對客觀、準確具有誤導性;大資料不總是更好的資料;如果脫離背景,大資料將失去意義;能夠獲取不意味著符合倫理;對大資料的有限訪問造就了新的數字鴻溝。
《大資料的批判性問題》激起了學術界對批判性資料研究的興趣,首次使用“批判性資料研究”這一術語的是美國霍夫斯特拉大學全球研究與地理學助理教授克雷格·M.道爾頓(Craig M. Dalton)和美國華盛頓大學塔科馬校區城市研究助理教授吉姆·撒切爾(Jim Thatcher)。他們在2014年發表的文章《批判性資料研究是什麼以及我們為什麼關心它?》中提出若干關鍵論點,以推動對新的資料制度的全面批判。
第一,必須將大資料置於時間和空間當中。19世紀的統計製圖、社會物理學,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地理學計量革命、基於地理人口細分的市場營銷以及資訊科技產業的盛衰迴圈,都為大資料時代的到來創造了條件。如今,大資料嵌入社會過程中,催生了企業、政府、公民之間的、新的權力幾何學。我們必須提問:資料是誰的?資料收集依據何種規範?目的是什麼?
第二,技術永遠不像看起來那樣中立。在創造和解讀大資料的過程中,大資料技術永遠與文化環境相互決定。對大資料的工具性審視,將導致人們忽視大資料技術產生的根本性的認識論影響。我們必須提問:被量化意味著什麼?大資料作為一種技術形式,對我們的文化和生活帶來什麼樣的可能性和約束?
第三,大資料不能決定社會形態。技術變革與社會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大資料在社會變化中的作用遠不是資料分析或對社會建模這麼簡單。技術的創新、生產、應用普及發生在充斥著權力、經濟、身份、偏見等元素的社會背景下,並反映社會背景。一種技術不可能脫離其背景單獨起作用,更不能決定社會形態。
第四,資料從來不是未加工的。對一切資料的生產和解讀,都是社會實踐的結果。每個資料模型對資訊編碼和建立結構的方式,都遵循了研發人員的設想。哪些資訊被量化、儲存、分類?哪些被丟棄?任何資料組都是對世界的有限表現,這樣理解資料才能使其揭示出某些有意義的規律。
第五,“大”不意味著一切。大資料分析不可能回答所有問題,因此它不能替代更加成熟的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在定性研究中,科研人員透過直接詢問參與者的個人感受和動機,得到關於參與者立場的深度、細節化資訊。在田野研究中,科研人員親身體驗一個地方、一種背景,這些都是大資料難以提供的。此外,關聯性與因果性之間的區別、資料組的價值等問題在大資料時代依然存在。將大資料與“小資料”及其他已有的研究途徑結合起來協調使用,能夠在研究話題、方法、概念、意義等方面開闢新的可能性。
2016年,美國賽吉出版公司旗下期刊《大資料與社會》出版《批判性資料研究》專刊,多國學者從哲學、治理、科研倫理、金融市場、農業、發展和援助等角度探討了資料與整個社會以及個人日常生活之間的相互作用。他們表示,批判性資料研究為人們提供了必要的工具,人們可以運用這些工具提升自身的數字素養,併為資料公正作出努力。批判性資料研究還應鼓勵人們在共同利益框架和社會背景下思考資料科學。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王悠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