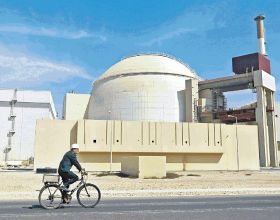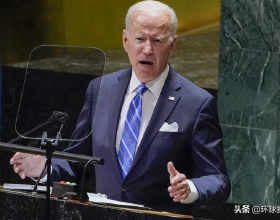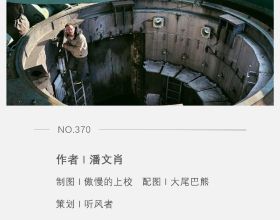黃河,九曲迴盪,穿越大半個華夏大地,所經之處,荒原染綠色,貧瘠變沃土,溝壑映日月;擇水而居的人們,沿著黃河兩岸建起了一個個村莊,一座座城郭。黃河,以甘露般淡黃色乳汁,滋潤了華夏子孫,給予炎黃兒女黃面板黑頭髮的民族基因……
黃河向東我們向西,懷著朝聖般的心情,尋找黃河——母親河的源頭。
文成公主的寶鏡化為日月山
日月山,傳說著美麗故事的山。
我們來到青海湟源縣,來到了日月山。正值初夏,山下一邊是阡陌良田,滿地的青稞已經揚花,那白色花兒如米粒般,一派江南風光;一邊是遼闊望不到頭的茵茵牧場,一幅塞外景色;爬到山中腰,山體的肋骨呈現出紫紅色,越往山上走著色越濃越厚越重,“遠看如噴火,近看如染血”——這由第三紀紫色砂岩構成的日月山,也叫赤嶺。到了山頂,天地蒼茫一片,雪將日月山裝扮成潔白的世界。
遙想當年,大唐文成公主,歷經千萬裡來到這裡,回首不見長安,幽思之情油然而生,忍不住取出日月寶鏡拋下,鏡摔成兩半,落東為日,落西為月,兩山隔空相望,同心一意。文成公主造就的日月山,成為中華多民族血脈相連親如兄弟的象徵。而文成公主由此便去吐谷渾,再往前走就是黃河源頭的柏海,她的白馬王子松贊干布已經率眾在此迎接她。
中華文明深深紮根黃河,比唐代更悠久。古老的《山海經》稱黃河為“河水”,《水經注》稱“上河”,《漢書》稱“中國河”,《尚書》稱“九河”,《史記》稱“大河”,戰國末期,黃河已有“濁河”之稱,到西漢,黃河更是泥沙淤積、水患頻繁。後來,“濁河”演變為“黃河”。而西漢時,全國6000萬人口中,約70萬人生活在黃河流域。
對黃河源頭的探尋,很早已經開始。最有名的當是元代都實,他沿黃河追溯,歷時四個月來到黃河源星宿海(當時的“朵甘思西部”)——星星睡覺的地方,頓時被美麗的景色所感動,發現“有泉百餘泓,或泉或潦,水沮如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溺,不勝人跡,弗可逼視,履高山下瞰,爛若列星”,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河源考察。此後,清代官吏拉錫尋源寫下“登山之至高者視之,星宿海之源,小泉萬億,不可勝數”。
黃河源頭,廣義上指西藏、青海、甘肅的廣闊山川,無數涓流小溪匯成黃河之源。然而,“黃河之水天上來”,人們追尋黃河第一個成流聖地——正源,那麼就要仰望雪域高原。
黃河,哪一滴水來自細流,哪一滴水來自珠穆朗瑪千年的積雪!
鄂陵湖的悲壯
沿著文成公主走過的“和親之路”,我們來到瑪多縣,夜宿在星宿海旁。
星星睡覺的地方被藏族同胞稱為“錯岔”,就是“花海子”的意思,黃河水流經至此,河面變寬,四處漫淌的河水許是過於留戀這片美麗的土地,留下星羅棋佈大大小小數以百計的沼澤湖泊。晚上,站在高處遠望,如鏡的湖泊熠熠閃光,宛如夜空眨眼的星星。
第二天一早,我們與嚮導兼司機的藏族小夥邊巴一起,趕往鄂陵湖、扎陵湖,向黃河正源——措日尕則山的頂峰出發。這條公路,名叫“察木蘭”,即將擴建完工的柏油路在清晨陽光下閃著鋥亮的光。為修復生態,保護“中華水塔”,三江源國家公園黃河源園區核心地帶的牧民被遷移至別處放牧。所以,一路幾乎看不到犛牛、羊群。行駛在有著地球第三極美譽的青藏高原腹地,綿延逶迤的雪峰從眼前一座連著一座閃過,幽綠的沼澤,飛翔在天空的鳥群,偶爾還能看到奔跑的羚羊……冰川原野湖泊,天水相連——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極致風光,是大自然給予中華民族安身立命的家園。
午後,我們來到鄂陵湖、扎陵湖,這對黃河源頭的姐妹湖。鄂陵湖,藏語“青藍色長湖”,她氣勢浩蕩,海水一樣的湛藍。據說她在每一天不同時刻,色彩會不相同:早晨碧綠,中午淺藍,午後深藍,黃昏又成為一縷鮮紅。只是,我們時間緊,無法靜觀她的五彩斑斕。
扎陵湖又是另一番景色,黃河像一條黃色的絲帶從扎陵湖的湖心穿過,將湖分成兩半,一半清澈碧綠,一半微微發白。
高原人把姐妹湖稱為“聖湖”,每逢新年,很多人都會來到湖邊,用聖湖的水洗一洗,以此祈求新一年的豐收和幸福。然而,就是這聖湖,也曾被屈辱踐踏。
1884年,幾乎在西方艦隊炮擊我福建水師,馬尾海戰爆發的同一時刻,歐洲列強以探險之名,對黃河源進行野蠻的文化侵略,武裝侵犯。他們猖獗地記錄下強盜行徑:在行進途中,看到水鳥大群在湖岸活動,忍不住要打,這回我們趕緊取出霰彈鳥槍,三個人半小時共擊中95只……在美麗的母親河源頭,強盜不僅僅是動物的獵食者,也對高原人進行野蠻凌辱殺戮。
在黃河源區看到這些記錄的文字,我彷彿看到了一把把帶血的刺刀扎入母親的胸膛,我知道了鄂陵湖、扎陵湖為什麼會變成紅色?那可是母親的血滴在源頭,是母親以紅色告訴她的子孫,百年的恥辱莫忘記。
在黃河源頭我聽到了母親的訴說,我聽到黃河在怒吼——
“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黃河在咆哮……”這首誕生於抗日戰爭時期的《保衛黃河》,氣勢如虹,唱出了黃河母親與她億萬兒女的不屈不撓,奮起抗爭精神!
喊一聲黃河
鄂陵湖,一端通向約古宗列曲源頭的曲麻萊縣麻多鄉,一端通向措日尕則山下,那裡就是松贊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的“迎親灘”。我們翻過一個山口,到了茶錯,這是一個很小的湖泊,卻是動物的天堂,成群的鳥或在空中飛翔或憩在岸邊,羚羊悠閒地在湖邊啃著草,清澈的水中魚兒穿梭成行……
充滿無限生機,它們與高原人一起,是黃河源真正的主人。
越往前走,離措日尕則山越近,我們的心如同山頂上飄揚的經幡,難以抑制的激動,隨著風在嘩嘩作響、在陣陣飄舞。走到“迎親灘”,走近金色的多卡寺。松贊干布與文成公主,他們共同“在湖邊栽下了雪域的恩澤之株,閃耀著銀質的光芒,風一樣的頌詞一直書寫到現在。”我們一行向山頂爬去,這裡海拔高度4610米。
黃河,我們來了!
顧不上高原反應,面對約古宗列曲——一汪永不幹涸的泉眼,它不是想象之中的滔滔洪流,而是一股股涓涓細流,我們撲下身體,掬一捧水在手心,感覺到母親的溫暖。在它的四周,散落著無數個美麗的大大小小的湖泊溪流,由於近年來治理力度的不斷加大,黃河源頭的“千湖美景”重現;再極目遠望,北依莽莽崑崙,南靠巍巍唐古拉,西擁茫茫可可西里,東有俊俏巴顏喀拉山;還有天空那似乎觸手可及流動的雲彩,時刻都在變化,千姿百態,宛如仙境……黃河源,被中外科學家譽為“宇宙中的莊嚴幻景”。
在華夏之魂河源牛頭碑前,我們像久別的遊子見到母親,邊巴從懷裡掏出潔白的哈達,弓腰遞給我們。我們雙手接過,轉身面向牛頭碑虔誠地將哈達敬獻。
蒼穹之下,一座青銅澆鑄的碑,豎立在漢白玉基座上。它是黃河源的守護神,護佑著這條融有千年文明的中華母親河;它是黃河魂,是千百年形成的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民族性格;它是中華民族的根,紮根在世界之巔,浸泡於雪域高原的江河湖泊之中,滋養出“天地人和,和諧共生”“美美與共,源遠流長”大美善良的人生理念。
黃河之水天上來!黃河,融匯著華夏民族血脈,容百川納千河,以凝聚起億萬人民堅韌不拔的蓬勃力量,向著東方、向著大海、向著太陽,奔流不息,九曲注海,浩浩蕩蕩,澤被其遠……(郭秋香 江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