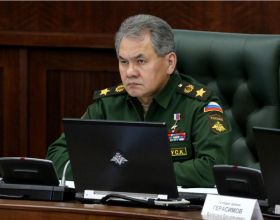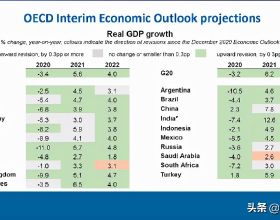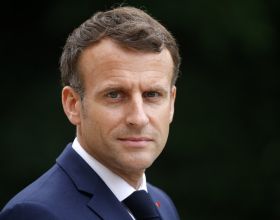春節實在不好玩,除了打撲克還是打撲克。無聊極了,我便邀約自小與我情篤意投的夥伴張勇去逛長山埂,一面還可以在我的母校——發輪中心小學拾得一些已逝的相去甚遠的夢。也許是這幾年疲命於讀書學習之故罷,我是有好久沒到我的難忘的時時縈繞在我夢際的母校去看一看了。
我們出發的時日是初三早晨,這天天氣還不錯,陰晴陰晴的,而且,前兩天泥濘不堪的路已不復存在了,代這以的是不溼不幹踏著人舒爽的路。由於一路上談談笑笑,不知不覺我們就轉悠到兩山之間的大山谷下,這就是我的母校之所在了。
呵,母校是變了不少。新添了許多房屋樓舍。帶著無限的欣喜,我領著張勇來到了曾留下我不少足跡的,在山腳之下的“兵洞”。“兵洞”洞口已長滿蔥蔥郁郁的荒草,看來後來於我的小朋友是不常來拜訪它的,我心裡頓然升起了一種非常遺憾的情思。我的記憶腦海裡時時戀著的兒時的聖地喲,我今天來拜訪你了,撒播過我迷濛愛慾的“兵洞”喲,你還記得我嗎?在我念小學的時候,經常聽一些比我們知曉人事的大朋友講,這“兵洞”在戰爭年代曾住過兵,還說在“兵洞”裡有幾位頗吃了豹子膽的人拾到過槍殼。大凡我們這些新社會的少年兒童們都喜歡聽些關於革命戰爭年代的故事吧,對給我們帶來幸福生活的解放軍們是懷著無比憧憬,無比嚮往之情的。“兵洞”的神秘史給我幼小的孩童的心地裡由然而然的蒙上了一張神秘的紗衣,總想在某個時候揭去這張紗衣,解開“兵洞”之迷。可是,當時學校曾明令禁止過不準鑽“兵洞”,為的是安全起見。然而,好奇和無限神秘的“兵洞”史的天國色彩使我完完全全把這些禁令拋向九霄雲外去了。我是定要去闖一闖的,無論如何。機會竟來了,在一天下午的體育課上,等老師一領完操,讓學生自由活動時,我便招引了幾位小夥伴,弄了幾個淋透煤油的火把,飛快地溜向“兵洞”,合力搬開封著洞口的那塊大石頭,點燃火把,然後風風火火地往下鑽。“兵洞”裡本黑魆魆 的,然而我們所到之處,卻被照得通亮。在“兵洞”裡行走,磕磕絆絆的,我們邁著踉踉蹌蹌的步子,深一腳,淺一腳,行走極困難,稍不留意,頭上就是一塊“青包”。“兵洞”裡初進時很扁,只容一個人側身走,越往下雖是洞口越寬敞了些,但更陰森可怖了,還有一股叫人不好受的溼氣。大家的心緊了,不敢往下走,手裡的火把也快燃盡,而且,下一節課恐怕開始了,大家一合計:出去。於是,我們急急往外狠鑽,待到每個人頭上又新添了好幾個“青包”後,方才看見光亮了。我鑽在大夥前面,很為自己的領先而自豪,可不想,剛往外一探頭,糟糕!校長已挺立洞口了。
“出來!站在這裡。”嚴厲的校長一聲令下,我便乘乘地成了“俘虜”,其他幾個也沮喪著頭被“俘”了。校長把我們領到他的辦公室很受了一頓批評後,把我們交給了正在上課的老師,老師也沒好氣,讓我們站著上了一堂課,不過當時我是心甘情願的。
想到此,我不由得“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張勇不解,問我笑什麼,我說:“我想起了一件有趣的往事。” 說畢,我們離開了“兵洞”,我領著張勇從學校背後橫穿而過,從一條小路抄在了學校裡面,經過一條水溝時,我忽而深有感觸的對張勇說:“你不知道,就是在這兒,我們捉迷藏時,由於不小心,我摔到在這條溝裡,左手肘脫臼,不能動彈了。當時,我的班主任駱月華老師連同幾個同學把我弄到醫院,醫生很費了些勁才把我的手接好,然後他們又扶我回校上課,而上課我的右手又不能執筆,心裡著急死了,便用左手執筆寫字。當時駱月華老師看見了,當即在班上表揚了我,說我‘很有出息。’噯,你看到底我有沒有出息,偌大年齡了,還一事無成。出息在哪兒呢”?我攤開雙手說。“時候尚早嘛,只要你執著地去追求,出頭之日不遠了。”張勇半是奉承地說。
正談話之際,我們來到了我小學念過書的一所給我印象挺深的教室。我們的教室在樓上,樓下是兩塊荒坡。那時,每到植樹季節,學校便號召我們植樹造林,綠化校園。號召一下,班主任老師就吩咐我們每個人獻一棵樹或一株花草,種在這兩塊荒坡上,爾後我們又找了些石頭圍上一圈,就成了現在這樣。
“你看,哦呀,好茂密呀”我驚喜得叫了出來。滿眼的、青翠碧綠、菖蒲、黃花一籠一籠的,濃陰匝地,並上一些藥草,美極了!“呀,你快看,我栽的那棵柳樹已齊樓高了,伸伸展展的,可哪裡會想到,插時還不及我一臂之長呢。”“哎,要是還能在這教室裡哪怕讀一會兒書,那也該多好哇!可是已經是不可能了。”我不無深意地說。回憶往事,我感慨萬千。
我領著張勇,在我的母校走了一遭,每到一處,我都會記起許多,許多。到我們離開母校時,已有人叫吃午飯了,可我還留戀忘返於我的母校——發輪中心小學。
1989年於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