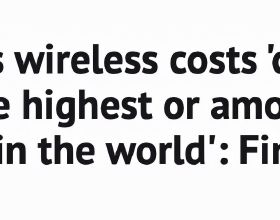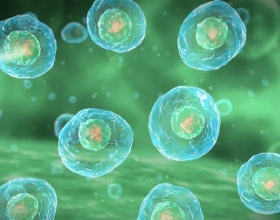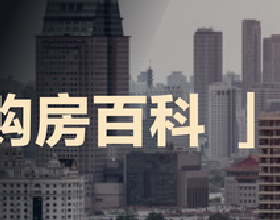至今算來,我離開軍隊已經31年了。現在回過頭來看,由學校到軍隊,再由軍隊到地方,大方向是正確的,也符合事物發展規律。
當年,我們這些從軍者,在部隊能幹多久,能幹到什麼職務?真是無法估測。如果幸運,少數人幹到師團,按服役條例,50至55歲之前就要退休。這個年齡段,正是年富力強、經驗豐富的好時候,如果在能幹事的年齡退下來,閒著無事,還不如去地方上多幹上幾年。有些戰友,有的40歲出頭就從部隊退下來,在家閒得慌,出去找事幹,因為沒有業務,沒有技術,找到物業、保安崗位也幹,之中不乏營團職幹部。
面對現實,我想趁年輕早些去地方吧。但前提是要加強學習,拿到正規大專以上學歷。我高中一畢業就去當兵了,這個高中文憑,是在“文革”中拿到的,沒有真金白銀,含金量低。當時在煙臺一中上學時,連個正規課本都沒有,教材是油印的。上學期間,每年還要拿出幾個月,去學工學農學軍。正值獲取知識的大好時光白白浪費掉了。1977年恢復高考,我認真作了參加高考的準備,但事後聽說,現役軍人不能參加地方高考,讓我求學的心涼了。“文革”結束後,部隊大力開展學習文化活動,我參加了一些學習,但不繫統不正規,一直渴求去正規大學學習。還有,八十年代,部隊一直風傳要恢復授銜,授銜是一種榮譽,一種標誌,一輩子就這麼一次,機會難得。所以,我始終抱有拿到正規學歷和授銜以後,再考慮轉業去地方的想法。
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的。1985年,濟南軍區與山東大學商定,從全軍區部隊中挑選一百名後備幹部,參加成人高考尋取後上山東大學中文系。聽到這個訊息,我十分高興,山東大學是我向往的高等學院,能踏進山大校門,是莫大的期盼。我是幸運者,單位確定讓我去山大學習。1985年,我從分部政治部秘書科副科長崗位上離職,到山東大學中文系學習了兩年。在學校,如飢似渴地學了兩年,許多教授給我們授課,看了不少名著,受益匪淺。
1987年7月畢業後回到分部機關,我努力工作,寫了不少政工材料,有的獲得軍區後勤部獎勵。不久,組織上提升我為分部政治部秘書科科長(副團級)。爾後,中央軍委決定在1988年的10月1日正式實行新的軍銜制。9月14日,上將軍銜的授銜儀式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進行。16日,中將、少將和部分校官的授銜儀式在各軍區分別進行。我也和全軍官兵一樣,更換了新的軍服,肩膀上戴上了新的軍銜肩章,以一個嶄新的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在這次授銜中,按照資歷、職務等條件,我被授予為陸軍中校。
作者於1988年
授銜以後,說實話,我沒有再多的想法了,也不再對自己在軍隊裡作任何打算了。
1988年年底,我調離分部去濟南某單位工作,臨走前向時任分部的一些領導告別,部長、政治部主任等領導,勸說我不要著急走。政委直接了當勸我,馬上會安排我到某團單位任政委,分部管轄近20個團單位,讓我去團單位任正職並不難。但此時我沒有多想什麼,對再上一職也沒有多想。於是,謝謝領導的好意,離開了近20年的萊陽軍營,調到濟南,因為家人在濟南。
雖然離開了萊陽濟南軍區後勤十分部,但畢競在這方熱土上從軍,工作生活近20年,至今,時常想念分部對我的培養教育,感謝幫助過我的領導和戰友們。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性格決定命運,由於有了轉業想法,於是在1990年,我在濟南的一個部隊單位作出了轉業決定,結束軍旅生涯,去地方“闖蕩”了。
1989年,此時,已經在嚮往、期待去地方工作了。當時,我對地方工作,地方單位沒有什麼概念,黨委政府各部門工作、業務、職能等,全然不知。只是聽別人說,進省直單位比市直單位好。當時只抱有一個想法,一定要進省直單位。那個年代,進省直的要求是,軍轉幹部大專以上學歷,年齡不過45歲。當時我學歷夠了,年鈴30多歲,符合條件。那一年,省軍轉辦沒有實行計劃安置,而是採取雙向選擇辦法,讓軍轉幹部自己去找單位,單位認可即成。我帶著在部隊的工作成果,即在部隊寫得一摞材料,找到山東省農業委員會主要負責人,我記得很清楚,他對我說,幹農業要不怕吃苦,要經常下鄉,調研、瞭解情況,當好領導參謀。在省直機關,能寫能說能想能幹才能立住。我向他表示,我當過兵,不怕吃苦,一定努力,好好學習,好好工作。接著,他向我點頭默許。下半年,我接到轉業接受單位通知,到山東省農業委員會報到,由此,我的人生開啟了新的征程。可以說,轉業去地方,也是一個無悔的選擇。
人世演繹到半程,應該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了。
人生後半程,應該是"而今邁步從頭越”,期待著“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在地方工作24年,得到不少有益的收穫。見識長了,眼界開闊了,思維變化了。這麼說吧,一生過來,一半在軍隊,一半在地方,地方上的人生閱歷,部隊是不可比擬的,或說是無法得到的,當然,如果沒有從軍經歷,軍人閱歷也是無法得到的。離開軍隊轉業來到地方,見識了未聞未見的一些東西,人生閱歷彷彿增加了好幾倍。
山東省人民政府
作者1991年冬於省政府大院前
1991年冬季的一天,下了一場大雪,我冒雪來上班,巧遇一位同事在拍雪景,印象中那個年代,冬季大雪並不多見,他熱情地招呼我拍個雪景留念,於是留下了山東省人民政府大院門前的留影。
1990年轉業後,我被分配到山東省農業委員會,就在山東省人民政府大院。當時大院內有省政府辦公廳、計委、經委、人事廳、科技廳等部門。一進大院,就有一種莊重而神秘的感覺,大院內五星紅旗飄揚,大門口武警戰士站崗執勤,進出門要驗查工作證(後來熟了不查了)。大院內有上千人,但有序安靜,大家都在辦公室裡埋頭工作,到了晚上,幾棟辦公樓內燈火通明,許多人挑燈夜戰。有些省長辦公室晚上也有燈光,也在加班。當時省政府有三位副省長,都四十多一點,年輕有為。因為工作,我陪委領導多次去分管農業的省長辦公室,請示彙報工作。省領導待人和藹,才思敏捷,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那年代,大家都在為山東改革開放、經濟社會發展而努力工作,山東九十年代發展較快,GDP一度曾超過廣東、江蘇,我們的工資收入也在不斷增長。所以,在省政府大院裡工作十年,儘管有順利也有挫折,但總體上充滿自信和快樂。
轉業後正式上班前,按照省軍轉辦要求,軍轉幹部要到山東省軍轉培訓中心學習3個月。所學內容,是在地方工作的知識,和軍隊完全不一樣了,讓我產生了新的求知慾望,渴望學到在地方工作的知識。學習期間,結識了不少分配在省委、省政府等有關部門的軍轉幹部,大家喜氣洋洋的,對到新單位工作充滿信心。
學習結束後,我懷著憧憬和期待,來到省農委上班了。這個部門剛剛有省委農工部改為省農委,一百人出頭,三四十多歲以上的幹部居多,我三十多歲,不算老也不年輕,剛開始,二十多歲的大學生有幾個,鳳毛麟角,後來,每年都進來一批大學生,大學生幹部越來越多,後來,除軍轉幹部,基本上都是大學生,幹部隊伍結構發生根本性變化。農委大多人一直從事農業工作,情況熟業務通。農委主要職能是綜合、協調、服務、指導。在農委工作,我們經常和水利廳、林業廳、海洋漁業廳、農機局、畜牧局等單位聯絡,要情況要資料,彙總後上報省委、省政府。在農委,我們的主要工作是圍繞全省農村改革發展,調研情況,出思路出主意出政策,為省委省府領導決策當好參謀。
當時省計劃委員會、省經濟委員會、省農業委員會,號稱“三大委”,曾幾何時,都有副省長兼任這三個委員會主任職務。農委是農口的綜合部門,頂盛期間管理林業、漁業等部門的人財物,“權大位重。”
我到地方後,第一個處室是農委調研室,該處主要職責是負責全省農村改革、農村政策等相關工作,比較宏觀。
作者在農委調研室辦公
和在部隊工作的區別是,工作性質、內容、範圍、層次、思路、眼界完全不一樣了。主任滿腹學問,大筆桿子,寫材料的高手、快手,副主任也很有才氣,寫材料的高手,且硬筆、軟筆寫得很捧。處裡有四位大學生,他們聰明能幹,專業知識強。還有兩位年近60歲的老同志,工作經驗相當豐富。和他們在一起,我學到了不少東西。
我印象較深的是,到農委不久,陪同調研室主任去雲南參加了國務院農業產業化會議。第一次參加國家層面的會議,讓我大開眼界。
1991年,我接受重任,參加農業部組織的《中國農業全書山東卷》編篡工作,一年多的時間,和農業部相關單位以及省領導、省直30多個相關廳局委打交道,讓我初步瞭解地方工作程式、流程、特點等,瞭解全省農業農村基本情況。
九十年代,山東農業結構、規模、格局開始發生根本性變化。首先是諸城貿工農一體化產生,讓我們看到農村改革的方向,隨之,我們大力研究農業產業化和規模化經營,山東各地湧現出許多典型,我們加以總結提練。
那個年代,一度出現過全國農業看山東的景像。外省農業部門紛紛前來考察,較多的是江蘇、浙江、四川等省市區,我陪同外省考察團下去考察有不少次,也親歷現場學習觀摩。當然,我們也出省考察,比如去廣東、深圳和江蘇、浙江等省份。1992年我去廣東,乘坐航空公司圖154去的,這型飛機比較落後,噪音較大,讓乘客提心吊膽的。
在調研室,我還從事了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農村固定觀察點調查工作。一位年輕有為的小夥子,學農經的大學生幹部和我一起負責這項工作,我們一起共事幾年,合作得很愉快。農村固定觀察點調查工作,這是中央建立的農村社會經濟典型調查系統,專為各級黨委政府指導農業農村工作提供重要決策參考。這項工作是直接在村和農戶設立樣本進行調查,調查內容涉及農村社會經濟各方面2000餘項指標。我和同事們,經常到全省各地,深入到村、戶,調查瞭解有關情況。當時,山東最富裕的村和最貧困的村,我都去看過,深感改革開放對農村帶來的鉅變,農村徹底脫貧任重道遠。我們對農民收入、農業生產成本、農村貧困等進行研究分析,形成報告上報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關於農業產業化、規模經營、減輕農民負擔、工業反哺農業等,那時候我們醞釀相關政策,想農民所想,把農民對國家的期盼變為政策,懷著這種情懷,調研、思考、分析,提出對策建議。今天看,這些幾十年前研究的課題,全部變為政策落地,讓農民得到實惠,農業得到大發展。
1993年,我去科技處任副處長,這對一名軍轉幹部來講,“官復原職”挺快的了,也知足了。我主要負責農民體協和其他工作。幾年來,和一位學體育的大學生幹部,組織農民體協工作,他熱情高幹勁足,是個得力助手。我們多次往返北京、上海等地,帶隊參加全國農運會,取得名列前茅的好成績,和各省代表,到過中南海,受到時任副總理田紀雲等領導同志接見。第一次來到中南海,心中特別仰慕,這裡曾經是毛主席、周總理辦公、生活的地方。
建國45週年成就展
建國45週年成就展
作者在人民大會堂觀看演出
1994年,我和同事們在北京完成國家交辦的八省市建國45週年展覽後,十月一日晚上,在天安門廣場和黨、國家領導人相聚同慶。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安排我們來到人民大會堂,為我們進行慰問演出。
1996年,國務院在廣東召開六省糧食規模經營工作會議,我陪同有關領導同志參會。分管農業的國務委員陳俊生到會,我們參會人員,和國務院領導同志一起探討發展糧食生產的經營模式、政策措施等問題,讓我頗有收穫。
1997年,我到農村基層處工作,參與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工作,經常要到全省各地調研農村合作經濟建設發展情況,這種合作摸式,和人民公社完全不同,比"單幹"更有力量和效益,是農村經濟發展的方向,我們為省政府起草推進相關工作的意見,召開全省現場會,請省長到會講話,大力推開這項工作。
還有,山東農村於1984年解決溫飽問題後,開始有序推進農村小康建設。農村小康是啥樣子?我們和省統計局反覆研究制訂農村小康標準,每年到一批縣市區查驗小康工作,整體推進全省農村小康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