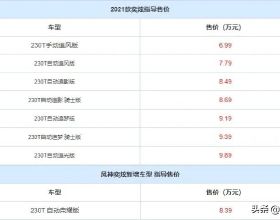《以世界為家》(Home in the World: A Memoir,企鵝Allen Lane出版公司 2021年7月出版),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回憶錄,寫到他年滿30歲為止。森解釋說,30歲之前是他的求學歲月。1963年,他回到印度,任教於德里經濟學院,身份從學生轉變為教師,那是另一段故事。
書名與森個人經歷有關,他是孟加拉人,當時孟加拉還沒有獨立,首府是加爾各答。3歲的時候,做化學教授的父親攜帶家庭從達卡搬到緬甸曼德勒。後來森又回到孟加拉農村上學,再到加爾各答念大學。從這裡出發前往英國,後來任教於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和美國哈佛大學,同時也在印度教書。
在森的學生時代,孟加拉處於英國統治之下。當時孟加拉知識分子有一種世界眼光和世界聲譽,這就是以泰戈爾為代表的黃金一代(泰戈爾是第一位來自亞洲的諾貝爾獎得主)。有人認為,森應當算是孟加拉黃金一代最後的存世者。
森的外祖父是泰戈爾的秘書,他的名字“阿馬蒂亞”就是泰戈爾起的,意為永生。後來他又在泰戈爾創辦的寂園學校讀書10年,深受泰戈爾自由與理性觀念的影響。森有兩本著作在書名中包含自由一詞,《作為自由的發展》和《自由與理性》。
從劍橋大學開始,森在經濟學領域中的遊學經歷由一連串偉大經濟學家的名字組成,其中最關鍵的選擇是將學術重心從英國劍橋大學轉向美國。他在MIT向薩繆爾森和索羅學習,在哈佛大學向阿羅學習,正是和阿羅的合作為他在社會選擇理論中的重大建樹開啟通路。
1998年諾貝爾獎頒獎詞中寫道,森在福利經濟學中“開拓了新領域,供後來好幾代研究者進行研究”。在學術界,大師的意思是幫助其他研究者找到飯碗。
根據阿羅不可能定理,民主決策必然是非理性的,而獨裁者卻能做出理性決策。這項分析在邏輯上無法反駁,卻讓經濟學界陷入尷尬。森發展了阿羅不可能定理,找出了約束條件。
他的研究證明,在投票者掌握更多資訊的條件下,由民主程式達到的社會偏好可以滿足理性條件。這一理論成果的思想淵源仍然可以回溯到泰戈爾的自由和理性觀念。自由是絕對價值,但自由也必須是理性的。
1961年,森在劍橋大學任教,希望開設福利經濟學課程。劍橋大學的經濟學家多方反對,最後勉強同意他講8課時,這可能也是導致他離開英國的原因。森在劍橋大學的繼任者米爾利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張維迎的老師)要求繼續開課,遭到拒絕。校方解釋說,這門課是作為讓森留在本校任教的條件才開的,並非常設課程。
看森的傳記,對劍橋的學生培養機制印象深刻。森在入學時並不順利,但到學校後,很快受到瓊·羅賓遜和皮耶羅·斯拉法的賞識。作為學生,他向以賽亞·伯林請教,得到伯林的認可。伯林在名著《自由四論》中數次提到森的名字,他甚至在前言中寫道,“斯賓諾莎和森的觀點是錯誤的”。
博士畢業後森去MIT訪學,受到保羅·薩繆爾森的照顧。薩繆爾森當時已經是經濟學界的領袖,他非常重視森的研究工作,請森代替自己講授一節福利經濟學課。森的印度背景沒有妨礙他進入主流學界,而中國經濟學家卻很難成為世界的學者。
劍橋大學過於政治化和忽視福利經濟學,他前往美國尋求發展。美國經濟學界又過於保守,森的研究固然受重視,卻缺乏社會影響。2015年諾貝爾獎得主安格拉斯·迪頓在劍橋上學的時間比森晚了12年,他提到劍橋大學和芝加哥大學之間的差異。
在劍橋時,迪頓讀到斯蒂格勒(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文章裡面說,“經濟學的專業研究使人在政治上變得保守”。當時他以為斯蒂格勒寫錯了,因為在生活中,他沒有遇到過一位保守的經濟學家。1983年,他也到了美國,才知道斯蒂格勒說的是真相。迪頓選擇經濟不平等作為研究課題,在美國同行看來,這是不專業的表現。
森還記錄了另一處反映劍橋大學與美國大學學風差異的例子。斯拉法是劍橋大學最傑出的經濟學家和哲學家之一,是世界上極少數能夠與維特根斯坦爭論並贏得後者尊重的學者。他自己幾乎不寫書,卻花了22年時間主持編輯大衛·李嘉圖全集共11卷(中文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有一次美國經濟學家阿羅到劍橋大學拜訪斯拉法卻吃了閉門羹,因為他這一整年都忙於為全集編制索引,不見客。阿羅不能理解,向森抱怨說,索引這種事有什麼重要的。森試圖為斯拉法辯護,但他也知道自己沒能說服阿羅。
森對政治頗為熱衷,只是他的立場讓左右兩派都不喜歡。在回顧以往經歷時,他說,自己從未做過政府顧問,但一直生活在民主社會,從來不缺少提出建議和批評的機會。在他的評論中,有不少刺耳之聲,例如對亞洲價值觀的嚴厲批判,這和他對自由的強調是一致的。
饑荒研究
森對經濟學的一項重要貢獻是饑荒研究。1943年,他親身經歷了孟加拉大饑荒,那次饑荒中餓死的人數達到兩三百萬。雖然森的家庭和家族都沒有受到飢餓的威脅,但加爾各答大街餓殍遍地的情景讓他受到極大的震動。28年後,他寫成《貧困與饑荒》一書。
關於饑荒,已經有了許多記錄和研究,但在現實中卻始終難以根除。常見的解釋有三項,糧食減產導致供給不足,官僚主義政府和黑心商人。這些只是常識,學術研究的意義在於突破常識,形成洞察。森的研究證明,饑荒並不是因為缺少糧食,而是另有發生機制。
1943年和1974年孟加拉發生饑荒時,當地糧食供給並未減少,但糧食的分配卻出現了問題。人類社會本身有多樣化的糧食分配機制,每個人都可以從不同渠道交換糧食。因此,儘管許多地方貧富差距嚴重,飢餓是常見現象,饑荒卻並不常見。
饑荒的典型特徵是在短時間內發生大量餓死人的事件。其具體表現就是短期內糧食價格迅速上升,經濟學中稱為衝擊。如果市場上存在著多種交換糧食的渠道,衝擊就會減弱並停頓下來。
但是,在造成饑荒的衝擊出現之前,社會上往往已經發生了某些變化,其結果是剝奪了部分社會群體透過交換獲得糧食的權利。當所有糧食交換渠道都中斷之後,饑荒就會集中暴發。森的研究發現,通常饑荒餓死人的比例不超過人口的10%,這10%就是被剝奪獲得糧食權利的群體數量。
1943年孟加拉饑荒發生時,英國殖民政府保證像加爾各答等大城市的糧食供給,對陷入災難的農村卻放任不管。1974年孟加拉再次發生饑荒,這一年的糧食產量增長高達14%。
一方面是統計數字顯示糧食並不缺乏,另一方面是在現實中,農民和農業工人被高價格擠出市場,並且在這之前發生的經濟政策變化讓他們失去了用勞動交換糧食的權利。《貧窮與饑荒》一書的副標題為“論權利與剝奪”,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1999年,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後,森出版了《作為自由的發展》。書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觀點。某些地區出現糧食長期短缺的現象,這是有可能的。但在民主社會中,只要沒有書報檢查,就不會有大量死人的饑荒發生。
1943年,英國殖民政府以戰爭為理由壓制新聞自由,英國民眾不瞭解饑荒真相。直到幾個月後,媒體拒絕合作,揭露了真相,饑荒的訊息才傳到倫敦。一旦公眾知道饑荒發生,政府就不得不採取措施緩解饑荒。
1947年之前,印度是英國殖民地,談不上民主政治,曾經多次發生饑荒。獨立後,印度民主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效率在世界上名聲不佳。即使如此,印度再也沒有發生過饑荒。
簡單地說,在民主社會中,窮人會捱餓,但不會有饑荒。這個結論因為違反直覺不斷受到挑戰,許多經濟學者認為森不應當越過經濟研究的界限進入政治評論。森在接受媒體時說,他沒有想到這一論斷會引發如此多的爭議。[i]
《紐約時報》說,正如提到亞當·斯密就會聯想到看不見的手,提到熊彼特就會想起破壞性創新,森的名字已經與民主防止飢荒的論斷聯絡在一起。
今天,《貧困與饑荒》仍然代表著經濟學對饑荒最深入、最具原創性的研究,應當列入大學通識課必讀書目。
[i]https://www.nytimes.com/2003/03/01/arts/does-democracy-avert-famin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