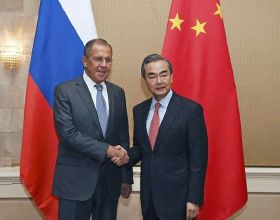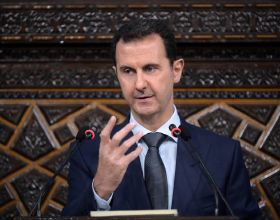只希望自己不辜負當下的一切,電影是我一生的事業,我會再接再厲。
作者|何合
編輯 | 陳令孤
章子怡的特點在於,她一旦決定了做某件事,就不惜力,勇往直前,追求最好的狀態。
比如《詩》的創作。接到這份工作前,她沒想過當導演;決心以航天為題後,她也不管深入此專業的難度有多大。其間,她推翻了十幾版劇本,也在原址重建了航天人回憶中的房屋、工廠、學校。多年來腦海中積攢的電影庫,化成了影片質檢的標杆。“她對每一件事都追求極致。”製片人田甜評價說。這句話伴隨了作為演員的章子怡20多年,如今又到了導演章子怡身上。
在2021年國慶檔上映的影片《我和我的父輩》中,《詩》作為唯一一個女性執導的單元,以上世紀60年代一個普通航天家庭的故事,激發起無數觀眾的共鳴。透過孩子的視角,身為火藥雕刻師的母親鬱凱迎(章子怡飾),與身為火箭工程師的父親施儒宏(黃軒飾),在荒涼戈壁中揮灑青春與生命,而他們的一對兒女則面對著如何對待“死亡”的沉重命題。
透過對影片精益求精的把控,章子怡還原了初代航天人在漫天黃沙的戈壁上、在漏雨的乾打壘房屋中,開啟浩瀚宇宙征程的那份浪漫。正如戚發軔院士所說,“艱苦而幸福的生活。”
從影22年,章子怡塑造過無數經典電影形象,而如今,她在電影這塊版圖上又邁出了新的一步,去追尋更大的理想。
以下為章子怡的講述—
打破瓶子
2021年絕大部分時間,我都在《詩》的創作中。自從接到這個專案,從劇本階段到後期剪輯,我的腦子裡裝不下別的,天天想的都是如何把這個作品做好。當今年(2021年)10月電影上映時,我才如釋重負,有種交上答卷的心情。
“痛苦”,這是我接到這份工作的最初想法,源自於未知——故事未知、拍攝主創未知、如何做導演未知……所有的一切都是未知的。
從2019年的《我和我的祖國》開始,我一直在關注“我和我的”系列,所以收到《我和我的父輩》導演邀約時,我內心是誠惶誠恐的,不知道自己有沒有這個能力,去完成這樣一項工作——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想過要當導演。
很多人都在鼓勵我,包括凱歌導演、程耳導演,張藝謀導演還跟我說:“有任何問題儘管找我。”這些溫暖善意對我來說是一種很大的鼓勵。我的家人更是無條件地支援我、包容我,讓我能心無旁騖地去創作。這令我最終下定決心,去嘗試涉足導演這一領域。
《詩》之所以選擇航天題材,是因為我自己是個航天迷,一直以來都對宇宙、太空很著迷。我記得有一回在機場候機時,在電視裡看火箭發射,升空那一刻,民族自豪感也油然而生。
但僅僅出於興趣的瞭解,肯定是遠遠不夠的。我們最初寫了一稿故事,講“兩彈一星”時期新婚夫妻分別,在一牆之隔工作,卻為了保密而互不相知。但我們去拜訪航天專家時,這個故事直接就被否決了。因為我們創作時其實落入了原子彈故事模式中,航天工作者們其實是“萬人一杆槍”,彼此之間要緊密協作配合。
當時,航天專家給我講了很多初代航天人的故事,有許多默默無聞的人犧牲在這個崗位上,而他們的家人做好了思想準備。“犧牲”兩個字似乎流淌在那一代人的血液裡。第一代研製人造衛星的人,沒有任何經驗,沒有任何圖紙,也沒有任何的老師,不斷地試錯,而試錯的過程中,就會有失敗——失敗就意味著,可能獻出生命。
航天專家們非常支援我們的工作。在前期調研時,我們和航天人多次溝通,去深入瞭解這個行業的故事。但越是瞭解深入,我就越感覺難以選擇一個故事去代表航天精神。當時我們底稿素材生成了許多不同方向的故事,但都不太滿意。
直到後來有一天,我在電視上看到《大國工匠》中火藥雕刻師徐立平的故事——現在全中國從事這個職業的只有200多人,他們每天用金屬刀具去雕刻火藥,一旦用力稍有不當,點著了,就會發生爆炸,幾千度高溫。
我就在想,“每天跟死亡打交道的人,他們會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透過朋友我們聯絡上了徐立平老師,採訪了他和他的母親,問了好多問題,瞭解火藥雕刻師的日常工作與生活,一遍遍修改劇本,最終才確定下來了《詩》的故事。
我感覺導演就是一個“打破瓶子”的過程——不像以前做演員的時候,努力就可以了。你得把瓶子打碎了,鑽出來透口氣,再鑽進另一個瓶子裡,這是一個週而復始的過程。
迎難而上
《詩》的開篇,是長達三分鐘的一鏡到底。鏡頭跟隨孩子們的腳步,翻過土牆,穿過院子,經過乾打壘小學學校的廣場,最後在屋頂上眺望遠方。
我希望用這個開篇,將觀眾一下子帶入到60年代的氛圍裡面去。這是一個集體完成的動作,就像接力遊戲一樣,需要33個小朋友的緊密配合。但孩子們是不可控的,如果一個人注意力不集中,所有人的付出就全白費了。
我們第一次拍攝時,拍了30多遍,只有2條是勉強合格的,大家都感覺太難了。然後我就去給孩子們開動員大會,獎勵表現好的人吃冰棒,一個個儘量去調整他們的狀態。第二次拍攝,才終於有了比較滿意的鏡頭。
做新人導演,我是摸著石頭過河,每一步都是未知的挑戰。以前做演員的時候,我只負責把自己角色做透,任務就完成了。但導演是一個大管家,需要把電影裡每個人物做透,每個細節做透。從拍攝場景的勘察、乾打壘學校的原址重建,到雨戲中降雨的大小、一個牆面標語……都需要去操心。
《詩》這個故事需要很多兒童演員,我考慮過拍攝難度,張藝謀導演也問過我,“知不知道孩子最難拍?”但思來想去還是覺得,透過孩子的視角去切入父輩、航天人的故事是最合適的。
比如父親這個角色只有在和孩子交流的時候,才會說出“我的工作其實就是在天上寫詩”,孩子的視角讓整個故事能夠立起來。而且初代航天人的故事,肯定要描寫艱苦,但如果直接向觀眾展現艱苦,力度就會弱。以孩子童真的眼光,去透視這種艱苦,恰好能賦予一種苦中作樂的趣味。
我對於和孩子的交流也是有一定信心的,我是三個孩子的媽媽,有足夠強大的耐心和方法陪伴孩子們。我覺得就是要足夠信任和尊重他們。其實孩子們都是很聰明也很敏感的,你的真誠和友善,他們能感受得到,他們回饋給我的是信任和與大家的協作。
我們的小演員很多都是城市長大的,為了讓他們適應環境,呈現出那個年代孩子的狀態,我帶著他們提前到拍攝地,讓他們去適應這樣一個環境,主要就是玩。孩子們融入得很快,天天玩土,滾鐵環、玩彈弓、和泥巴、拔河比賽之類的,他們都玩得很高興。我也陪著他們一起玩,經歷著他們的改變。
沒有耐心,你是拍不了孩子的,需要很長的時間去打磨。你要用各種“招”去把他們帶入那個狀態。無論是對於哥哥還是妹妹,你都要幫他們想該怎麼演,教得很清楚,幫他們進入那個情景狀態。但一旦進入了,他們可以給你最真實的狀態。
在《詩》殺青前,我又把一鏡到底的長鏡頭重拍了一遍。因為反覆觀看後,我覺得有些細節可以再生動一點,比如標語和喇叭,我希望抓住最後的時間和機會,儘量做到最好的效果。我們最後一次拍攝,超乎預期的完美。
殺青的時候,我給了小朋友們一人一個小獎狀。因為我覺得這些孩子表現得都非常好,也是因為孩子們的配合和信任,才有了《詩》的完成,沒有他們,電影不會精彩。所以我覺得他們值得被鼓勵,也希望這次拍攝可以鼓勵他們未來的成長。
再回首
“靠我一個人,就是沒戲。”我當時就跟所有劇組成員這麼說。
我拍過很多戲,但我只是負責演員的部分。拍《詩》的時候,我回想以前做演員的時光,一場戲拍完了,就問導演“你覺得怎麼樣”,一天戲拍完了,就打個招呼“導演辛苦啦”,然後收工。但現在作為導演,擔子一下子重了很多。
對我來說,這是史無前例的一次經歷。但是經歷了這一次的拍攝,我意識到拍一部戲——哪怕是30分鐘——它要付出多大的代價。我感謝所有人為這部電影付出的每一天,每一分鐘,每一滴汗水。
這次做過導演之後,我特別感激在從影22年中遇到過的導演。他們教會了我很多東西——不僅僅是表演。多年來跟許多優秀的導演以及專業的攝製團隊合作,我潛移默化地學到了很多東西。
我閱片量很大,腦子裡有一個電影庫,裝著所有看過的電影。在拍攝《詩》的過程中,這些記憶全都被調動出來了,運用到了這個電影中。我的攝影師餘靜萍老師也給予了我非常大的幫助,我們共同找到了一個合適的基調和色彩,去詮釋《詩》中黃沙漫天的艱苦和征服蒼穹的浩瀚浪漫。
因為這次拍攝,我深刻感受到了,電影不是一個人的獨角戲,它是所有人一起努力的結果。我們這次整個主創團隊大部分都是女性,也希望透過《詩》讓更多人瞭解到這些優秀的人,讓她們的才華被更多人看到。
我一度不太想演鬱凱迎這個角色。因為按照我的習慣,要用三個月以上的時間進入角色,她是誰,她是怎樣的一個人,她受過怎樣的傷,然後我會一直沉浸在角色裡。而身為導演,你必須“跳出來”去管片場的其他事情。但這一次恰恰相反,我入戲特別順利,後來我想,大概是因為我陪伴這個角色,經歷了從無到有的過程。
為了演鬱凱迎這個角色,我有一段時間跟著火藥雕刻師羅懷聰師傅學習雕刻火藥。有一次我就問他,有沒有考慮過去做別的工作。他說,“我一點這個心思都沒有,這就是我的職業。”
那一刻,我被觸動了。“擇一事,終一生”,這種信念太感動我了。在我們這個時代,可能有很多的選擇,但是對於他們那一代人,一旦有了事業上的選擇,就會全心全意投入到這個工作崗位上,不會再有其他的心思了。
電影上映後很多人鼓勵我拍攝一部長片,我很感謝大家對我第一次做導演的認可。未來如何,我沒有預測,只希望自己不辜負當下的一切。電影是我一生的事業,我會再接再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