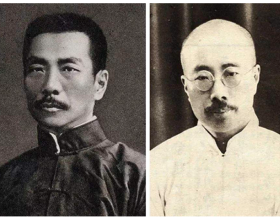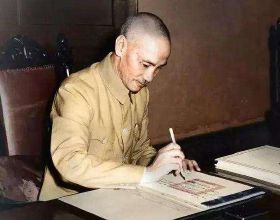1906年,魯迅在日本仙台醫學專科學校學習已近兩年。在此之前,他在東京求學,那時正是日本國力強盛之時,又在甲午海戰中打敗了中國的北洋水師,整個日本瀰漫著野心的氣息和對中國的輕蔑。當時日本的報紙上印著這樣的文字:
“西洋人視中國人為動物,實際確乎不得不產生動物、下等動物的感覺,因此,他們(指中國人)在生理上已失去人類的資格。”
魯迅就在這樣一個環境裡修習日語,他後來說過這樣一句話:
“一個人乏到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也就難保別人不來打你的嘴巴。”
在充滿侮辱和鄙視的異國他鄉里,魯迅見到的中國人,是怎麼樣的呢?
“頭頂上盤著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鑑,宛如小姑娘的髮髻一般,還要將脖子扭幾扭。實在標緻極了。”
魯迅去了仙台,打算學成之後為國人治病,若仍在戰爭時期就去當軍醫。在仙台醫學專科學校,他的處境依舊算不上好,生活艱苦,成績中等。據他的老師藤野先生回憶:
“記得那時周君的身體就不太好,臉色不是健康的血色。當時我主講人體解剖學,周君上課時雖然非常認真地記筆記,可是從他入學時還不能充分地聽、說日語的情況來看,學習上大概很吃力。”
“如果是在東京,周君大概會有很多留學生同胞,可是在仙台,因為只有周君一箇中國人,想必他一定很寂寞。可是周君並沒有讓人感到他寂寞,只記得他上課時非常努力。”
儘管學習用功如此,但是魯迅還是收到了一封學生幹部的信,上面寫著:“你悔改吧!”
不過魯迅也沒有忍氣吞聲,他把這件事告訴了藤野先生,幾個和他關係好的同學也很不平,最終是把流言擺平了。在二十多年後,提及這件事,魯迅嘲諷而無奈地寫下:
“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
然而這只是一個小插曲,對他影響最大的,甚至可以說是影響了他一生的事情,在第二年發生了,那就是著名的“幻燈片事件”。當時已經用到幻燈片放映微生物,課餘也放一些時事片子。魯迅作為全教室裡唯一一箇中國人,看著電影上的一群中國人圍觀自己的同胞被外國人槍斃,末了還高呼“萬歲”,這個場景深深地刺激了魯迅。
“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而在魯迅學習著新的知識,接受著新的思想,面對著新的挑戰的時候,在他的故鄉紹興,又發生著什麼呢?魯迅的母親在為他謀劃“終身大事”。1906年夏,也就是他在日本留學的第四年,魯迅收到了來自家裡的電報,上面寫著母親病重,速歸。
等魯迅回到紹興,看到的是修繕好的房子,添好的新傢俱,還有家裡的張燈結綵,他知道沒有退路了。他反抗過這場包辦婚姻嗎?反抗過。
1899年婚約初定的時候,他就寫信回去,自己不願成婚,希望讓朱家姑娘另嫁他人。然而無用,於是他又寫信,說接受婚約也可以,不過有兩個要求,希望女方進學堂、放足,而這兩個要求被朱家拒絕。
在他不在家的這幾年,母親前前後後張羅完了出口、請庚、文定、看戲、拜壽。周家與朱家一直保持著禮節上的往來,由本家親戚做媒,兩個家族間已經建立了相當穩固的關係,況且由本家的親戚做媒,因此要想悔婚是很困難的,也是絕對說不出口的。
或許魯迅也曾經希望能夠接受朱安,透過女方讀書和放足來縮小兩人之間的差異,然而這個巨大的鴻溝從一開始已是不可縮小的了,在紹興盛行的是“婦道”與貞潔牌坊,朱安也不例外接受這種思想的薰陶:從小背誦女兒經,侍奉丈夫長輩才是女子一生之道,讀書不是女子該做的;這足是從五六歲開始纏的,朱安現已二十八歲,放足也無濟於事了,三寸金蓮的骨頭已經被扭曲掰碎定型,怎麼可能再長一回呢?
魯迅知道事情已無可挽回,他抱著“陪著做一世的犧牲”的心態,接受了這一切。
“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1904年在日本的時候魯迅曾參加不少反清革命運動,甚至還接收到過暗殺的任務,或許他也猜想,自己參加革命將命不久矣,那就應了他們的要求吧,何必再節外生枝,讓母親難堪呢?
這時家裡的親戚都擔心他身為新派人物,是不肯做舊式婚禮的,而魯迅卻一言不發,默默地照他們說的辦,完成了這場婚禮所有該走的章程。戴著一頂羅制的簡袍,裝著一支拖出在帽下的假辮子,身上的服裝用袍套,腳上穿著靴子。
在禮堂裡接過全身古裝的新娘,拜堂成親。魯迅一生戰鬥,用辛辣狠戾的武器抨擊著舊社會舊時代,卻用寬厚無奈的心態接受最親近的人給予他殘酷的命運。假辮子,新郎官,新娘假裝大腳掉下來的鞋,在魯迅心裡,大概是這輩子都不再願意回想起這恥辱的一幕了。
周家的傭工王鶴照回憶說,結婚的第二天晚上魯迅就搬到書房去睡了,起來時印花被的靛青把臉都染青了。婚後魯迅很少對人提及自己的婚姻,只對好友徐壽裳說過這樣一句悲哀的話:
朱安被當作一個禮物,一個物品對待,她的命運如何完全取決於接收者的喜好、心情。可惜以她思想裡僅有的傳統觀念讓她終身沒有理解到自己命運悲劇的根本原因。魯迅在婚後第四天,就和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離開了母親強加給他的女人。
朱安從訂婚之時,被周家少爺逃避了五年;新婚不足一週,她再次被拋棄了。沒有人記錄過朱安這時的心情,她是怎麼想的,怎麼安慰自己的,然而她依舊沒有心死,她的想法很簡單,那就是這些年來長輩們不斷傳輸給她的“生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覺得自己就像—只蝸牛,只要慢慢爬,慢慢熬,總能等到周家少爺回心轉意的一天。
從此以後,魯迅和她各過各的,既不吵架,也不交談。不過這並不是因為雙方互相的對立,而是徹徹底底的無話可說。
魯迅和朱安,一個學識淵博,一個目不識丁;一個追求革新,一個固步自封;一個志向遠大,一個目光如豆,毫無共同語言。
在紹興時,魯迅每天晚上就抄寫古籍,並時時向好友徐壽裳詢問是否有事可謀,1912年初,魯迅終於如願以償,離開了令他失望的故鄉和家庭。
2月,他於紹興到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擔任部員,5月初與許壽裳一同北上,就任北京教育部部員。從此,朱安又開始了長達七年的獨居生活。即便是七年後魯迅舉家搬遷到北京八道灣,周家兄弟失和後又隨魯迅從八道灣搬到磚塔衚衕。
魯迅對朱安的態度始終沒有變過,能少說話就少說,能不交流就不交流,他甚至發明一個方法,在自己屋門口放一個籃子,每天把舊衣物放進去,朱安去取出來,在換上新洗滌好的衣服。在磚塔衚衕時,朱安憑藉每道菜的剩菜量揣測魯迅喜歡吃什麼,剩得少的,大先生大概喜歡吃,下次就多做一些。
在紹興時,朱安常常回孃家,一回就是十天半個月,在孃家,她可以得到一些家的氣息和親人的愛與陪伴。侄子朱吉人那時只有五六歲,她很喜歡與同胞兄弟的孩子一起玩耍,朱吉人回憶,自己當時也非常喜歡姑姑。但1919年周家賣掉了祖宅,舉家搬遷到北京時,朱安就明白,自己是再也回不到一個可以給予自己溫暖的孃家了。但是,“生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她依舊毫無怨言地隨周家一起北上了,此後再也沒有回過自己的家。
朱安對魯迅在生活上的照顧是無可挑剔的。魯迅遷入磚塔衚衕不久,就病倒了,她對“大先生”的照顧可以說是無微不至。
魯迅當時不能吃飯,只能吃粥,據魯迅的學生俞芳回憶:
“大師母每次燒粥前,先把米弄碎,燒成容易消化的粥糊,並託大姐到稻香村等有名的食品商店去買糟雞、熟火腿、肉鬆等大先生平時喜歡吃的菜,給大先生下粥,使之開胃。她自己卻不吃這些好菜。
在磚塔衚衕,魯迅的書桌是放在朱安的屋子裡的,魯迅白天的案頭工作,一般就在這某上進行,因為這裡光線好,安靜,朱安白天常在廚房裡張羅飯菜等事,輕易不去打擾他的工作。
有時同院的俞家姐妹有些吵鬧,朱安也提醒他們不要吵大先生,有時甚至是懇求她們:大先生回來時,你們不要吵他,讓他安安靜靜寫文章……這一刻的朱安,終於有了一點女主人的樣子。
朱安總抱著一絲幻想,以為只要好好地服侍好丈夫,孝敬婆婆,終有一天對方能幡然悔悟,發現從前是錯待了她。對朱安在生活上給予自己的照料,魯迅也是清楚的,可是,他可以同情她,供養她,卻無法對她產生那種“愛情”。
魯迅對待朱安的態度也是他當時和之後一直被詬病的,他似乎是過於冷漠、過於無視朱安的存在,他極少和她說話,從不和朱安一起吃飯,朱安在他的日記裡只有模模糊糊的一個“婦”字,收到朱安慌張的來信,他也不回信,只是在日記裡寫上“得婦來書,頗謬”。身為一個人道主義者,他對待朱安卻似乎一點也不“人道”。然而,除了關心這種情感上的給予,魯迅已經儘自己所能,給予朱安能給的責任和庇護。
在魯迅所寫的短篇小說《祝福》裡,塑造了一個受封建禮教迫害的不幸女性的形象,祥林嫂。
當祥林嫂改嫁喪夫後第二次來到魯四老爺家時,已經不允許被觸碰祭祀的東西了,因為她碰到了就會“不乾不淨,祖宗是不吃的”。她存了一年的工錢去捐了門檻,神氣舒暢,以為可以重新“做人”了,但是依舊是被視作“不祥之兆”。
魯迅對舊式婦女受壓迫不可謂認識不深,這種深刻悲哀的同情,是他一直沒有拋棄朱安的理由。他知道朱安一旦被休棄,面臨的是怎樣刻薄的社會評價和她自己內心絕望的鬥爭。
不管是幾次搬家、離居,魯迅一直都帶著她、保障著她的基本生活,即便是在二十多年後朱安徹底心死,放棄了讓魯迅對她回心轉意的願望,她也嘆道過:
“看來我這一輩子只好服侍娘娘(魯迅母親)一個人了,萬一娘娘歸了西天,從大先生一向的為人看,我以後的生活他是會管的。”
魯迅在家鄉目睹了不少舊社會女性悲劇的身世,對她們的同情也是他日後寫作的重要積累和鋪墊。但是,當自己身邊就有一個同樣因舊思想受害的女性時,他只有道德義務上的關注,卻似乎沒有對她個人情感上的憐愛了。在這裡不是一個旁觀者對一個平白受難的不幸者的同情惋惜,而是在同一個婚姻悲劇裡一個受害者對另一個受害者的複雜感情,既可憐她的無辜,也怨艾她給自己帶來的苦難吧。
魯迅對朱家也一直維持著照顧與聯絡。從1919年開始,便時常收到朱家來信,魯迅也在1924年和1925年有過兩次匯款寄去禮金。1930年朱家情況惡化後,也常常受到周家的救濟。魯迅曾在朱家有困難時多次匯款予以援助,他寄給朱家的錢款,大多是出於禮節性的,但也體現了一種親情。
1931年,朱安的父親朱可銘因病去世,在這前後,魯迅兩次寄到紹興100元。1932年、1933年的匯款可能是因為朱安母親病重及去世。對此,朱家也是很感激的,曾多次寄贈紹興的土特產,以示答謝。
朱安的想法沒有錯,之後她與魯迅徹底分居之後,大先生果然一直維持著她的基本生活,然而在魯迅過世之後,她的生活就逐漸困頓。再之後魯老太太的西去,更使朱安在經濟和精神上都陷入無依無靠的境地。
在朱安實在是窮困潦倒無法自給的時候,想要賣出魯迅生前的手稿,立刻有許多社會人士表示強烈反對,紛紛前來勸阻,許廣平也是在這是急急忙忙地給朱安寫了一封信,同情她的不幸,表示自己以後會照顧她的生活,魯迅的手稿是珍貴的資料,萬萬不可以賣掉。
在魯迅去世之後,為了大先生的名譽,她不接受社會的捐贈、也不喜歡向和魯迅決裂的周作人尋求幫助,默默一人忍受飢餓、貧窮和孤獨,在她實在生活不下去時,卻有這麼多人跳出來指責她不顧惜魯迅的遺物,朱安情緒激動,她哭訴道:
“你們總說魯迅遺物,要儲存,要儲存!我也是魯迅遺物,你們也得儲存儲存我呀!”
1947年,戰爭結束後兩年,朱安越來越感覺到自己大限將至,她寫信給許廣平鄭重交代了自己的後事,並列出了兩份清單,一份衣物清單一份送人清單,這兩份清單,包羅了朱安一生的財物,也包羅了她臨終前所記掛、感激和親近的人們。
這些人當中,第一位自然是許廣平和海嬰,這兩位是她在戰時孤苦生活的精神安慰和經濟支撐的來源。此外還有宋子佩及其太大,她的內侄朱古人、周作人一家,阮紹先一家、隔壁博太大一家,以及那些照料她多年的老媽子等等。這份留存到今天的清單,讓人多少感到一絲安慰,畢竟,在朱安晚年,作為魯迅的家眷。還是有那麼多人熱心地照料她。
她是個舊式女人,同時也是一個善良的女人,在度過極其痛苦的一生後、心底裡還保留著感激和暖意,希望用她遺留下的衣物和被褥,給活著的人以溫暖。
參考文獻:
魯迅《藤野先生》
王曉明《魯迅傳》
藤野嚴九郎《謹憶周樹人君》
魯迅《吶喊·自序》
《魯迅的婚姻與家庭》
喬麗華《朱安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