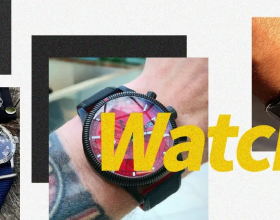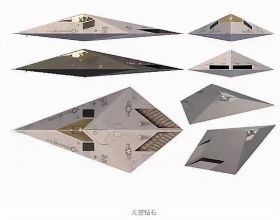1988年初夏,在南京湯山靶場,一場實彈測試正在緊鑼密鼓的準備中。正在除錯裝置的美國雷神公司技術人員,突然向我國負責人,開口索要靶場地區的軍用地圖。軍用地圖可是國家機密,怎麼能交給外國人?在給出了一個極不自然的笑臉後,我國負責人表示,這個問題需要請示上級。
請示的報告從炮院打到軍區,再從軍區一路打到總裝,最後直達軍委。最終經過軍委的拍板,地圖還是拿了出來,並在一臉的不情願中,靶場軍用地圖被裝到了繪圖器上。當然,我們還是留了一手,把試驗限定在南京湯山靶場的有限範圍內,而沒有選擇條件更好的地方。
這段軼事的具體出處已經無法考證,不過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美軍貿往事中,AN/TPQ-37炮兵定位雷達的味道確實很苦澀,因為整個交易可以說是被美國玩弄於鼓掌之間。
美國套路中國,“吃完甲方吃乙方”
1987年,我國與美國簽署了一攬子的軍工技術合作與引進轉讓協議,陸軍的主要部分是以6200萬美元,引進4套AN/TPQ-37 Fire Finder“火力偵查者”炮兵定位雷達系統。在1987年,我國的外匯儲備只有不到30億美元,全年軍費也不過210億元人民幣(當時約合56.4億美元)。
而且,當時第一批2套雷達剛到貨不久,結果就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後續單子被美國單方面卡了。直到1992年,時任美國總統老布什為了爭取選票,做出緩和對華關係的表態,才下令“簡單了結”中美原有的防務合作計劃,後續的2套雷達才跟著滯留美國的2架殲-8B一起回了國。
在與我國簽署合同之前,1986年8月美國就悍然違背“八一七公報”,向臺灣出售了2套AN/TPQ-37雷達系統。而向我國交付第一批2套雷達的同時,美國又向韓國提供了5套同樣的裝備。東南和東北是我們當時兩個最重要的戰略方向,可美國卻以“保持戰略平衡”為藉口,出售給臺灣和韓國同樣的武器,真不愧是“吃完甲方吃乙方”。
雖說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與西方國家的關係被稱為“蜜月期”,我們也趁此引進了不少先進技術,但是每一筆交易的背後,都有著西方國家深深的套路。比如MK-46 mod-2魚雷同時賣給臺灣和大陸,Mirage-2000也同時向兩岸推銷。更惡劣的是,大名鼎鼎的“黑鷹”直升機,賣給大陸的S-70C是民用版,而賣給臺灣的SH-60B卻是軍用艦載版。 “國防現代化是買不來的”,這句話的背後又有著多少辛酸。
中國臥薪嚐膽,三管齊下實現翻盤
1987年,雖然我們完成了對“辛柏林”雷達的仿製,但是仍然缺乏反制大口徑遠端火炮的手段。尤其是當美國向臺灣出售2部AN/TPQ-37之後,兩岸的軍力平衡被徹底打破。在這樣的情況下,儘管明知美國“兩頭吃”,但是我們也只能忍辱負重,捏著鼻子把AN/TPQ-37買了。
當時,英、法、德牽頭聯合研製的Cobra“眼鏡蛇”彈道定位雷達還處於開發階段,瑞典的Arthur“亞瑟”火炮搜尋雷達還在PPT上。蘇聯雖然有現貨,但是兩國關係還沒完全解凍。找來找去,也只有從美國能進購現貨。當然,美國人精明,我們也不傻,AN/TPQ-37一到貨,我們就立即三管齊下:一探虛實、二找對策、三搞復刻。
一探虛實。就是前面提到的,在南京湯山靶場進行實彈驗證性測試。在紙面上,AN/TPQ-37對加榴炮的測程達到35千米以上,對火箭炮要超過50千米,對彈道導彈也有100千米。不過,因為場地限制,在湯山的試驗只打到了27千米。為了打出這個射程,我們還拿出了當時的王牌——86式152mm加農炮。
測試結果表明,AN/TPQ-37雷達的捕獲機率可以達到0.95以上,高於0.85的驗收指標。定位精度也達到了54米,高於手冊宣稱的0.35%水平(在27千米距離上為94.5米),而一般確定炮位座標的時間為7-12秒。這一組資料,無疑碾壓了國產370雷達和371雷達。
二找對策。拿到了AN/TPQ-37雷達,我們也就能尋找對抗AN/TPQ-37雷達的方法。1994年,總參謀部炮兵局在河北宣化的黃羊灘炮兵靶場進行了一系列試驗。首先是無源干擾,嘗試打箔條彈,結果並沒有用。因為AN/TPQ-37是X波段無源相控陣雷達,具有動態精確測距額測速的功能。透過對比彈道特性,就能區分出箔條和實彈。之後進行有源干擾試驗,結果乾擾機功率不夠,直接被“燒穿”。更可怕的是,AN/TPQ-37對干擾源的方位定位精度達到10mil,如果採用雙站交匯,就能直接引導火力摧毀干擾源。以我軍90年代的電子戰水平,在面對AN/TPQ-37時,顯然是無從抵抗。
既然軟得不行,那就只能上硬的。一番海選下來發現,我軍901型雷達偵測器可以透過多點交匯完成定位,並且精度可以滿足炮火打擊的需求。同時還發現,AN/TPQ-37對以59-1式130mm加農炮為代表的,初速較高而彈道低伸的火炮,定位精度要顯著低於榴彈炮。正因為有了這個結論,我們才堅定了開發45/52倍徑155mm火炮的決心。同時,我們還發現AN/TPQ-37的多目標識別能力存在缺陷,當距離200米以上的陣地同時開火時,就會使得推算出的方位座標發生偏移。
三搞復刻。針對AN/PTQ-37的特點,在仿製的同時,也在進行技術升級。在世紀之交誕生的國產373型彈道定位雷達,就採用了S波段固態有源相控陣體制,定位精度更高,而且能同時定位多個方向的目標,效能全面超越了進口的AN/TPQ-37雷達。它的出口型號SLC-2,隨同PLZ-45型155mm/L45自行火炮系統實現出口,並發展為系列化型號。
雖然美國的霸權主義做派令人厭惡,但是在作戰理念上還是值得學習的。在引進AN/TPQ-37雷達的同時,我國還借鑑美軍的配置方式,以AN/TPQ-36雷達為基礎,自行研製了採用固態有源相控陣體制的704型彈道定位雷達。它的出口型號BL-904,同樣作為PLZ-45外貿自行火炮系統的組成部分,已經銷往多個國家。
從引進AN/TPQ-37,到SLC-2和BL-904超越的過程,是對“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抓住機遇、有所作為”這28字方針的最好詮釋。在實力不濟時,逞匹夫之勇也許會很壯烈,但是如果能忍辱負重、臥薪嚐膽,也許就能實現翻盤,而這才是更大的智慧。
站上更高的起點,中國炮兵偵察雷達達到國際領先水平
回顧上世紀90年代,其實很多事情並沒有表面上那麼可怕,當時在彈道定位雷達領域,我們與歐美等國家相比其實並沒有落後太多。實際上,後來出口歐亞多國的瑞典Arthur“亞瑟”火炮搜尋雷達,直到1999年才正式列裝。而英、法、德牽頭,歐洲多國聯合研製的Cobra“眼鏡蛇”彈道定位雷達,直到2004年才開始交付。相比之下,早在1997年,我們的PLZ-45系統就已經實現成套出口。
進入新世紀後,炮兵雷達領域呈現了新的變革。在作戰要素指數級增加的背景下,對於炮兵偵查雷達的效能需求,已經從過去單一的彈道定位,延伸到了地形測繪、防空反導、無人機防禦、電子對抗等多個領域。
在這樣的背景下,炮兵偵查雷達的系列化發展和技術迭代,也呈現出了日新月異的變化。而在這個領域,我國也已經達到國際領先水平。比如,在第十一屆珠海航展上首次亮相SLC-7型L波段多功能情報雷達,就採用了含有氮化鎵元件的數字式有源相控陣技術,不僅能夠定位火炮和火箭彈發射陣地,還可以遠距離探測和準確識別跟蹤包括隱身飛機、常規固定翼飛機、直升機、無人機、巡航導彈、戰術導彈、臨近空間目標在內的多種威脅,其用途之廣泛遠超其它國家的同類雷達,是具有國際領先水平的第四代情報雷達。
而行銷多國,累計出口超過100套的SLC-2系列雷達,也已經發展到了E型,而且還升級為多功能武器定位雷達。在第十二屆珠海航展上亮相的RA-2型彈道定位雷達,一分鐘可以處理850個目標,全系統反應時間小於8秒,對普通榴彈目標偵測距離達到50千米級別,定位圓機率誤差小於30米,綜合性能也超越了美國AN/TPQ-53雷達。
在炮兵偵查雷達領域,我們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從追趕到並駕齊驅,再到獨具特色,就是因為我們始終貫徹著“堅持獨立自主,積極爭取外援”的方針。在引進先進技術時,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原則,這才使得我們總是行進在正確的技術路線上。
小結:時至今日,世界上只剩下美、俄、中三家能實現全套炮兵偵查系統的自給,歐洲各路老牌列強都只能透過多方合作的方式勉力維持。當年,我們忍辱負重引進了AN/TPQ-37,到如今我們的系列產品行銷亞、非、拉十餘國,這逆襲背後無不彰顯著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