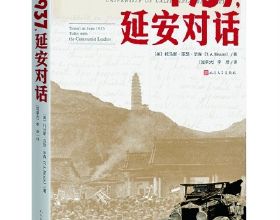如果說,這世界上有什麼事情對一個國家來說稱得上可怕且後果嚴重的話,那大概就是與一枚核彈“親密接觸”。
至於更嚴重的,那就是被甩上兩枚。
不管這個辦法是否不道德,以及人們是否同意,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認,在見識了某島國十幾萬人在一瞬之間灰飛煙滅之後,所謂的“核威懾”便成為二戰結束以來“維護”世界和平的不二“法寶”。
2015年12月22日,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不聲不響地披露了一份於1959年冷戰期間頒佈的“核戰爭計劃”。
在這份計劃中,美國政府擬定將在“戰爭”爆發後,向蘇聯以及世界上的其他紅色政權的1200座城市投放至少3400枚核彈,以一舉摧毀世界上主要的“反對者”,其中又有至少870枚對準了中國這個未擁核國家的117座大中型城市。
新中國曾經離核打擊有多近?又是誰在“核威懾”的巨大陰影下保護了稚嫩的中國?
答案或許簡單,但答案背後的故事卻絕不平凡。
1,
所謂“核威懾”,簡而言之就是,國家或政治集團為實現既定的政治目的,透過顯示核武力或準備使用核武器,以遏止對方行動的行為。
在1945年8月核武器在日本國土上展現出他無比巨大的破壞力後,“核威懾”這個詞便不脛而走,迅速成為後二戰時代最為人嚮往,也最讓人恐懼的詞彙。
對美國來說,蘇聯一直是敵人。
冷戰是上世紀美蘇兩個大國之間的政治、經濟,與區域性軍事衝突的統稱,然而即便在二戰尚未結束的時候,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對“社會主義”發自內心的恐懼,就已經讓美國視蘇聯為二戰結束後最大的敵人。
既然是敵人,按照美國一貫“先發制人”式的國家政策,作為有可能的最後手段,“核威懾戰略”自然而然會被美國政府提上“議程”。
事實上,在1946年3月5日丘吉爾於美國富爾頓城威斯敏斯特學院發表舉世聞名的“鐵幕演說”後,斯大林和杜魯門之間索性直接攤牌,1946年6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要求透過,一旦戰爭爆發,便迅速以核武器打擊蘇聯各大城市的“鐵鉗計劃”。
等時間來到1949年,蘇聯核武器意料之中的成功研製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不過同一時間壓力陡增的美國核打擊能力在來自蘇聯的重壓之下迅速提升,在這樣的背景下,“特洛伊”計劃,“敲詐”計劃等對蘇核打擊計劃爭相出爐,其打擊規模也是愈發肆無忌憚。
不過話說回來,對美國而言,遠不止蘇聯,其實地球上所有紅色政權都是敵人。
朝鮮戰爭是一場由“家事”發展成“區域性熱戰”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韓國喊著“爸爸救我”找來了美國和一眾“長輩”,朝鮮打出唇亡齒寒的大旗,沒能引來蘇聯的直接幫助,倒是找到了將在接下來表演“如何連挑韓軍與聯合國軍17個堂口的地表最強輕步兵。”
麥克阿瑟,人稱“韓國國父”、“五星天皇”,在他指揮朝戰期間,這個自出生起性格里就帶著剛愎自用的傢伙由於屢被志願軍“教做人”,一度“精神失常”,叫囂著“向中國投放30-50顆原子彈”;“在中朝邊界製造一道放射性鈷隔離帶”之類足以掀起三次大戰的過激言語。
然後,這位一度被日本愚民稱之為“神”的先生,就被杜魯門從“聯合國軍”總司令的位置上搞走,換上了更為穩妥的李奇微。
當然,麥克阿瑟的離任並不能代表美國不支援這位狂人口中的“核打擊”戰略。
1952年,軍人出身的艾森豪威爾贏得大選。然後,其任期內朝鮮戰爭的失利讓他腦海中誕生了一個清楚的認知:在當前時代背景下,美國的常規軍事力量的侷限性。正因如此,他開始迷信“全面核戰爭理論”,一度在修訂前任杜魯門的戰略時將該理論推進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1953年,在艾森豪威爾的大力支援下,美國在原有法案基礎上,再次透過一項名為“大規模報復戰略”的檔案。按照當時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的說法,所謂“大規模報復戰略”就是:美國國情決定我們需要擁有一支龐
大的報復力量,它能夠用我們選擇的武器與我們選擇的地方馬上進行報復。
換言之,艾森豪威爾政府的這一戰略把“賭注”押在了核武器上。
1956年,冷戰的第九年,為了預估未來可能發生的核大戰,美國空軍戰略司令部制定了一份“絕密計劃”,沒錯,這份計劃,正是開頭我們提到的那份計劃書。
2,
《1959年原子彈需求研究》,這就是那份計劃書的正式名稱,計劃書中,美國人以極為詳細的方式羅列了共計1200座戰爭開始後需要用核武器襲擊的城市。
DGZ,全稱Designated Ground Zero,翻譯過來就是“原爆點”。
在該計劃書中,美國為蘇聯、中東歐蘇聯“衛星國”,北朝鮮,以及中國準備了3400餘個DGZ,按照一個爆點一枚核彈來計算,美國本計劃將在1959年的中華大地上投下至少870枚各式各樣的核彈。
如圖所示,在上面這張1959年的中國行政區劃地圖中,我國當年各大省市在美國政府計劃中所要遭受核武器襲擊的數目一目瞭然,顏色越深就代表著要遭受核武器打擊的數量越多。
其中,單論區域內原爆點密度,首當其衝的是身為我國經濟中心,東海艦隊駐地之一的重要港口城市上海。從那份計劃書中我們獲悉,在上海這6340.5平方千米的土地上,美國人竟足足部署了82枚當量十倍於廣島“小男孩”的核彈,儼然一副要將整個上海“退陸還海”的模樣。
而與此同時,美國該計劃書中部署於中國同級行政區劃中原爆點數量最多的,則是東三省中的遼寧。
毛主席在視察哈爾濱時首次提出了東三省是“共和國長子”這個概念,因為這裡解放最早,距離蘇聯老大哥比較近,也擁有昔年日本侵略者遺留下來的工業基礎,其中,遼寧又因為地理上的微妙優勢成為“共和國長子”中的佼佼者。
“一五”時期,新中國156個重大專案中24個落在遼寧,全國17%的原煤、27%的發電、60%的鋼產自遼寧,第一爐鋼、第一架飛機、第一艘巨輪等1000多個新中國工業史上“第一”都誕生在遼寧。
這也就能解釋157顆核彈分配給遼寧的原因。
再說起重要性,我們就不得不提起我們的首都北京。
在這份計劃書的註釋中,美國人對他們要打擊的每個城市的重要性都標上一個數字,數字越小就代表著這座城市的重要性越高,其中,遼寧省會瀋陽是44,被82枚核彈鎖定的上海是28,北京則以13這一數字拔得國內頭籌。
在敵人的“肯定”中,首都對一個國家的重要性再次不言而喻。
不過有意思的是,美國人除了將各大省會與其餘一些著名的大中型城市標為核武襲擊目標之外,還在一度計劃中專門標註了許多現如今頗顯得“名不見經傳”的城市。諸如雲南箇舊、遼寧北票、黑龍江東京城,為什麼要襲擊這些地方?答案簡單而殘酷,美國要在最大程度上搞亂中國,盡全力摧毀中國的戰爭潛力。
好比個舊,這本是一座時至今日除了雲南人之外大部分國人幾乎從未耳聞的城市,然而在美國人的計劃中,這裡卻被部署了2枚核彈。為什麼?因為箇舊是以生產錫為主併產鉛、 鋅、銅等多種有色金屬的冶金工業城市,是中外聞名的“錫都”。
所以美國就要把它摧毀。
再比如雅安,這是一座山城,倘若不是曾於過去歷經地震浩劫,我們興許同樣不會有很多人瞭解這個名字,但是,這裡也被美國人部署了兩枚核彈,這又是為什麼?
因為雅安是成都平原進藏的交通樞紐,是川藏茶馬古道的起點。試想一下,1956年美國人提出該計劃的時候西藏在和平解放之後真的安寧了嗎?並沒有。那時尚未掀起“暴動”的達賴還在心心念念著他的“高原自立”,那麼中蘇美三國混戰的背景下,進藏樞紐雅安的失陷是否就代表著再起“佛國”的“宏願”時機以到?
言盡於此,我們自然會再度感受到美國的喪心病狂。
3,
“核訛詐”,這是“核威懾”理論的重要分支,指的是擁有核打擊力量的某個國家或軍事集團,利用擁有的核武器對其他國家進行的以核攻擊為背景的恐嚇或威脅行為。
而應對“核訛詐”的有效手段屈指可數,最有效的就是“確保互相毀滅”,即同樣擁核。朝鮮戰爭爆發之初,杜魯門在一次記者釋出會上向世界宣佈:“一旦中國參與朝鮮半島上的戰爭,那麼美國將在必要時動用任何武器。”
當記者詢問是否包括原子彈時,杜魯門的回答是:
“任何,你明白任何是什麼意思嗎?”
沒錯,這就是他阻止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參戰的“方法”,是赤裸裸的“核訛詐”。
面對核訛詐,毛主席喊出了“他打他的原子彈,我打我的手榴彈”這般振聾發聵的口號,一舉戳破美帝“紙老虎”的本質。但與此同時,我們終究不能否認原子彈的巨大威力令其存在本身足以成為一種“立國”之本。
正因如此,在朝鮮戰爭告一段落的1954年1月末,毛主席在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上,做出了中國要研製原子彈的戰略決策。
曾經,赫魯曉夫在與我們長期交涉後,終於答應給予新中國“合適的”核武器技術,而至於什麼是合適的,就像蘇聯專家在當年告訴我們的那樣:蘇聯有氫彈,完全可以保護中國,中國沒有必要造千萬噸級的。
對此,我們給蘇聯專家的回應是中國的一句老話: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
沒錯,關於蘇聯擁有世界上當量最大的氫彈這點,我們並不否認,但是蘇聯能夠永遠擁有氫彈,而中國卻只能擁有蘇聯“借給”我們的氫彈,蘇聯說自己可以充當中國的保護傘,但是誰又能保證這把保護傘不會在將來某天成為刺入中國咽喉的利劍?
沒有劍和有劍不用是兩回事。
上世紀50年代末,由於中蘇之間在“聯合艦隊”、“三和主義”、“修正主義”等一系列問題上產生嚴重分歧,雙方關係最終在短暫的蜜月期後走入低谷,蘇聯一口氣撤走了中國境內所有專家,撤銷了所有援建專案,其中自然包括“核物理研究”。
蘇聯專家撤走那年的世界,除了美蘇英三國之外,即便是法國的核武器也仍處於研發階段,而那時新中國剛剛完成“一五計劃”,整個國家的工業化水平還處於初級階段,不客氣的說,那時的中國一窮二白,幾乎還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
然而,正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戈壁灘上的戰士們無怨無悔,核武器研發的關鍵階段適逢國家遭受“三年自然災害”,物資供應不上戰士們就挖野菜,吃樹葉,喝鹽鹼水,把充足的配給留給科研工作者。
而“兩彈一星元勳”與其他科研工作者們也甘願一生隱姓埋名,他們演算的稿紙足以鋪滿整個羅布泊,用算盤生生打出了,蘇聯專家口中“不用計算機要花上兩年時間才能完成”的正確資料。
“死亡之海得玉漿,天山為屏崑崙障。縱橫南北十萬裡,敢問驚雷何日響。”
這首詩出於影片《橫空出世》中李雪健老師扮演的馮石將軍之手,詩中道盡了馮石將軍對原子彈轟鳴在羅布泊奏響的殷切期望,也同樣說出了當年所有人對核武器研製成功的期望。
1964年10月16日,一棵蘋果樹在羅布泊的茫茫大戈壁灘上抽枝發芽,茁壯成長,那種十年如一日的盼望也終於有了結果。
10、9、8......3、2、1,起爆。
當原子彈綻放出讓太陽都為之失色的光芒,那副場景,一如毛主席1935年所作《念奴嬌·崑崙》一詞中雲:
橫空出世,莽崑崙,閱盡人間春色。
飛起玉龍三百萬,攪得周天寒徹。
夏日消溶,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
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
而今我謂崑崙: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
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
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
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
從此,史學家要把中國的歷史分成兩段來寫,新中國這個立國15年的稚嫩國度也終於能夠從求生存變為求發展。
終於能夠在面對“大規模報復戰略”,面對“外科手術”的威脅時昂首挺胸,說出那句:
“NO!QN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