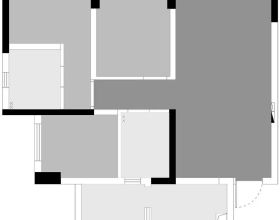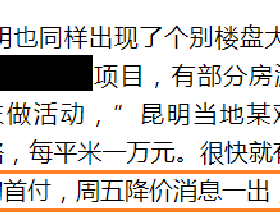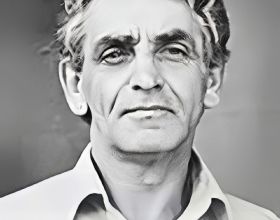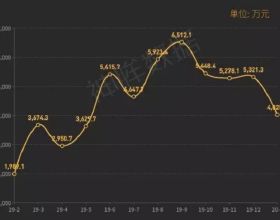歷史上族稱的由來經歷了複雜的演變,它承載了民族和周邊族群特別是中原王朝交往交流交融的融合歷史和族群記憶,畲族族群的由來也不例外。從唐至明朝的歷史記載中,我們清楚地看到“畲”最早表示田土型別、耕種方式和居住方式,在唐宋因文人士大夫的關注而開始發展成為人群的稱呼,經歷了宋元之際“畲”與統治的互動和元代制度中較為穩定的指稱和地理範圍擴大,明代的“畲”更多用於指代東南山區的特定人群,連結了特定的反抗、接受、適應的融合過程以及王朝的統治歷史。“畲”的含義變遷既是東南地區民族融合早期歷史圖景的一個真實寫照,也是東南原始居民融合成為中華民族一部分的一個發展階段。
相較於中原王朝的文字傳統,南方族群較少有文字資料保留下來,而我們能窺見的南方先民活動痕跡記載,多來源於現存的歷朝正史等記敘。這種漢族精英或者統治者對於他們的描繪,始終都是來自族群外部,不可避免地受到書寫者、書寫方式和流傳的限制。特別是中古時期南方地區各民族和族群的分類,很可能不同程度地均出自華夏特別是華夏士人的“文化創造” 。在這一表述下,唐宋之前南方族群的演變經歷了從越民族群體、苗蠻族群到山越、僚、俚、夷洲人、烏滸人、豫州蠻、荊雍州諸蠻、莫徭蠻等群體的分化,唐宋時期進一步融合與分化,形成了諸多不同族群。其中就包括東南山區的畲族先民。與大部分南方族群一樣,刀耕火種的遊耕風俗是他們最明顯的標識之一。現多認為,至遲在7世紀,聚居在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區的一部分山民,被統治者或漢族精英稱作“蠻僚”“峒僚”等,而後在接下來的十來個世紀不斷往周邊特別是東北方向遷移至閩東北、浙南,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 。而以“畲”為主體有關畲民的記載也在清至晚近的資料中大量顯現了出來。雖然南方少數民族的族稱多來源於中原王朝和華夏士人的“文化創造”,但歷史上族稱的由來卻經歷了複雜的演變,它承載了民族和周邊族群特別是中原王朝交往交流交融的融合歷史和族群記憶。筆者從“畲”這一族稱早期演變的歷史出發,管窺中原王朝以及士人對這一群體的主觀認識過程。
一、唐宋時期南方族群的命名與族稱“畲”的出現
1. 南方族群與王朝接觸
南方族群在中古人口南遷、經濟重心南移等歷史背景下得到了中原王朝比以往更多的關注。唐代士人對南方地區稱之為“俚、僚、蠻”等族群的地理位置、社會狀況、風土人情等描述,多與前史相同。新舊《唐書》中關於唐代南方民族史的撰述內容豐富,所載部族眾多,除前史中已有記載的林邑、婆利、盤盤、真臘等,還出現了南詔、陀洹、訶陵、墮和羅、墮婆登、東謝蠻、西趙蠻、牂牁蠻、南平獠、東女國、南詔蠻和驃國等民族,這與少數民族的發展演變以及唐代廣泛的民族交往不無關係。隨著中原王朝統治的擴大和經濟中心的南移,中原王朝與南方族群也不可避免地產生接觸。就中南、東南地區而言,史籍中記載了王朝與嶺南、今江西、湖南等地非漢人群的衝突,如:
(唐玄宗天寶元年)嶺南五府經略綏靖夷、僚,統領經略、清海二軍。
(僖宗中和二年)五月,以湖南觀察使閔勗權充鎮南節度使。(鹹通六年,置鎮南軍於洪州。閔勗時據潭州,而以洪州節授之,欲使之與鍾傳相斃也。)屢屢求於湖南建節,朝廷恐諸道觀察使效之,不許。先是,王仙芝寇掠江西,高安人鍾傳聚蠻獠,依山為堡,眾至萬人。仙芝陷撫州而不能守,傳入據之,詔即以為刺史。至是,又逐江西觀察使高茂卿據洪州。朝廷以淮本江西牙將,故復置鎮南軍,使勗領之;若傳不受代,令我因而討之。不知朝廷意欲鬥兩盜使相斃,辭不行…… [6]8497-8498
福建也有相關的敘述,但既有衝突,也包含了合作關係。例如昭宗景福元年“範暉驕侈失眾心,王潮以從弟彥復為都統,弟審知為都監,將兵攻福州。民自請輸米餉軍,平湖洞及濱海蠻夷皆以兵船助之。” 昭宗乾寧元年“黃連洞蠻二萬圍汀州,福建觀察使王潮遣其將李承勳將萬人擊之;蠻解去,承勳追擊之,至漿水口,破之,閩北略定。潮遣僚佐巡州縣,勸農桑,定租稅,交好鄰道,保境息民,閩人安之。材料中不僅包含了衝突,也提及“濱海蠻夷”兵船相助,或許正是由於這一段較早合作歷史,在後來許多畲民的自敘材料中,都監王審知也和畲族先民的由來相關聯。
正史記敘了許多“夷”“僚”“蠻僚”“嶺海群盜”“洞蠻”“峒寇”“溪峒蠻”等群體的活動,豐富度遠遠超過前代,這體現了中原王朝和南方族群接觸加深。但接觸早期,衝突難免發生,這些南方族群常常是以動亂的形象出現在王朝的視野中,僅偶有合作。王朝也開始在這些地方設定管理機構,管轄和收編包括各種族群在內的山民。在不同人群的接觸、衝突與融合中,中原王朝對南方族群的命名隨著統治的擴大和南移而逐漸變化和細化,這一時期,作為族稱的“畲”隨著士人的命名也開始出現在南方族群的相關描述中。
2. 唐宋文人筆下的“畲”與南方畲田人群
《詩經》的《周頌·臣工》中便有“如何新畲”,《周易·無妄》中有“不耕穫,不採畲”的說法。據許慎《說文》所釋,“不蕃畲,從田餘聲(以諸切)”,《集韻》所解,“畲,火種也,詩車切”。“畲”有兩個讀音,“yú”是指代耕種兩至三年的田,“shē”是指用火燒田。
東晉陶淵明曾寫“茅茨已就治,新疇復應畲”這裡的畲還是指代耕種行為。到了唐宋文人筆下,畲的意義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兩個讀音的意義已經發生了融合,如:李商隱“燒畲曉映遠山色,伐樹暝傳深谷聲” ;貫休“燒侵姜芋窖,僧與水雲袍。竹鞘畲刀缺,松枝獵箭牢” ;劉禹錫“照山畲火動,踏月俚歌喧” “銀釧金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畲;李德裕被貶往嶺南的路上所做“五月畲田收火米,三更津吏報潮雞” ;陸游“煙寺高幡出,山畲一老鋤” 。
出現在嶺南路上、武陵、武夷等地的詩句中和中南、東南山區密切相關的“畲”,是山田的一種,其在詩文中的出現一般都伴隨著刀耕火種的生產方式,有時候又和族群聯絡在了一起。不僅是“俚”人有參與,接受王朝統治的漢民士人也有參與。蘇洵“重祿無意取,思治山中畲。往歲栽苦竹,細密如蒹葭” ,其中“畲”指代山田,而他自己亦在其中從事農業活動。雖然東南、中南山區具體的人群變化路徑在中原王朝的正史中不可知,但唐宋時期這一地區已經存在大量山民的農業活動,特別是與“畲田”有關的活動。
這種畲田行為也被人們關注,在唐代南嶽玄泰禪師所做歌謠中,已經將“畲”加入對人群的稱呼:“畲山兒,畲山兒,無所知。年年斫斷青山嵋。” 玄泰禪師所呼的“畲山兒”,就是對這些在衡山中耕山畲田、不斷遷徙的南方族群的一種稱呼。這時“畲”的意義已經從指示田土型別和耕作方式變成了指代人群。
3. 族群“畲”的命名與東南山區的社會互動
現在的研究多認為,“畲”作為族群稱謂在漢文典籍中最早出現在南宋時期,被用來稱作居住在粵、閩山地的早期畲民。王象之《輿地紀勝》中稱梅州地區“菱禾,不知種之所出,自植於旱山,不假耒耜,不事灌溉,逮秋自熟,粒粒粗噎,間有糯,亦可釀,但風味差,不醇。此本山客輋所種,今居民往往取其種而揖之”。“輋”為“畲”異體字,用於表述其居住方式,學界多認為“畲”在現存文字中作為族稱出現始於此。
劉克莊的《漳州諭畲》是研究畲民極為重要的一篇文獻,其中提供了南方許多當地山區先民的資料:
漳尤閩之近裡,民淳而事簡,樂土也。然炎紹以來,常駐軍於是,豈非以其壤接溪峒,茆葦極目,林菁深阻,省民山越往往錯居,先朝思患預防之意遠矣。凡溪峒種類不一:曰蠻、曰徭、曰黎、曰蜑,在漳者曰畲。西畲隸龍溪,猶是龍溪人也。南畲隸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贛,奸人亡命之所窟穴。畲長技止於機毒矣,汀、贛賊入畲者,教以短兵接戰,故南畲之禍尤烈。二畲皆刀耕火耘,崖棲谷汲,如猱升鼠伏,有國者以不治治之。畲民不悅(役),畲田不稅,其來久矣。厥後貴家闢產,稍侵其疆,豪幹誅貨,稍籠其利,官吏又徵求土物蜜蠟、虎革、猿皮之類。畲人不堪,枉於郡,弗省,遂怙眾據險,剽掠省地,壬戌臘也。
文天祥《知潮州寺丞東巖先生洪公行狀》也提及與漳州、汀州接壤的潮州地區畲民:“(鹹淳五年)潮與漳、汀接壤,鹽寇、輋民郡[群]聚,剽劫累政。以州兵單弱,山徑多蹊,不能討。公應變設奇,降者相屬。又欲於接境置屯,多者三百人,少者二百人,掎角為援。郡為創撙節庫以贍之,具有條劃,悉以言於朝,並下之漳、汀放此,且嚴保伍之令,以澄其源。大抵公智慮深達,如宿將持重,而規劃綿絡,不以鄰為壑也。”
中原王朝和士人隨著對南方山民的瞭解逐漸增多,對分佈在不同地域的群體也進行了細分。據劉克莊、文天祥的表述,“畲”只是其中的一種,其分佈於包括漳州、潮州在內的東南地區,而在漳州至少也有不同的兩種畲名,在山中居住生活,刀耕火種,也有部分亡命之人逋逃至此。這些群體本不受統治管轄,有著自己的領地,以往統治者都是以“不治治之”。而隨著地方的開發,當地的家族、豪強在開闢產業的過程中對他們有了利益攫取,官吏也開始向他們徵收貨物,在此過程中群體之間、“畲”與官府之間常產生衝突。這都表明,在東南山區群體之間、群體與國家之間的互動中,群體之間的接觸逐漸加深。“畲”也在這些過程中,被統治者及士人用作族稱。
當然這裡的“山客輋”、漳州的“畲”、潮州的“輋”不能完全等同於畲族先民,但毋庸置疑,唐宋以前在東南山區不斷變動的畲田群體的一部分在此時得到了士人和知識分子的關注和命名。他們或是來源於早就遷居於此的山民,或是歷次離亂中逃脫管制的齊民。而隨著此時國家對南方族群開始從“不稅”到編戶的漫長歸化過程,“畲”也開始被逐漸構建成了管制下的與漢民不同的群體。
二、宋元戰爭與元代記載中“畲”群體的書寫
1. 宋元戰爭中的“畲軍”“畲兵”
《漳州諭畲》可視為國家統治與畲民在史料記載中的第一次具體的互動,而“畲”的活動也在宋末和元明的史料中記載漸多。宋元應是“畲”發展的重要時期,隨著政治經濟中心南移,南方山區從遠畿之地變成了近治之所。這一時期,被稱作“畲”的群體,頻繁參與了與國家的互動。
《宋史·張世傑傳》中記載,在宋末的宋元戰爭中,張世傑麾下有陳吊眼和許夫人的“畲兵”,於德祐二年(1276)進攻已經降元的蒲壽庚,但未能成功:“四月,從二王入福州。五月,與宜中奉昰為主,拜籤書樞密院事。王世強導大軍攻之,世傑乃奉益王入海,而自將陳吊眼、許夫人諸畲兵攻蒲壽庚,不下。十月,元帥唆都將兵來援泉,遂解去。”
文天祥麾下亦有“畲軍”。丁丑年(1277),文天祥四處征戰不利,諸多地方已有人歸順元朝,“畲軍”亦軍心不穩。同年,張志傑再攻泉州。《宋季三朝政要》中記載蒲壽庚偷偷賄賂“畲軍”而使得張世傑攻城不力被擊退:
六月,文天祥兵至吉州,戰於鍾步不利,戰於永豐又不利,戰於空坑大敗。未幾,攻贛之兵又敗……天祥與長子道生、客杜儲以數騎免時處置安撫,聚兵數萬在永豐境。天祥引兵就之,其軍亦潰。收散兵復入汀。而南劍、建寧、邵武多有歸正者。諸畲軍皆騷動,尋為大兵收復。天祥兵出會昌,趨循州。是冬,朋兵屯南嶺。是月,大元兵檄戍,張世傑回潮州以圖興復。
七月壬申,張世傑圍泉州將淮軍及吊眼、許夫人諸洞畲軍,兵威稍振,蒲壽庚閉城拒守。興化陳瓚起家丁民義五百人應世傑。八月,謝洪永任進攻泉州南門不克,而蒲壽庚陰賂畲軍,攻城不力。而求救於唆都元帥,王績翁亦遣人至唆都處趣兵。十一月丙申,唆都元帥大兵至福州。甲辰至興化,守臣陳瓚不降,城陷,大軍屠城三日乃止,血流有聲,車裂瓚,五門以徇。至泉州,張世傑解圍去。
文中可見,中原王朝記載中的“畲軍”“畲兵”並非宋軍官方軍隊,而是數支搖擺的地方武裝。或因他們並沒有產生如文天祥、張世傑對宋朝正統的認同,其對元的抵抗並不是十分堅定。從“福建之畲軍”作為“不出戍他方”的鄉兵被介紹在元代兵制中 ,我們或可推測至少部分被稱作“畲”的地方武裝後來受到了元代統治者的管轄。
2. 元代敘事中“畲”與統治的對抗與合作
雖然史書中記載“畲”在宋元戰爭中的態度曖昧,但其也因宋元之際與宋元兩朝勢力的互動而進入了正史的書寫。這種書寫在某種意義上從外部製造了一定的身份認同,使得“畲”這一群體在元代史書的記敘中十分活躍,而前史提及的其他族稱幾乎都在這一區域的王朝記載中減少或消失,“畲”成為東南山區中一類重要的人群。元代南方的民亂似乎從未停止過,而作為並非齊民的“畲”,也常常與統治產生對抗,元代統治者亦有將其納入統治的努力。
據《元史》記載,元朝建立早期,“畲”的抗爭尤為激烈,其中因部分人群參與宋廷抗元而受到元代統治者的關注:至元十五年十一月辛丑,“建寧政和縣人黃華,集鹽夫,聯絡建寧、括蒼及畲民婦自稱許夫人為亂。詔調兵討之。”
抗元的地方武裝中,黃華是頗為曲折的一支,其早期組織“頭陀軍”聯絡許夫人抗元。但隨即被元軍招順,轉而攻擊另一撥抗元力量。隨後再次“反元復宋”,以失敗告終,而元廷收編了其勢力。至元二十二年八月,“令福建黃華畲軍有恆產者為民,無恆產與妻子者編為守城軍。” [22]279
宋元之際,東南地方政局十分複雜,地方豪強常在南宋小朝廷和蒙元之間左右不定。較為知名的如陳五虎因助元有功而被封官加爵,而陳吊眼、陳桂龍等被稱作“畲”的山民集團即因抗拒元軍而被撲滅。平亂與招安,似乎是王朝統治進入一個地區必不可少的過程。元初至元年間,不斷有被稱作“畲”的群體爆發動亂:
(至元二十五年三月)甲寅,循州賊萬餘人寇漳浦,泉州賊二千人寇長泰,汀、贛畲賊千餘人寇龍溪,皆討平之。
(至元二十六年正月)畲民丘大老集眾千人寇長泰縣,福州達魯花赤脫歡同漳州路總管高傑討平之。
(至元二十七年六月)廣州增城、韶州樂昌以遭畲賊之亂,並免其田租。
元代統治者亦不斷用一些政策對其進行招安:
(至元十六年五月)詔諭漳、泉、汀、邵武等處暨八十四畲官吏軍民,若能舉眾來降,官吏例加遷賞,軍民按堵如故。以泉州經張世傑兵,減今年租稅之半。
(至元十七年十二月)壬辰,陳桂龍據漳州反,唆都率兵討之,桂龍亡入畲洞。
(至元十九年五月)招諭畲洞人,免其罪。禁差戍軍防送,禁人匠提舉擅招匠戶。
(至元二十一年八月)甲子,放福建畲軍,收其軍器,其部長於近處州郡民官遷轉。
在皇慶、元貞年間的記敘中,我們可以看到,“畲”參與到當地的屯田:
(皇慶元年)十一月戊戌,調汀、漳畲軍代毫州等翼漢軍於本處屯田。
汀、漳屯田:世祖至元十八年,以福建調軍糧儲費用,依腹裡例,置立屯田,命管軍總管鄭楚等,發鎮守士卒年老不堪備征戰者,得百有十四人,又募南安等縣居民一千八百二十五戶,立屯耕作。成宗元貞三年,命於南詔、黎、畲各立屯田,調撥見戍軍人,每屯置一千五百名,及將所招陳吊眼等餘黨入屯,與軍人相參耕種。
縱觀元代的記敘,“畲”似乎發展出一些固定的組織。“畲洞”或是指代特定的聚居地。“八十四畲”的官吏軍民,雖不知是元代統治者的建制還是民間習慣中特定的命名方式,但書寫者對“畲”已然有了穩定的定義。部分畲軍也聽從統治者的調配。元代的軍屯有諸多畲軍的參與,是這一地區這一人群進入王朝的重要方式,也是王朝管理的重要手段。與此同時,“畲民”“畲賊”等反抗的記敘在同一時空也從未停止。“畲”成為文字記錄者筆下一個與統治亦近亦遠的符號,王朝和“畲”有著十分複雜的互動關係。
在這一時期,被稱作“畲”的群體也並非一個整齊、穩定的人群構成。《元一統志》中載,宋代以來汀州山區有民“黨與相聚,聲勢相倚,負固保險,動以千百計,號為畲民”,實際上是“江右、廣南遊手失業之人逋逃於此。”雖然從文字來看,統治者試圖將“畲”納入版圖,元代統治者亦多次招安“畲”,編為軍、民,但這似乎並不是一個順利的過程。書寫者對“畲”事蹟的主要敘述,還是與起義、呼應、平亂、招安相伴隨。但隨著該地區的多次叛亂和平定,文字中被稱作“畲”的群體與齊民之外的各地“民賊”相區分,成為東南山區最主要的非漢族群體,記載出現的區域與前朝相較,也擴大到括蒼、泉、汀、邵武、廣州、韶州、贛等浙江、福建、湖南、廣東及江西各處。
三、明代東南山區的社會整合和“畲”的建構與認同
1. 東南山民稱呼的多元記敘與“畲”的指稱
雖然元代史料中,東南山區的“畲”似乎是在這裡主要活動的人群之一,而且也有穩定的建制和指代。但或受華夷之辨的影響,或因畲至此未能形成穩定族群,明王朝和明代知識分子對居於此地的化外之民稱呼並未承襲元代以“畲”為主的記載,反而回到了多元稱呼的時代,這一時期歷史記載也清晰地出現了接受、適應、反抗的涵化過程。
顧炎武記敘了東南山區的不同地域中這些非漢人群的稱呼,如閩中的“漳猺”“山首峒丁”等:
猺人,楚、粵為盛,而閩中山溪高深之處間有之。漳猺人與虔、汀、潮、循接壤錯處,亦以盤、藍、雷為姓。隨山種插,去瘠就腴。編荻架茅為居,善射獵,以毒藥塗弩矢,中獸立斃……國初設撫猺土官,令撫綏之,量納山賦……今山首峒丁,略受約束,但每山不過十許人,鳥獸聚散無常所,漢網當寬之爾。
廣東的“輋”“猺”特別是潮州的“畲猺”“山輋”“猺獞”等:
猺本盤瓠種,地界湖、蜀溪峒間,即長沙、黔中五溪蠻,後滋蔓,綿亙數千裡,南粵在在有之……粵人以山林中結竹木障復息為輋,故稱猺,所止曰輋……其姓為盤、藍、雷、鍾、苟,自相婚姻,土人與鄰者亦不與通婚。猺有長有丁。國初設撫猺土官領之,俾略輸山賦,賦論力為準,羈縻而已。今猺官多納授,從他邑來兼攝,亦不常置。
潮州府畲猺,民有山輋,曰猺獞。其種有二:曰平鬃、曰崎鬃。其姓有三:曰盤、曰藍、曰雷……我朝設土官以治之,銜曰輋官,所領又有輋。輋當作畲,實錄謂之畲蠻。
謝肇淛《長溪瑣語》亦記錄了太姥山中火種的“畲人”:“過湖坪,值畲人縱火焚山,西風急甚,竹木迸爆如霹靂。”
明代史書中也是對不同的地區、人群有著不同的命名:
(福建漳州府)漳平……南有百家畲洞,踞龍巖、安溪、龍溪、南靖、漳平五縣之交。
(嘉靖四十三年)潮州倭二萬與大盜吳平相掎角,而諸峒藍松三、伍端、溫七、葉丹樓輩日掠惠、潮間。閩則程紹祿亂延平,梁道輝擾汀州。
他們當中的部分人群與王朝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如廣東“畲蠻”:
(永樂五年十一月)廣東畲蠻雷紋用等來朝。初,潮州衛卒謝輔言:“海陽縣鳳凰山諸處畲蠻,遁入山谷中,不供徭賦,乞與耆老陳晚往招之。”於是,畲長雷紋用等凡四十九戶,俱願復業。
相較於宋及之前的稱呼,明代的族稱也因地域、身份、與王朝關係不同而精細化起來。因更多的國家力量、人群互動在東南山區發生,明代“畲”已經基本用以指代人群。“畲”的稱呼,有多處明確的來源。其中有明確管轄甚至設立機構管制下的民,也有“羈縻”之下的人群,他們或“量納山賦”,或“略輸山賦”,或“歲納皮張”。還有文人筆下描繪出其獨特風俗的地區及人群:“依山而居,採獵而食,不冠不履”,自相婚姻的廣東畲蠻;“百家畲洞”的漳平之南;福建北部,太姥山中的畲田人群,也被士大夫稱之為“畲人”。
2. 畲“賊”的王朝表達與反抗者的族群認同
這一時間南方存在著眾多反叛者,“畲”亦是其中的一支。其族稱被賦予了更多的政治上象徵意義。王朝建構了“畲”的反面形象。明正德十一年(1516)爆發的南贛地區起義,一直被學界認為是明代規模最大、最有代表性的一次以畲民為主的起義,給王朝帶來了一定的麻煩,明政府派出王陽明巡撫南、贛、汀、漳等處,來鎮壓起義:
(武宗正德)十二年二月,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檄四省兵備官選募民兵操練。初,陳金討桃源、華林諸賊,多所招撫,未大示懲處;又民間父兄被殺者,不得報仇,時相垢訾,諸兇不自安轉徙嘯聚,不數年仍起為盜。又南贛地多山險,易為巢穴。南安、橫水、桶岡諸寨,有賊首謝志山、藍天鳳,漳州、浰頭等寨有賊首池大鬢等。於是福建、江西、湖廣、廣東之界,方千里皆亂。兵部尚書王瓊知守仁才,特薦用之……
冬十月,王守仁討汀州左溪賊藍天鳳等,平之。天鳳等與贛南下新、秔下等洞賊雷文聰、高文輝等盤據千里。
谷應泰曰:“正德濁亂,群盜蜂起,而江西之盜有五:大帽山者號贛賊;仙女寨、雞公嶺號華林賊;瑪瑙寨、越王嶺者號靖安賊;王浩八為桃源賊;樂庚二、陳邦四為東鄉賊……至正德十一年,而南贛賊黨略平。皇靈未暢,苞櫱旋萌,於是江西之賊復有四:藍天鳳等為左溪賊,謝志山等為橫水賊,鍾景等為桶岡賊,池大鬢等為浰頭賊。”
如文所見,這些起義者多被稱“賊”,王陽明亦稱四省交界的“亂民”為“輋賊” [29]。受到中原夷夏觀薰染的文人士大夫,也開始對“畲”的根源進行追溯,對他們的祖先、姓氏、生活方式等開始關注,但也往往記載了他們野蠻未開化的特點,如對其祖先形象歧視性的表達,喜仇殺、好訟、狡黠等負面形象也多出現在這時中原士人的描述中 。而明人編寫的《宋史紀事本末》中也將同張世傑一同作戰的陳吊眼、許夫人所統“畲軍”“畲兵”稱之“諸峒畲賊”。這一表達無疑是表明明王朝主位的價值取向,尋找鎮壓起義的“合法性”,而將反抗者建構為負面形象。
反抗者群體,也利用一些相關的文化符號,構建起了自己的群體認同。南贛地區起義首領謝志珊、藍天鳳自稱盤皇子孫,利用盤皇信仰發動了擁有相同信仰的周邊人群,“避役逃民”和“百工技藝遊食之人”都雜處於內,聲勢浩大 。這種身份標籤或符號在對統治反抗的組織上是有效的,也擴大了族群來源。“畲”作為一種政治身份認同(politicalidentity) [32],其起了雙向作用:不僅原有的“畲”等族群會被統治所影響而被王朝建構,而且被稱為“賊”的粵、閩、贛遊民和亂民也進入山地,接受其信仰與習俗,成為“入畲”之人,進入到這個標籤內,參與到反抗之中。在“平亂”期間,部分起義軍被殺,部分被招安,在地方上也有新縣如崇義縣、和平縣的設立,減稅等政策隨行 。在“平亂”結束後,新的地方行政中心成立,並整合新民進入地方社會時,族群邊界會被統治者有意打破。大部分山民隨著南方山區動亂的平定進入地方社會成為齊民,但仍有少部分人群還會踐行原有的信仰、習俗、姓氏等禮儀和身份標識,繼續在山地進行刀耕火種的生活,並不斷遷徙,不僅因他們的原始耕作方式仍需要年年拋荒,更是出於逃避賦役、戰亂、尋求生計等政治經濟原因考慮。
這種情況在13-16世紀的東南山區的互動中一直適用,這一時間這一群體不斷地經歷著變動。分佈在浙、贛、閩、粵的“畲”等非漢人群不僅有歸附與抗爭,繼續了與中原王朝漫長的磨合過程,而同時東南山區的群體也在互動中逐漸分化與固定,“畲”的概念因為這些對抗的歷史過程保留在了王朝的敘事中。而在山區活動的這些群體在明清之際直至晚近定居於閩東浙南後,漸漸退出與王朝對抗的歷史,進入到地方社會的發展與生計中。伴隨著東南山區的發展,他們因獨特的習俗、文化而再次被地方士人們關注,族稱“畲”在17世紀後進入地方書寫,在地方史志中大量被使用也就不令人意外。
四、結論
在中國歷史上,少數族群與王朝接觸的過程中,會產生各種中原王朝主觀敘述下的族稱。這些族稱所承載的亦是這些民族和周邊族群特別是中原王朝交往交流交融的融合歷史和記憶。從唐至明朝的歷史記載中,我們清楚地看到“畲”從田土型別、耕種方式和居住方式在唐代開始發展成為人群的稱呼,宋代其用於漳州、潮州等地部分非漢人群的稱呼,經歷了宋元之際“畲”與統治的互動和元代制度中較為穩定的指稱和地理範圍擴大,明代的“畲”用於指代東南山區的特定人群,連結了特定的反抗、接受、適應的融合過程以及王朝的統治歷史。可以說直至17世紀,“畲”因為中原王朝士人的命名而用以指稱東南山區的特定山民。雖然其一直處於動亂與遷移的狀態,在歷次離亂中,史籍所指稱的“畲”的群體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這一族稱命名過程,正是東南地區民族融合早期歷史圖景的一個真實寫照,也是東南地區原始居民融合成為中華民族一部分的一個發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