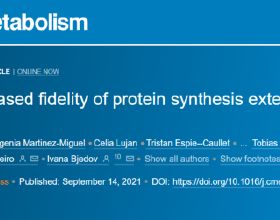《新居》
不足5平米的小臥室的拉門一貫的敞開著,母親面朝裡,一邊鋪著那洗得發白又打著補丁的床單,一邊喃喃的嘆道:“明年咱們就在大房子裡過年咯。。。”
我正好走過,從狹小的走廊裡看著她佝僂的背影,聽得出她語調裡夾雜著那種幸福的感覺,心頭卻泛起一絲酸楚。
眼下我和母親正居住的這個小戶型是建於八六年的老房子,全家攢錢零八年買的,兩個面積不大的臥室,沒有客廳;按母親的話說,好歹算是個獨立的套房,不用和鄰居共用一個廁所了。。。在那之前的二十六年裡,我們一家三口住在父親單位分的團結戶裡--一個很小的套二房,兩家分住共用衛生間,為了能在11平的房間裡住下三人,動手能力頗強的父親充分的利用了建築物的立體空間。。。從小學到高中的12年裡,我的書房就是一個兩平米左右的封閉陽臺:一張舊寫字檯,一個自制簡易書架,一幅貼在牆上被陽光曝曬得發黃的世界地圖。。。晚上的時候,屋子裡父母戴著耳機看電視;陽臺上我在臺燈下背書做題。。。至今依然清晰的記得冬季窗戶上結的冰花和望向窗外萬家燈火時自己的面孔映在玻璃上的黑漆漆的虛影。
高中時好友少發同學第一次來我家,離開後,他很真誠的跟我說了兩句讓我難以忘懷的話:“我一直覺得你心胸不夠開闊,原來是你住的房子太小了;你這麼嘮叨嘴,現在看來是隨你媽。” 我知道他說這話是為我好,可在當時卻是無法改變的現實。特別是母親的嘮叨,總是繞不開那個“房子太小”的主題,就像唐僧的緊箍咒,從我上學考試拿第一名時就開始念,小升初,升高中,保送大學,畢業找工作,,,一直唸到二零二零年初新冠病毒爆發前她作為代理人替當時正在智利常駐的我簽下這套的三居兩衛的新房。
去年十月份,新房一交付,我便啟動了裝修工程。一月份主體完工,我帶著父親去看新房。進門後,父親看到鋪好的地磚,粉刷好的牆面,封閉好的大陽臺,臉上一下子泛出那久違的笑容,乾癟黝黑的面板頓時神采奕奕,上一次見到他這麼開心大概還是十年前他給我前妻“改口費”的時候。父親曾是一名長途卡車司機。在那個沒有導航的年代,他拿著紙質地圖,一個人開著卡車從山東去福建等南方省份拉貨。那個時候,國營單位卡車司機的收入是和普通工人一樣的,到福利分房結束後,他就退養賦閒在家。他和母親的積蓄也只夠我上大學的費用,買房是一件不可企及的事情。我能理解他開心的緣由:老伴這四十年的“想住大房子”的心結,在他倆年逾古稀之時,終於被他的兒子解開了。。。
我猜想,旅行的基因也是會遺傳的。父親作司機的時候,駕駛長途卡車跑了大半個中國。而我因為專業是西班牙語,畢業後一直從事針對拉美市場的商務,為了開拓業務到過離中國最遠的智利和阿根廷;有時與同事結伴而行,有時一個人獨來獨往,再後來我帶領銷售和售後團隊駐紮在礦山小城蘭卡瓜。。。
母親一生節儉,縫縫補補,就是要攢錢買大房子。這會兒新房子是有了,按她的意思,傢俱電器甚至窗簾還是留用目前這個小戶型的,把更新換代的選擇權留給新房將來的女主人。。。此刻,我看著她瘦小枯乾的身型,不禁感慨,我與西班牙雕塑家蘇索在零二年九月定下的“加利西亞之約”才是這人世間最難實現的願景。二十年時光荏苒,百萬里拉美征途;艱難困苦,玉汝於成。
記敘二零二二年一月除夕前的一個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