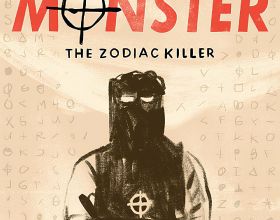如果命運讓我重來一次,我一定會選擇“撞大運”而不是“撞牆”。畢竟,2015年那次撞牆,為我悲催的腦殼埋下了伏筆。
我說的“撞牆”不是打比方,而是真的走路時不看路,感受了一下力和反作用力的博弈。又疼又懵的感覺逐漸消退以後,腫起了一個小包。
隨著時間推移,疼痛的感覺逐漸好了,那個小包卻依然沒有消退,按著還有點疼。想想為了這麼個小事去趟醫院挺沒必要,我選擇無視它。“也沒準哪天起床就消腫了吧。”
兩三年的時間裡,我一直和這個包和平共處。
摸摸額頭,它還在;但是大小和形態並沒有發生過多少變化,就是一個黃豆大小的凸起,按著也不怎麼疼了。
“也許是撞牆的時候有東西硌進去了?”我只是自己嘀咕,依然並沒有動過念頭去醫院看看。
(一開始,頭上的包還不那麼明顯。患者供圖)
但是到了2018年5月,事情開始不按照預期發展。我明顯感覺到這個包在長大,而且越來越凸起。
起初,它從黃豆大小長到了1釐米左右用了挺長時間,但增長速度越來越快。
更悲催的是,伴隨著年齡增長和遺傳因素,我的髮際線在那幾年間全面回撤,額頭的部分越來越閃亮。
除了每天早晨照鏡子的時候滿心迷惑外,身邊也有很多人開始注意到我不同尋常的外觀:“你這是真實版的‘腦殼有包’啊。”
這句略帶調侃的話,每天至少會聽到一次。周圍開始有人勸我去醫院檢查了。
那正是我工作最忙的時候,經常加班加點到昏天黑地。偶爾有一天能休息,也只想躺在床上補覺,“去醫院”這個念頭屢次提起,屢次被放下。
遇到勸我趕緊去就醫的人,我也只是跟他們嘴硬:“你見過老壽星嗎?那額頭也是凸起來一個包的,裡頭裝的都是福壽……”
後來回憶起當時心情,我也十分驚訝:拖延症和諱疾忌醫帶來的心理負擔如此強大,竟然能讓這“腦殼有包”的詭異造型伴隨了一個人五年多。
2019年5月,額頭上那個最開始只有黃豆粒大小的“不明腫物”已經今非昔比,直徑長到了3釐米左右,而且位置在我腦門的正中間,想選擇忽視它都不行了。
除了影響容貌,凸起在額頭上的大包牽拉著頭皮造成壓迫感,我會時常感覺到腦袋悶悶的不舒服。
而且這個腫塊越長越大但性質不明,難免讓我心裡嘀咕,自己會不會是得了“腦門兒癌”之類的絕症啊……不行,還是去醫院吧!
(患者頭上腫起的包愈發明顯。患者供圖)
終於鼓起勇氣走進醫院,血常規尿常規核磁心電圖做了一大圈,我收到了一個好訊息和一個壞訊息:
好訊息是醫生認為它是個良性的脂肪瘤,不是什麼“腦門兒癌”,也不會直接帶來生命危險;
壞訊息是,瘤子會繼續長大,或快或慢且不可控,我很可能早晚躲不過一場掀開頭皮的手術。
“現在核磁顯示瘤子還不算大,位置在額頭正中央。你暫時可以先回去觀察,如果它長太快,帶來的外觀改變或者其他不舒服影響你生活了,就只能動手術了。”醫生看著檢查報告說,“除了手術之外,也沒有什麼更好的干預手段。”
醫生一語成讖。
(患者頭上腫起的包越來越大。患者供圖)
2020年,額頭上的包體積越來越大,越來越凸起。悶悶的壓迫感逐漸變成了疼痛感,從一開始的額頭區域性隱痛,變成整個腦袋共振式、串聯式的疼痛,伴隨著難以忍受的眼睛發脹。
且這種疼痛的發作頻率也越來越高,半個月疼一次,每次疼一週;到了10月份,頭疼發作的時候我連入睡都很困難了。
也就是那時候,我完全理解了孫悟空的處境:為啥一身本領還害怕只會叨叨的唐僧呢?因為唐僧會念緊箍咒啊,緊箍咒能讓孫悟空疼得滿地打滾兒,正如這個瘤子能讓我疼得想撞牆。
“不忍了,不拖了,手術吧!”我暗暗下了決心。
2020年11月28日,在過完生日的第二天,我懷著一種悲壯的、任人宰割的心態,再一次走進了醫院。
“你能不頭疼嗎?這整個腦門兒都被它撐滿了!”醫生一邊皺眉頭看結果一邊說,瘤子“長得太快了”。
而且我這個瘤子長的位置還比較“缺德”,一來壓迫神經會造成頭疼和眼壓升高,二來有很大的靜脈血栓風險,如果形成血栓,分分鐘危及生命。
“你得住院。儘快安排手術把它切了。”醫生用筆敲敲我的病歷,語氣不容置疑。
(為了手術,我剃光了頭髮。患者供圖)
2020年12月3日是我的“大日子”,早晨8點被推進手術室,下午3點半才推出來。
後來我才知道,因為額頭上的脂肪瘤面積太大,手術時醫生只能先把我整個頭皮掀開,搞清瘤體分佈的位置,調整好手術方案,再把頭皮進行縫合,最終是“從髮際線裡頭掏著切除的”。
我腦袋上的刀疤長達12釐米,但醫生技術高超,把整個疤痕都埋在髮際線裡面,外表完全看不出來——我沒毀容。
而且,就算傷口這麼大,這依然還算是一個微創手術。“只要不開顱,就算微創。”聽了醫生這句話,我還是有一絲為自己慶幸的。
對我來說,7個小時的手術過程是整個治療中最不可怕的環節:打上麻藥,眼睛一閉再一睜,“多餘的東西”已經被切除得乾乾淨淨。
(手術後的我。患者供圖)
但是當麻藥退去,煎熬才真正開始。
術後7小時之內不能吃東西,也不能隨便活動,我忍!
可是傷口刀割一樣的疼痛完全不間斷,就算大劑量服用芬必得也無法緩解。
我幾乎是強行要求護士姐姐給了鎮痛泵,不然連一分鐘都睡不著;而這樣的疼痛差不多持續了一週。
此外,術後每三天需要換一次藥,總共換三次;換藥的過程彷彿是剛剛稍微長好的頭皮被重新掀開……不堪回首啊,不堪回首。
手術後第三天,我出院了。半個月後疼痛消失,我擺脫了“腦殼有包”的造型。一個月之後,傷口徹底痊癒,我才終於充滿儀式感地舒舒服服洗了個頭。
對了,這中間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出院後沒兩天,我整個右半邊臉全腫到皮膚髮亮,眼睛完全睜不開,我嚇得趕緊諮詢醫生,被告知是“面板積液”,腫脹是術後正常的現象。
(手術後眼睛完全睜不開的我。患者供圖)
當時我攬鏡自照,形象狼狽又好笑:為手術而剃的禿瓢鋥光瓦亮,髮際線裡橫亙著一道十幾釐米長的大刀疤。
整張臉腫得亮晶晶,右邊眼睛像個核桃……一副捱了頓胖揍的樣子。
自拍一張,我把自己最狼狽的樣子分享到好友群裡,如期收穫許多表示驚恐的表情包——不能我一個人受驚嚇,即使那個帶來驚嚇的人是我自己。
我始終不明白,為啥這個瘤子就找上我了,而且長在腦門正中央呢?是那次磕碰給它埋下了種子?我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讓它有機可乘?……還有,它會復發嗎?
但我的主治醫生說,脂肪瘤是個“致病機制尚不明朗”的病。
“不是你瞎吃吃出來的,更不是熬夜熬出來的,很有可能是基因裡帶的,也許你就是比別人更容易長這種瘤子。”
至於它長的這個位置,也沒什麼規律可循。脂肪瘤是有可能復發的,但也沒什麼更好的預防手段,“萬一又長了,再說吧。”
(手術在我頭頂留下的傷疤。患者供圖)
手術的疼痛逐漸在記憶中淡化,髮際線裡頭那道疤痕也被新長的頭髮慢慢遮擋起來。
意想不到的是,我收穫了一個令人開心的“副作用”:
臉上的皺紋明顯變得平滑了,尤其是抬頭紋一掃而光,眼角的細紋也有了很大改善——這普通的外科手術,竟然還做出了醫美的效果;手術檯上躺一遭,不僅切掉了撐滿整個額頭的大瘤子,還免費做了個“拉皮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