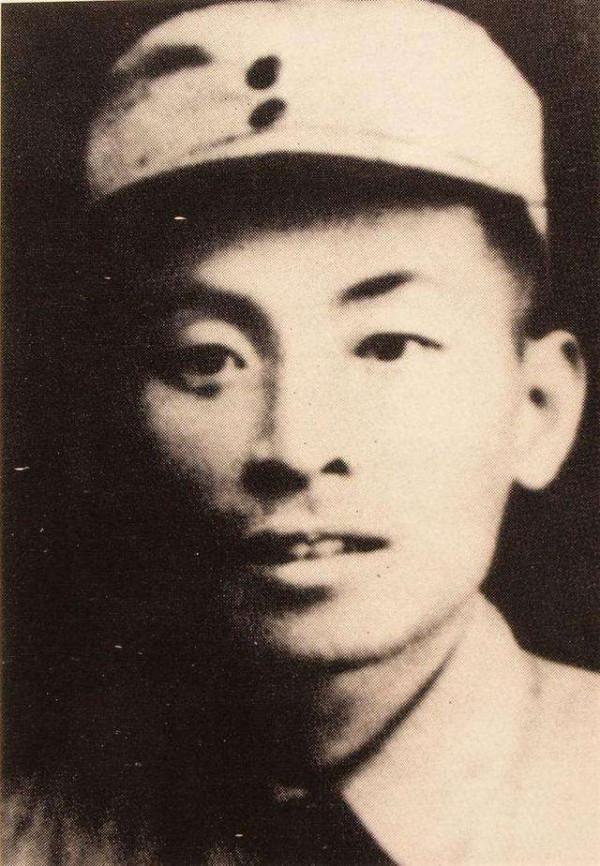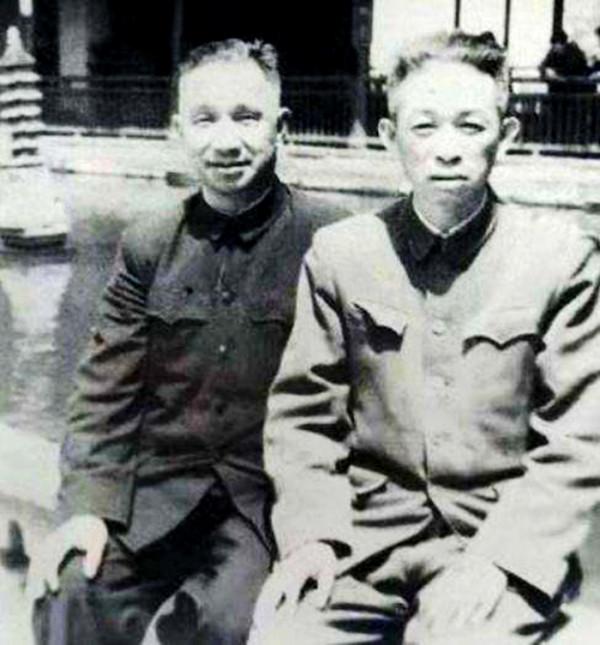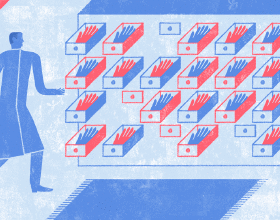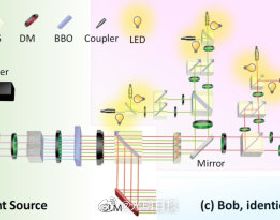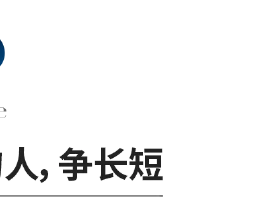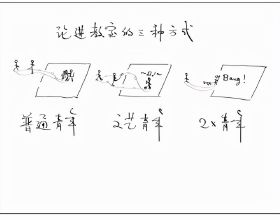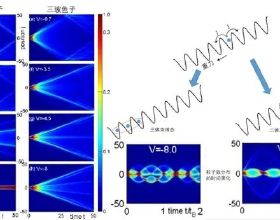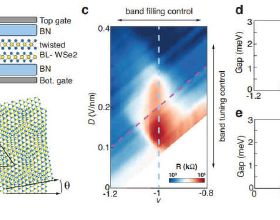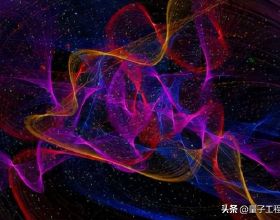新中國成立後,有位年輕的軍史工作者採訪葉飛上將,問:“江蘇抗戰和華東解放戰爭的史料裡多次提到‘葉王陶’,不知這個人是誰?他現在何處?”
葉飛大笑著,解釋道:“葉王陶,不是一個人,而是葉飛、王必成、陶勇三人的合稱。葉王陶不是‘桃園三結義’,從1940年夏開始,這三個縱隊一直並肩作戰,三個司令員的姓也就一直連在了一起。”
葉飛、王必成、陶勇三人,是粟裕將軍的手下愛將,也是陳粟大軍最初的班底,在新四軍和華野的很多電報、命令中,三位將軍的被合稱為“葉王陶”。“葉王陶”不但是華野,甚至在整個解放軍中都是有名的黃金組合。
葉飛的經歷比較傳奇,他是菲律賓華僑,回國後在廈門讀書,參與建立閩東革命根據地。紅軍主力長征後,葉飛在艱苦卓絕的環境中堅持三年游擊戰爭。
在“葉王陶”三人中,粟裕最早結識的就是葉飛。1936年秋,粟裕在閩浙地區打游擊時,曾經與葉飛打過交道,還因為一些誤解將其“誘捕”,不過這些往事並未影響二人關係。新四軍成立後,葉飛被任命為新四軍第6團團長。
王必成是湖北麻城人,是許世友的同鄉,早年出自紅四方面軍,參加了紅四方面軍從鄂豫皖到川陝的主要戰鬥歷程。長征結束後,進入抗大學習。
同王必成一樣,陶勇也來自紅四方面軍,他原名張道庸,出身於大別山區安徽霍邱縣,他的戰鬥經歷同王必成一樣,跟隨紅四方面軍一路征塵直到長征勝利。此後,陶勇隨軍參加西路軍,西路軍失利後,陶勇被馬家軍俘虜,後經黨組織營救方才返回延安。
新四軍成立後,為加強新四軍的領導,補充軍政骨幹,延安方面給新四軍派來一批幹部,陶勇、王必成都在其中。王必成任新四軍第1支隊參謀長,陶勇任第4團副團長,後來兩人都在戰鬥團擔任軍事主官,王必成任第2團團長,陶勇任第4團團長。
1938年6月,新四軍第1支隊(司令員陳毅)、第2支隊(司令員張鼎丞,副司令員粟裕)相繼挺進江南敵後。不久,第2支隊司令員張鼎丞返回延安。8月中旬,新四軍軍部決定第2支隊由陳毅暫時指揮。11月,正式成立新四軍江南指揮部,以陳毅、粟裕為正副總指揮,兩支部隊被捏合在一起。
在兩個不同的支隊分別擔任團長的葉飛、王必成、陶勇開始在一起建制內戰鬥,共同成為陳粟二位首長的部下。
率先打出名氣的是王必成。1939年3月,日軍將新四軍2團包圍在鎮江附近,王必成率軍在絕境中殺出一條血路,硬是透過不怕死的勁頭血戰突圍成功。此戰之後,王必成就有了“王老虎”的外號,2團也因此被譽為“老虎團”。
王必成
兩個支隊聯合戰鬥半年多,在敵後作戰200餘次,建立起10塊小型游擊區,部隊由1700多人發展到6000多人。
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決心跨越長江,進一步向江北地區發展,打通與南下八路軍的聯絡,開闢華中根據地。
正在華中的中央局書記劉少奇十分贊同這個意見,恰巧這時,國民黨頑固派、江蘇省主席兼魯蘇戰區副司令韓德勤所部8個團,向中原局機關所在的半塔集地區發動圍攻,陳毅命令葉飛火速馳援。葉飛不負眾望,擊潰了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反共摩擦。
劉少奇正在構思一盤經略華中的大棋,他知道國民黨頑固派不甘心失利,遲早還要反撲,他要求葉飛引敵圍攻、孤軍堅守、待援殲敵,這樣就可以讓南下的八路軍黃克誠部和北上的新四軍主力對國民黨頑固派進行合圍。
劉少奇要求葉飛堅守一個星期,但八路軍黃克誠部因日軍“掃蕩”不能如期趕到,新四軍張雲逸部也無法按期北上,葉飛一時間陷入困境。這時,陳毅命令陶勇率新四軍蘇皖縱隊日夜兼程急行軍200餘里,火速趕到戰場,終於化險為夷。
1940年7月8日,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渡江進入江北,改稱新四軍蘇北指揮部,由陳毅任指揮兼政委,粟裕任副指揮。
部隊整編為3個縱隊,葉飛擔任第一縱隊司令員兼政委,王必成擔任第二縱隊司令員;陶勇擔任第三縱隊司令員。
葉飛、王必成、陶勇聯手作戰的第一仗,就是黃橋決戰。
黃橋決戰是抗戰以來全國規模最大的反摩擦作戰,國民黨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糾集了3萬餘人的兵力進攻黃橋,意圖一口吃掉陳粟部隊。粟裕安排陶勇率第三縱隊2000餘人堅守黃橋,葉飛率第一縱隊、王必成率第二縱隊秘密集結於黃橋西北,待機出擊。
敵軍在猛烈炮火下向黃橋發動集團衝鋒,危急時刻,陶勇自己光著膀子上陣,帶著部隊衝上去與敵人肉搏。王必成率隊向南迂迴穿插,葉飛以3000人對3000人的同等兵力,果斷分割敵八十九軍一部。進攻黃橋的敵軍被擊潰後,粟裕又命令善於穿插迂迴的王必成擔負追擊任務,王必成率第二縱隊逢水過水,見橋奪橋,邊打邊追,使黃橋決戰畫上了勝利的休止符。
此戰,新四軍以劣勢兵力殲敵1.1萬人,敵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獨六旅旅長翁達斃命。黃橋決戰是“葉王陶”聯手作戰的第一仗,也是成名戰。從此,“葉王陶”名聲大震。
皖南事變後,新四軍在1941年2月開始重建,粟裕所部被改編為新四軍第一師,葉飛、王必成、陶勇分別擔任第一師第1旅、第2旅、第3旅旅長。
他們跟隨粟裕轉戰四方,從蘇中到蘇南,特別是1943年3月發起的車橋戰役,殲滅日軍800餘人,俘虜日軍48人,創下抗戰史上一戰俘虜日軍最多的戰役,令驍勇善戰的陶勇大呼打得過癮。
1944年9月,毛主席從戰略反攻的高度,命令新四軍派主力部隊向長江以南進軍,開啟因皖南事變後一度日漸式微的江南抗日局面。這個任務落在了粟裕的第一師肩上。1944年12月,粟裕帶著王必成、陶勇共7000餘人率先渡江南下,建立蘇浙軍區,在日、偽、頑的合擊下接連發動兩次天目山戰役,站穩了腳跟。
1945年4月,葉飛率部南下,“葉王陶”再次聚首。5月,“葉王陶”率部出擊,在第三次天目山戰役中殲敵6800餘人,繳獲槍支上千,給正在召開的黨的七大獻上一份賀禮。
抗戰勝利後,山東八路軍主力去往東北,中央命令新四軍主力北上山東接防,已經接替粟裕擔任新四軍第一師師長的葉飛,接到命令調往山東。新四軍蘇浙軍區第一縱隊司令員王必成,也被要求迅速趕往山東。
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緊急致電中央,要求粟裕留下華中,統一指揮未去山東的其餘華中新四軍部隊。粟裕認為,經過多年發展,“葉王陶”已經形成了各有特點、相互協作的整體,並且在全國各大軍區中率先實現了大兵團作戰的轉變。粟裕向中央建議,“儘可能不過分破壞編制”,以保持部隊的戰鬥力。
中央接到電報後,認為粟裕的意見很有道理,便做出裁決,“各師建制應儘可能不分割,……王必成留華中野戰軍”。
這樣一來,除了葉飛去往山東外,王必成、陶勇都隨粟裕留在了華中。粟裕將華中新四軍各部隊進行了重組,組成華中野戰軍,共成立四個縱隊,王必成任第六縱隊司令員、陶勇任第八縱隊司令員。
1947年1月,粟裕的華中野戰軍與陳毅的山東野戰軍合併,新組建華東野戰軍,葉飛任第一縱隊司令員、陶勇任第四縱隊司令員、王必成任第六縱隊司令員。這樣,“葉王陶”在分別一年多時間後又一次聚首。
葉飛、王必成、陶勇三位驍將合在一起,是陳粟大軍麾下的三隻鐵拳,為華野立下了赫赫戰功。葉飛的一縱、王必成的六縱、陶勇的四縱,都是華野響噹噹的主力部隊,共同參加了萊蕪、孟良崮、沙土集、豫東、淮海、渡江等重要戰役,並且都打得很好。
“葉王陶”的名氣,就連毛主席都約定俗成的將其視為一體,在1948年初與粟裕談及華野渡江南下,“執行寬大機動作戰任務”時,多次提及“葉王陶”及三個縱隊。
1948年5月,朱德到華野總部指導工作時,接見了“葉王陶”。總司令親切地說:“你們在蘇北、山東打得很好,真可謂名滿天下!”
解放戰爭後期和新中國成立初期,葉飛擔任第三野戰軍第十兵團司令員,王必成、陶勇分別升任第七兵團、第九兵團副司令員。抗美援朝時,王必成、陶勇先後代理過第九兵團司令員。
三人當中,葉飛資歷最老,更是閩東紅軍的代表人物,他也是三人中最早被提拔為新四軍師級幹部、解放軍兵團司令的。每當三支部隊聯合行動時,也總是臨時授予葉飛統一指揮。關鍵時刻,粟裕也總是對葉飛委以重任。
1955年授銜,葉飛被授予上將,王必成、陶勇被授予中將。
三位司令性格迥然不同,葉飛儒雅,陶勇豪爽,王必成內向。
長期在新四軍、華東野戰軍工作,後任第三野戰軍參謀長的張震回憶說:
當時我的印象,陶勇同志是外向型的,談吐自如,非常豪放;而必成同志是內向型的,沉默寡言,勤于思考。大家到一起時,他總是把說話的機會讓給別人,自己在一邊認真傾聽,有時也笑眯眯的,插上幾句笑語,但必成同志打起仗來就“判若兩人”。他指揮堅定,作戰頑強,他所領導的部隊,南征北戰,戰功卓著。
“葉王陶”的盛名與傳奇,以及他們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的巨大貢獻,除了他們自身的軍政素質較高以外,很大一點還得賴於粟裕的出色指揮,如果他們不是共同在粟裕帳下效力,“葉王陶”也可能就無法成為黃金組合了,真是應了那句老話“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