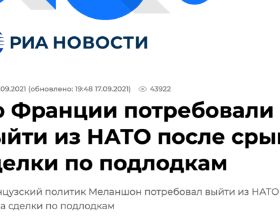公元前549年,一個名叫居魯士(Cyrus)的波斯人發動叛亂,併成功佔領了米底王國的首都埃克巴坦那。這一事件通常被看作波斯人建立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開端。(該王朝的名稱根據居魯士的祖先阿契美尼斯命名。阿契美尼斯在波斯語中被稱為哈卡梅尼什。)在此之前,波斯人受米底王朝統治,而從公元前549年開始,情況徹底翻轉。居魯士大帝統治伊始,其施政與米底人截然不同,他更加強調米底人和波斯人之間的共同合作。(在統治之初,米底人可能佔據絕大多數,居魯士本人則擁有波斯和米底雙重血統。)除了米底人和波斯人,與早期埃蘭帝國有關的一些人,以官僚和書記員的身份在阿契美尼德王朝一直髮揮著重要作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很多朝廷記錄就是用埃蘭文字書寫而成的。

在隨後的幾個世紀中,特別是在色諾芬(Xenophon)的《居魯士的教育》一書中,居魯士被塑造成一個智慧、公正的國王形象。色諾芬的著作雖然有許多虛構成分,但卻真實地揭示了居魯士備受世人尊崇的事實(儘管希臘人一直習慣性鄙視波斯人)。猶太人對居魯士可謂心懷感激,感激他在佔領巴比倫後將猶太人釋放,並同意他們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聖殿。居魯士的這一舉措在偉大的“居魯士圓柱”被發現後也得到印證。居魯士圓柱刻制於公元前539年居魯士佔領巴比倫(巴比倫人在當年奮起反抗米底統治者)後,並於19世紀在巴比倫的廢墟中重見天日,現存於大英博物館。與亞述人、埃及人和其他帝國的建立者常常在銘文中記錄囚犯、來襲的敵人和毀壞城市等以紀念勝利不同,居魯士圓柱上刻載了居魯士的仁慈、大度和寬容,以及對巴比倫人的主神馬爾杜克(Marduk)的推崇:
當我以朋友身份進入巴比倫時,並以喜樂為準,在這天堂建立起政府時,偉大的神馬爾杜克正在勸導寬宏大量的巴比倫人民去愛戴我,而我每天都不遺餘力地崇敬他。我的大批軍隊在巴比倫境內行進,所到之處一片安寧祥和。我不允許任何人威脅蘇美爾和阿卡德。我致力於捍衛巴比倫以及其他聖城的和平安寧。
居魯士允許他的屬民,不僅僅是巴比倫人和猶太人,去信奉各自的神明。在他統治時期和之後的一段時間裡,各屬國人民仍可以按照自己的習慣和法律進行自治,且管理者大多由本國產生。雖然並不是每一個居魯士的後世君主都嚴格遵照他的模式進行統治,但總體來說,波斯人的統治明顯帶有鬆散和權力下放的特徵。值得注意的是,居魯士本人和他的繼承者們無意將他們信仰的馬茲達教強加給他人,但卻將該教強調的道德品質和真理、正直、正義等融入全新、堅定且寬容的施政模式中。這些品質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後期的君主大流士一世時期的銘文中,比如貝希斯敦銘文和波斯波利斯聖殿(始建於大約公元前515年)的銘文中也有所體現。最近的學術研究對於大流士一世自稱的正直與誠實提出了質疑,但是他所宣傳的內容確實在不斷強化“良政”的品質,雖然他本人的一些做法還未達到相關標準。波斯人不僅要把阿契美尼德王朝建成一個“刀劍的王朝”,更想把它塑造成一個“思想的王朝”。
在居魯士統治末期,他的帝國已經成為當時有史以來最大的帝國,面積涵蓋了從愛琴海到印度河流域的廣袤地帶。他的兒子岡比西斯二世繼續擴張,並征服了埃及。大流士一世也沒有停止擴張步伐,不僅征服了色雷斯和馬其頓,還挑起了波斯人和希臘人之間一系列的戰爭。這些舉動深深影響了後世歐洲人對於波斯的看法,乃至對於整個東方的態度。希臘人(特別是雅典人)更傾向於將波斯人的形象描繪成頹廢墮落、專橫殘暴的人,這種廣泛傳播的論調從沒有得到完全的印證,甚至從來沒有被印證過,然而希臘人對於自身兇殘的一面以及其他方面的過失卻視而不見。正如世人所看到的那樣,《聖經》中有關阿契美尼德人的記載對於以上觀念起到了更正的作用。
希臘人對於阿契美尼德人的偏見也提醒著人們,世人(包括當代伊朗人)對於阿契美尼德歷史的認知,無論是來自希臘古典文獻還是19世紀轉錄的古代銘文,基本來自西方的記載和學術研究,而不是伊朗的歷史傳承。使用“Persia”(波斯)一詞也反映了這一點。由於阿契美尼德人來自“波斯省”,所以希臘人稱呼他們及其帝國的子民為“波斯人”。在此先例(以及其他慣例)的影響下,羅馬人也稱來自這一區域的人為波斯人。此後,歐洲人由於大量學習希臘和羅馬的經典文獻,直到19世紀仍一直稱這些人為波斯人(歐洲人也同時吸收了希臘人和羅馬人對於波斯人的各種偏見)。但是,在這漫長的歲月中,伊朗人一直稱他們的國家為“伊朗”。最終在1935年,巴列維王朝的締造者禮薩沙·巴列維(Reza Shah Pahlavi)正式要求各國駐伊朗使館在正式的官方交往中稱呼他的國家為“伊朗”(此舉部分源自民族主義情結,同時也是為了將他本人締造的巴列維王朝和被他推翻的愷加王朝加以區別,以確立自己的統治)。自此以後,“伊朗”一詞成為大眾普遍使用的名稱。今日伊朗人仍然稱他們的母語為法爾西語,即波斯語,因為在伊斯蘭教進入伊朗之前,(古波斯)法爾斯省的方言就已經在文化上佔據了主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