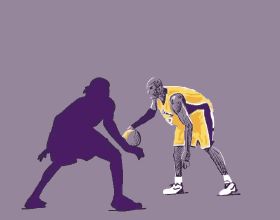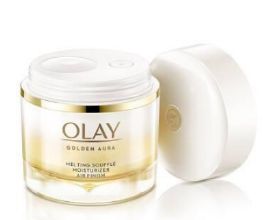1981年7月20日,在世界上頗有影響的美國大報《紐約時報》,於首頁登載了這樣一則社會新聞:一個被保釋出獄的囚犯,名叫傑克·亨利·阿波特,於7月18日清晨5時左右在紐約東城下區一家小餐館就餐時,因小事與侍者起爭端,一怒之下,拔刀將侍者刺死。阿波特隨後逃之夭夭,目前警方正在追捕中。
這個阿波特算何許人物?值得《紐約時報》在首頁的“黃金版面”予以報道?
當今西方社會,犯罪率高,殺人案多如牛毛。特別是像紐約這樣的大城市裡,兩人因吵架而殺人的事,算不上什麼“新聞”,連區區小報都不屑一顧,何況乎世界性大報《紐約時報》呢?想來,這個阿波特的確有一番來歷。
沒幾天,很有影響的《時代》雜誌與《新聞週報》等,也爭相報道了阿波特持刀殺人而逃亡的訊息。
事有湊巧,美國權威書評雜誌《紐約時報書評》週刊,也恰恰在這個週末以巨大篇幅發表長篇書評,推薦這個傑克·阿波特的作品《在野獸的腹腔中》。這篇書評稱這個正被警察追捕的殺人犯阿波特是“一個憑空而來的擁有特殊文學天才的特殊人物”,而把他的《在野獸的腹腔中》被稱為“美國監獄文學中一部最熱切認真的作品”。原來,阿波特早就是一個“新聞人物”了。
這個阿波特儘管被人保釋出獄才個把月,已經是美國文藝界和新聞界受人矚目的“紅人”。
他既是《紐約書評》的特約撰稿人,又是蘭登書屋的作家。尤為重要的是,他是美國作家協會當時的主席諾曼·梅勒一手提拔的“得意門生”。正是諾曼·梅勒的關係,阿波特才從服重刑的囚犯,搖身一變成了“文壇寵兒”。
超級囚犯
審視阿波特一生的經歷,人們不難得出結論:此人算得上一個地地道道的“超級囚犯”。
阿波特那年37歲,自12歲進入少年犯罪教養院開始,他一生真正自由的辰光只有九個半月,其中還包括六個星期的越獄在逃時間。美國各地聯邦監獄的鐵窗風味,他全都領受過。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我在獄中關了這麼久,自由對我來說,好像是一個常人幻夢中的天堂。”
阿波特是個混血兒。他出生不久,就被父母遺棄,一直由陌生人收養,得不到家庭溫暖和教育。在美國,這類離開親生父母的兒童,常常是未成年便沾上惡習,走上犯罪道路。阿波特就是因這種原因,小小年紀便被關進了少年犯罪教養院。
他17歲時,離開教養院不到半年,就因開空頭支票被判刑5年。在獄中服刑時,與其他囚犯爭吵而動手殺人,又被加刑19年。
從小失去母愛,以及多年艱苦磨難、與世隔絕的囚犯生活,養成了阿波特的倔強性格。即便是在監獄裡,他也從不肯向人低頭,常為此遭到懲罰,被關進單身囚室。
這類單身囚室,即便是在重罪監獄裡,也是一個令人恐怖的地方,囚犯們聞之喪膽。而阿波特卻先後在單身囚室裡囚禁了整整14年。
囚犯們把單身囚室稱呼為“洞”,裡面終年漆黑,室中一無所有,只在水泥地中間開了一個排水洞,犯人屎尿就在洞裡排洩。由於不通風,室內其臭無比。單身囚室供應的食物也比普通囚犯少,囚犯長期處於飢餓狀態。據阿波特自己說,他有時在囚室中捉到了蟑螂,就裹進麵包一起吞下肚子充飢。
美國一些聯邦監獄內幕極其黑暗,看守們對待囚犯兇狠殘忍。而囚犯為了自衛,常常互相鬥殺。這類獄中殺人案難得受到監獄當局調查處理,實質上是獄方慫恿囚犯互相殘殺。所以,被關進重罪監獄,就等於被判了死刑。囚犯們需處處提防,睡覺時也得小心翼翼,以防被人暗算。阿波特曾多次看見過獄中殘忍的兇殺。他出獄後曾對人說起過,在某個聯邦監獄囚禁期間,看到三四十個被刀捅死的屍體。
阿波特因其倔強的性格,加之又是個混血兒,更引起監獄看守們的偏見和憎恨。有次,故意將他與獄中最兇暴的黑人囚犯關在一起,其目的是促使他與黑人囚犯爭端打架,最後被殺死。可是,阿波特有強烈的生存願望與毅力,就連最兇暴的囚犯也要讓他三分。
然而,就是阿波特這名“超級囚犯”,卻因偶然機會和著名作家諾曼·梅勒相識後,以其獨特的感受和“罕有的寫作才能”受到梅勒的賞識,從地獄升到天堂,開始了一次頗不尋常的人生經歷。
對囚犯感興趣的文豪
阿波特能夠時來運轉,從一個重罪囚犯搖身一變成美國文壇的“作家”,全靠當代文豪諾曼·梅勒一手提拔。
諾曼·梅勒畢業於哈佛大學,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參軍在太平洋戰區與日軍作戰。後來他把戰爭中的經歷寫成第一部長篇小說《裸者與死者》。這部書被認為是“美國反映二次大戰的小說中最好的一本”,梅勒也因此一舉成名。以後,梅勒又陸續出版了《一場美國夢》、《我們為什麼賴在越南》等長篇小說,梅勒還善於抓住美國社會生活中的重大事件,運用小說加以表現。如寫1967年美國人民向五角大樓遊行示威的《夜間大軍》,寫美國宇航員首次登上月球的《月亮上的火焰》等小說,都以它們的敏感性和生動性吸引了廣大讀者。梅勒的小說具有獨闢蹊徑,技巧精湛的特點,使他一直雄踞美國文壇,享有國際聲譽。
1977年,美國曾經發生過一件引起全社會震動的事:在猶他州,一個叫加里·吉爾摩的殺人兇手,竟拒絕上訴,主動要求處決,堅決不要最高法院赦免。
在美國已多年未處決過犯人,特別是猶他州,自1963年以來14年間從未執行過死刑。加里如果上訴本來可以不死,但他卻主動求死。於是,加里·吉爾摩頓時成為“新聞人物”。
加里本是個無惡不作、長期坐牢的囚犯,他一生的35年中有18年在監牢裡度過。1976年4月,他假釋出獄,來到猶他州的普羅沃市找了個職業謀生。起初他工作還算努力,但終因劣根難改,又重新犯罪,從偷啤酒發展到偷槍支。後來,他的情人妮科爾同他爭吵離去,加之他沒錢買一輛卡車,一氣之下,竟槍殺了與他素不相識的一個加油站工人和一個汽車旅館經理。被捕後,加里對罪行供認不諱,只求一死。
加里主動求死這一訊息在社會上引起震動。在西方,凡是這類聳人聽聞的社會新聞總是和金錢聯絡在一起的。許多嗅覺靈敏的人,從這個案子裡嗅到了金錢的氣息。於是,大批記者、作家、攝影師、電影製片商,一下子湧到關押加里的猶他州鹽湖城監獄,採訪“內幕新聞”。這些人明爭暗鬥,為爭獲第一手材料不擇手段,到最後竟然把這樁兇殺案變成赤裸裸的現金交易。
加里行刑前夕的1977年1月中旬,這股宣傳熱浪達到高潮,各地湧來的記者擠滿了鹽湖城的大小旅館。有人甚至願意以12萬5千美元的高價,購買一篇關於加里伏法的第一手專題報道。隨著行刑時刻的臨近,記者們的神經緊張達到瘋狂的程度。ABC電視臺的記者對著話筒大喊:“快讓我廣播!我保證你們一定能聽到槍聲。你們一定能聽到槍聲!”直到11月17日處決加里的愴聲響過以後,新聞工具掀起的那股熱浪還未平息。
加里·吉爾摩主動求死,以及他伏法前後的曲折經歷和社會反響,對梅勒觸動極大。本來,梅勒正在創作她的第21部作品,這是一部宏篇鉅著式的長篇小說。他突然終止了創作計劃,四處採訪,蒐集有關加里案件的各種資料,並根據大量的採訪錄音帶,整理出1萬5千頁的創作素材。梅勒準備在此基礎上,創作一部題為《劊子手之歌》的“非虛構小說”。用他獨具匠心的藝術手法,以加里的經歷,寫“一部真實生活的小說”,以震動文壇。
正是在創作《劊子手之歌》的過程中,梅勒發現了阿波特。
偶然機遇
阿波特在獄中服刑,能與梅勒這樣的大作家結識,機遇極為偶然。
原來,阿波特雖說沒受過小學以上的正式教育,但他和其他囚犯不同,喜愛閱讀。阿波特靠他的姐姐和一家書店幫助,在獄中讀了許多文學與哲學書籍,其中包括柏拉圖、莎士比亞、黑格爾、康德、陀思妥也夫斯基和薩特、卡繆等名家的作品。
有一天,阿波特在獄中翻閱一本雜誌,讀到名作家梅勒準備寫《劊子手之歌》的訊息。他一時心血來潮,給梅勒寫去一封信,毛遂自薦,表示願意給梅勒提供“監獄內幕”。
像梅勒這樣的名作家,每年都要收到幾百上千封陌生人的信。他是個大忙人,常常顧不上覆信。但阿波特這次卻交了好運。第一,他正關押在亞特蘭大聯邦監獄,恰好是加里被關押過的一所監獄;第二,阿波特在信中說,很少人知道監獄內部的暴行,如果梅勒有意的話,他“可以幫助闡明吉爾摩囚犯生活的內情”。
梅勒讀了這封信後,作家的好奇心被觸動了,破例寫信給阿波特。梅勒的信使阿波特大受鼓舞,此後,他就頻繁地給梅勒寫信,詳細介紹監獄內幕及自己對監獄生活的獨特感受。而梅勒從阿波特來信中,驚奇地發現,阿波特和已處決的加里之間,兩個囚犯的人生經歷極為相似:都是自幼失家而犯罪,都是在監獄中度過了人生的絕大部分時光。但梅勒對加里的瞭解是間接的,而對阿波特的接觸卻是直接的。一句話,阿波特是個活著的“加里·吉爾摩”,梅勒對他的興趣日漸濃烈,兩人通訊頻繁。
兩年後,阿波特寫給梅勒的信竟達一千多頁。阿波特雖說沒受過正規教育,但他勤於自修,大量閱讀,文學修養不斷提高。加之,他那種獨特的人生體驗,使筆下的監獄生活和囚犯心理寫得頗為生動,梅勒讀後讚歎不已。
梅勒談到阿波特的那些信時,頗有感觸地說:“我發現信的內容非凡異常,大大地幫助了我對吉爾摩的瞭解。此外,他的寫作才能也給我以深刻印象。”又說: “阿波特自有他的語言。我從未聽到過這類語言。”表現出列阿波特的常識。
囚犯成作家
梅勒被文學界視為激進作家。他對美國現實的政治、經濟、司法等制度一直深為不滿。在同阿波特的深入接觸和了解中,無形中產生了對這個罪犯的同情心。而阿波特那些信,又給他寫作《劊子手之歌》提供了創作靈感和材料,以至他想幫助阿波特擺脫厄運。
而此時,梅勒那部長達一千多頁的“非虛構小說”《劊子手之歌》已經出版。這部長篇以它轟動一時的題材,新穎別緻的手法,吸引了廣大讀者,立刻成為暢銷書,文學界也是一片讚揚聲。在各方一致好評下,《劊子手之歌》理所當然獲得了1980年“普利策”獎。
《劊子手之歌》一書的成功,使梅勒對阿波特的處境更表同情和關切。
在一次文學沙龍的聚會上,梅勒向文學同行們講起他對阿波特的印象。《紐約書評》雜誌的高階編輯西爾伐斯當即表示,可以將阿波特寫給梅勒的信挑幾封出來,在他的雜誌上發表,並由梅勒寫篇短文予以評論。
梅勒回來後,從阿波特的來信中挑出幾封,寄給了西爾伐斯。西爾伐斯看過後,也對沒受過正規教育的阿波特的寫作才能表示驚服,立即決定全文刊登。於是,1980年6月的《紐約書評》雜誌上,發表了阿波特的幾封信。
這幾封信在《紐約書評》上發表後,立即受到蘭登書屋編輯麥克唐諾的注意,覺得阿波特的這些信中,有一種非同尋常的東西。他同梅勒聯絡,表示可以將阿波特的信件選編出版。
梅勒大喜,立即委託自己的文學代理人梅雷狄斯兼做阿波特的文學代理人,負責聯絡交涉出書的具體事宜。梅雷狄斯代表阿波特與蘭登書屋簽訂了出版合同,獲得了初版預付版稅12500美元。
梅勒把阿波特這部書信選集取名為《在野獸的腹腔中》,並親自作序。
從囚犯搖身一變為受人崇敬的作家,這是長期坐牢的阿波特做夢也不曾想到過的事。
假釋出獄登上文壇
阿波特書信選集出版後,梅勒及其朋友們一心要把阿波特這個“寫作天才”從長期監禁中拯救出來,過上自由自在的作家生活。
《紐約書評》的西爾伐斯就對人說過:“以他(阿波特)的智力與才能,他應有一個重返社會的機會。”而梅勒則進一步對人宣揚說,阿波特不但有寫作才能,他對物理學也很有興趣,以他高度的智力,這個人將來一定會在社會上有所成就。一些文壇人士也對阿波特寄予某種期望,認為他可以和世界文壇上兩位法國囚犯作家弗朗索瓦・維朗與讓・靜乃相媲美。於是,以梅勒為首,包括西爾伐斯、麥克唐諾在內,紛紛出面向司法當局申訴,要求將阿波特假釋出獄。他們說,阿波特不但已經改邪歸正,而且能靠寫作賣文謀生。
經過梅勒這樣的文壇鉅子出面作保,美國司法當局同意讓阿波特假釋出獄,恢復自由。對此,連阿波特本人也頗覺意外。他對重新獲得自由一事,原來根本沒存過奢望。經過長期的囚禁生活,已經把自由視之為“褪了色的夢”,認為自己此生是再難獲得了。他曾經說過:“我想,我要出獄的慾望等於常人希望成為百萬富翁。”沒想到,這個“褪了色的夢”又重新變得五光十色,終於實現了。
1981年6月5日,阿波特從聯邦監獄獲釋後,立即乘飛機飛往紐約。梅勒等紐約文化界人士到機場迎接。梅勒還在紐約東城下區,幫阿波特找到一個住所,讓他定居下來。
獲釋之初,阿波特尚無職業,梅勒當時正在寫作一本有關象形文字的書,便讓阿波特充當助手,做些研究工作。
阿波特定居紐約以後,不但有機會逛博物館,進圖書館、劇院,以擴大眼界,吸收新知識;而且在梅勒幫助下,他成了紐約文藝界沙龍的座上客,得以和美國文藝界人士交往。
令人深思的結局
不久,阿波特的《在野獸的腹腔中》一書由蘭登書屋出版。
由於梅勒的推薦,《在野獸的腹腔中》一書立即引起出版界和讀書界的注意。不少期刊紛紛撰文予以好評,稱讚《在野獸的腹腔中》是一本“很有力的著作”。
的確,阿波特在描寫獄中恐怖生活和看守們的惡毒手段時,其感情之強烈,語言之個性化,使人印象奇特。有人認為,讀後會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而阿波特承認他寫作受了司湯達《紅與黑》的影響。
不過,預定於7月19日出版的《紐約時報書評》週刊,卻把阿波特捧為“擁有特殊文學天才的特殊人物”,予以大吹特吹。這位評論家在文章中,還特別感謝梅勒發現了阿波特這個“文學天才",並幫助他獲釋。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篇有份量的吹捧文章原定於7月19日這個週末發表,但阿波特這位“文學天才”卻本性難移,惡習不改,在7月18日清晨僅因小事,便拔刀將餐館侍者殘殺後逃匿。
此案一出,輿論大譁。特別是死者也是一位很有前途的演員和劇作家,因失業才來小餐館當侍者的,這就更令文藝界惋惜。梅勒和西爾伐斯被這一突發事件弄得目瞪口呆,以至記者上門採訪時,梅勒僅說事件太具“悲劇性”了。
阿波特殺人後,即逃離紐約。在警察追捕下,他潛往美國南部,曾在路易斯安那州各地流浪,以替人做短工為生。有意思的是,阿波特在逃期間,仍秘密與其文學代理人梅雷狄斯保持聯絡。頭腦精明的阿波特,即便是在逃亡中,仍關也著自己的經濟利益。他通知梅雷狄斯說: “出於近來形勢的變化”,請他將《在野獸的腹腔中》一書的平裝本稿費和電影製片收入等,轉寄給他的姐姐。據估計,阿波特單是這兩筆收入即達25萬美元。
1981年9月,阿波特逃往路易斯安那州的摩根城。他隱姓埋名,偽造身份,想在摩根城的油田長期躲藏下來。阿波特混在來自外地的工人中,在油田找了一個工作。每小時工資僅4美元,食宿免費。阿波特不在乎錢少,只想在這個不惹人注目的小城躲藏下來。
可惜好景不長,僅過了9天,即9月23日下午,阿波特即被追蹤而來的警察捕獲,迅即押解紐約受審。
結語
阿波特這個“囚犯作家”,曾經因為梅勒的關係,在美國文壇紅極一時。自從重新落入法網後,他只能在美國聯邦監獄的鐵窗中度過餘生了。不過,他靠那部《在野獸的腹腔中》,賺下幾十萬美元的銀行存款。難怪有人感嘆說,這種奇怪的現象,只有在美國這樣的社會才會出現。而那個作了他刀下之鬼的年輕演員兼劇作家,卻實在死得太冤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