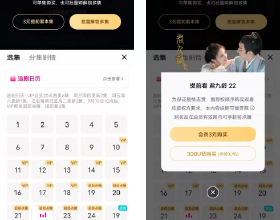邁克·弗雷澤把潛水面具拉下來蓋住了臉,讓南極洲冰冷的海水淹沒了他的緊身潛水衣。潛水是他工作之餘最喜歡的休閒方式。他是坎培貝爾島氣象站的頭頭。這個島是地球上最偏僻的地方之一,它是位於紐西蘭和南極洲之間的一座小島,終日被西風吹打的海水衝擊著。
但在1997年4月24日這天,大海閃藍,海風輕吹。
當四個隊友在淺灘潛泳時,弗雷澤在水下劃到了離岸40碼的地方,他喜歡獨自一人和自然相處的感覺。這裡有黃眼睛的珍稀企鵝搖來晃去,海獅們也毫不畏懼地和他一起游泳。
弗雷澤掃描了一下海床,為的是熟悉海灣的深度,這樣當南方的露脊鯨在冬季過來繁殖時,他就可以和它們一起游泳了。他放鬆了下來,這裡沒聽說有大鯊魚出沒。儘管水溫低至華氏43度,但他的潛水衣厚得足以禦寒。
半小時之後,弗雷澤已經看夠了海床。現在大約是下午3點39分,該潛下去了。他停止划動,讓自己漂流。呯!他的右肩被重物猛擊了一下。弗雷澤被一股猛力拋向前面,氣喘吁吁,一定是一隻巨大的雄海獅,他想。片刻後,他感覺自己被向上猛推,停在了水面上齊腰高的地方。隨後,弗雷澤朝下看去,只見咬住他右臂的是一頭巨鯊的2.5英尺寬的嘴。
弗雷澤本能地揮動著左臂,用拳頭猛擊巨鯊突出的大鼻子。他想,我必須警告其他人。“鯊魚!”他尖聲叫道。但由於巨鯊把他拖下了水,因此他的喊叫聲只變成了一連串無聲的氣泡。
弗雷澤的副手琳達·戴恩氣象員正在離岸15碼的地方潛泳,他和自然環保官員傑森達·艾米、電子技師羅賓·漢弗萊和技工加斯·麥克阿利斯特在一起。她正注視著罕見的太陽在沙底的倒影。他們在海底能聽到的只是他們自己呼吸引起的穩定的水流聲。接著,海面傳來了一聲微弱而壓抑的喊叫。潛水的人馬上浮上水面,掃描著地平線,可什麼也沒有。
突然,遠處浪花翻騰。弗雷澤躍出海面,一邊尖聲叫喊,一邊猛烈搏鬥。四個人看到咬住他的動物都驚呆了。大白鯊停頓了片刻,頭露出水面,隨後令人心驚地張開嘴把弗雷澤咬在嘴裡,好像是在試他肉的硬度。
快想辦法,戴恩催促著自己,肯定有你能做到的事兒。她朝其他人尖聲喊道:“有沒有人帶著潛水刀?”但她知道他們根本無能為力,幫不上忙。
大白鯊是海洋裡最可怕的食肉動物,對它1300磅的肌肉和軟骨來說,潛水刀就像牙籤一樣無用。從巨鯊的頭來判斷,它至少有13英尺長。戴恩無助地望著鯊魚把弗雷澤拖到了波浪下面。
到了水下,弗雷澤感到死亡近在咫尺。如果現在不自救,你就完了,他想。他抬起膝蓋,用力朝鯊魚嘴淡白色的下部踢了一腳。他踢了一次又一次,絕望地拽著被咬住的胳膊。鯊魚搖晃著他,牙齒深深地嵌入他的肉裡,他就像被剪刀鉗住一樣。弗雷澤又踢了起來。突然,他感到猛地一扭,人整個轉了一圈。
霎時,弗雷澤迅速上升。當他的頭衝出水面時,他吸了口氣,拼命踢蹬著腿向岸邊游去。但當他在水裡划行時,身體的動作很奇怪。他低頭看了看右臂,發現它已經沒了!從肘部往下什麼都沒了,只有殘碎的部分,向海中泉湧般噴射著鮮紅的血液。
弗雷澤知道,惟一的希望就是在他失血過多死亡之前找到隊友。他以前曾告訴過他們:“來到了這裡,我們必須相互關照,這裡沒有其他人。現在,該到考驗的時候了。
本能驅使著弗雷澤儘快朝岸邊游去。但長年生活在偏遠地區的經驗教會了他不能驚慌失措。他知道此時此刻每一次心跳都會把更多的血液擠壓到海水裡。因此,為了避免驚慌,他強迫自己有節奏地划動。突然,弗雷澤感到自己的脖子被拉了一下。
他轉過頭,從潛水面具看過去,是傑森達!為什麼她沒有游到岸上?他正想著的當兒,傑森達滑到了他身體的下面,開始拖著他朝岸邊遊。其他隊友等在那裡,把受傷的弗雷澤抬出水面。
戴恩立刻看到了弗雷澤的斷肢,撕爛的肌肉和面板從血肉模糊的殘餘部分突了出來。來坎培貝爾之前,她曾受過給斷肢上夾板、肌肉注射和縫合傷口的訓練,現在都派上用場了。但我對這件事沒有準備,她害怕地想。最近的醫院離這裡有400多英里,島上也沒有簡易機場,坐船要三天才能到達那裡。上帝幫幫我們吧,她禱告道,我們是他擁有的一切呀。
此時,休克已經臨近,弗雷澤開始呼吸困難。我可能要死了,他一邊想一邊喘著氣。
戴恩迅速拉開弗雷澤的潛水衣,取下他的面罩。漸漸地,弗雷澤的呼吸順暢了。接著,漢弗萊給殘臂施加壓力,麥克阿利斯特從弗雷澤的面具上撕下橡皮帶,纏住他的上臂並拉緊。血止住了。
雖然團隊基地放有大功率的無線電發射機和醫藥用品,但到那裡要艱難地步行4英里。
“我去,”麥克阿利斯特說著,就跑進了灌木叢。艾米知道,如果弗雷澤昏迷,他的處境就會更糟。“我們要讓他一直說話。”她對漢弗萊說。這時,戴恩跑上300碼高的山丘小屋,屋裡放著一隻急救包、一頂帳篷和一個超高頻無線電。也許正好有船和飛機在附近。
“請求援助!請求援助!”她喊道,“我們在坎培貝爾島,有人受了重傷。”但她的呼叫帶來的只是靜電的嘶嘶聲。戴恩帶著無線電和急救包,磕磕絆絆地下了山。她小心翼翼地用壓力繃帶換下止血帶。然後又轉向他的左臂,左臂上的傷口也很深,看起來像是骨折了。她把弗雷澤的黃色塑膠潛水管固定在他的前臂當夾板。
“我們一定不要讓他凍著。”戴恩告訴其他人。漢弗萊用從小屋裡拿來的一個睡袋、一隻舊船槳和一塊浮木,做了一副簡易擔架。
幾個人就把弗雷澤抬到平地並給他搭了一個急救帳篷。弗雷澤身上表現出了嚴重的休克症狀:慘白的面孔,發青的嘴唇,面板溼冷。
治療的方法就是先保暖,抬高雙腿使血液接近重要器官,並用鹽水滴來提高血液量,用共鳴器來提高血壓。戴恩和其他人割開他的潛水衣,把他拖進睡袋,在上面又加了兩個包。升高和取暖是我們能給你的一切,戴恩想。
5點剛過,無線電就尖利而急促地響了起來。麥克阿利斯特已經到達了大本營。“我已經往惠靈頓打了電話,他們將盡其所能幫助我們。邁克怎麼樣?”
“他仍很冷,加斯,”艾米平靜地說,“他非常冷。”
在位於紐西蘭北島塔坡機場的辦公室裡,直升機飛行員約翰·弗奈爾慢慢地把話筒放回到叉簧上,他開始飛快地思考。他6個月前到坎培貝爾執行一次補給任務時見過邁克·弗雷澤。儘管路很遠,他想,但我們必須得試一試。
弗奈爾曾因出色完成艱難的營救而出名,但這是一次真正的挑戰,他的六人座航空松鼠直升機的飛行範圍是354海里。而要到達弗雷澤那裡,機艙需要裝上長距離飛行油箱。首先,弗奈爾必須飛行570英里來到紐西蘭的最南端,然後再在海上飛行370英里。但飛行如此遠的距離,耽誤的時間可能會讓弗雷澤失去生命。
這時,一個大膽的計劃在弗奈爾的腦海中形成了。他需要兩個關鍵人物:一個是帕特·威恩,曾隨他多次完成營救任務的老練的護理員;另一個是格蘭特·貝爾,富有經驗的飛行員和領航員 --他能駕駛飛機飛到浩瀚的南極洲沿海的一塊突出的岩石上,而且是在夜間飛行。弗奈爾給兩個人打去電話說:“我們要救一個遭到鯊魚襲擊的傷員。”
與此同時,一隊飛機工程師在機艙裡飛快地裝上三個噴油桶,並在儀表操縱盤上裝了一個遠端導航系統。
威恩和貝爾到達後,弗奈爾就簡要說了一下他的計劃,貝爾呆在飛行員座艙,威恩坐在客艙裡,艙裡有三桶飛行用油和一臺行動式電泵。他們一邊飛行,電泵一邊將油抽到直升機的油箱裡。這雖是不合常規的策略,但三個人都知道弗雷澤此時性命攸關。
在帳篷裡的陰暗處,弗雷澤感到冷得要命,劇痛一陣陣地衝擊著他。至少我現在還活著,他想,儘管我已經失去了右臂,但我還活著。我的周圍有一個優秀團隊。我能依靠他們。他們不會放棄,我也不會。
當麥克阿利斯特帶著從基地取來的重重一包藥品、繃帶和幾個睡袋返回帳篷時,已經過了下午6點30分。戴恩撿出止痛藥和抗生素,分別抽到兩個注射器裡,注射進弗雷澤的大腿。弗雷澤的呼吸已經非常微弱,幾乎感覺不到。她走過去,用手抱住他的頭,希望她的觸控會給他力量恢復知覺。
凌晨2點,松鼠直升機從塔坡出發飛行五小時後,到達了紐西蘭大陸的最南端,進入了黑暗。三個人都繃著臉,一聲不吭一一前面是370海里的開闊海域。他們能否挽救即將凍死的傷員靠的只能是他們的小型飛機和格蘭特·貝爾作為領航員的技術。
為了在夜間找到小島,貝爾原打算依靠松鼠直升機的全球定位系統,這是使用軌道衛星發出的資訊計算位置、速度、高度和到達目的地的距離的計算機無線電接收器。
但那天夜裡,全球定位系統因為在空間常規復位而從空中中止。由於命運的捉弄,這一程式剛好又與他們的飛行發生了衝突。資訊傳輸要90分鐘後才能恢復,也就是正趕上他們去坎培貝爾的途中。此時,貝爾不得不運用對風的速度和速率的準確估計來領航,如果全球定位系統聯絡不能按時恢復,他們就可能被迫放棄嘗試,返回陸地。
威恩則擠在松鼠直升機客艙中的一個小角落,由於沒有站或坐的空間,他被迫彎著腰站在飛行員身邊。
“準備扔。”當第一個油桶的油快抽乾時,他對弗奈爾說。威恩把油管移到了第二個油桶裡。接著,在弗奈爾減速的同時,威恩開啟門扔掉了油桶。
到現在為止,他們的飛行已經超過了一個半小時。但全球定位系統接收器仍然沒有任何訊號。貝爾利用在他們上面1.4萬英尺高的一架納瓦霍飛機發出的無線電資訊,計算出了一個新的羅盤航向。領航員知道,即便一個微小的變化都會使他們偏航數英里。已經連續飛行了21小時的弗奈爾進入夜間飛行時,調整了一下操縱器。
整個夜晚,戴恩不斷給弗雷澤喝水,以防脫水,但由於身體狀況惡化,無論他喝什麼都會再吐出來,他的身體一直汗津津的。艾米拿掉一個睡袋,戴恩准備註射另一支止痛藥。
凌晨5點過了沒多大一會兒,弗雷澤恍恍惚惚地睡著了。戴恩檢查著他的生命跡象,時不時地推推他,以確定他是否還有知覺。
格蘭特·貝爾瞥了一眼儀表盤,終於看到了在全球定位系統小螢幕上閃現了黑色數字。他的航向幾近完好。“我們偏離航道一英里半。”他說。
但當松鼠直升機接近小島時,一個新的危險出現了:一層濃雲低低地籠罩在海面上空。這時弗奈爾聽說一艘官方漁業調查船唐歌拉號偶然收到了團隊的一條無線電對話,也在趕往坎培貝爾。他轉換到一個船用頻道,用無線電和那船隻聯絡。“我是唐歌拉號,”對方答覆說,“1000英尺高空處覆蓋著雲層,我們將開啟照明燈為你們導航。”
話音剛落。“他們在那裡!”貝爾說。他發現左邊的雲層中有一道微弱的橘色光。
就在剛好1000英尺高空,弗奈爾還在盲目飛行。突然,雲層翻騰著、旋轉著遠去了。他們看到了船上的燈光,就像海上的一串珍珠。弗奈爾以唐歌拉號為指示器,把飛機降到300英尺的空中。
“左轉舵,”船上的無線電操作員說,同時帶領他們繞過了離小島岸邊不遠處的兩處岩石。一分鐘後,飛機上的貝爾看到地面上的一道光亮。“找到他們了!”他說。
時間剛過早上6點--鯊魚襲擊15小時後一威恩爬進了帳篷裡,只見戴恩和艾米跪在弗雷澤身邊,受傷的弗雷澤已經臉色青白、眼睛緊閉。我來得太晚了,威恩想,他把手指壓在弗雷澤脖子的頸動脈上,幾乎察覺不到微弱的脈搏。威恩把血壓計纏在弗雷澤的胳膊上,讀數是高壓70,低壓40--血壓這麼低,他已接近了腎衰竭。
第一件要事就是馬上輸血。但在帳篷裡昏暗的燈光下,根本不可能將針管扎進弗雷澤脆弱的血管。“我們必須用飛機運他回大本營。”他對在場的女人們說。
飛機上,威恩在明亮的燈光下仔細尋找著弗雷澤右踝部的主血管,默默地禱告了一下,將一隻皮下注射針管推進了弗雷澤的面板。感謝上帝!一股發黑的靜脈血流入了注射管裡。
艾米拿著一袋血漿,威恩從針頭上取下針管,插上了滴液管。他在弗雷澤的左踝處重複同樣的步驟,救命的液體終於流進了弗雷澤的身體。
六小時後,弗雷澤被推進了紐西蘭印弗卡吉爾市的南地醫院,儘管醫生們估計他失去了軀體中多達一半的血液,但他還是很快恢復了氣力。在十個半小時的航程中,弗奈爾、貝爾和威恩飛行了將近2000英里,其中大部分航程是在海的上空。
這麼長的航行是直升機完成的,而這架直升機是設計用來作陸上短途運輸的--這是紐西蘭歷史上最英勇無畏的營救行動之一,是令人為之歡呼的一大功績。可帕特·威恩卻不這樣看。他說:“我們只是在做自己分內的工作。”
弗雷澤在面板移植和恢復性的外科手術後,現在為惠靈頓的一家氣象臺工作。透過鍛鍊,他失去兩根肌健的左臂變得越來越強壯。這次磨難使他對人類的勇氣和機智充滿了極大的敬意。他說:“這正好表明,如果我們相互關照,就能成就異乎尋常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