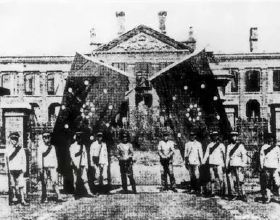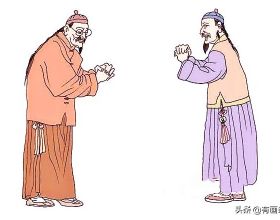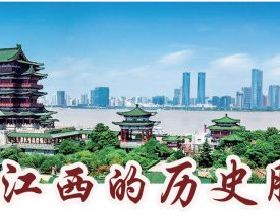縱觀我國曆史,明朝似乎是最喜歡拿“華夷之辨”學說來“說事兒”的中原封建王朝之一。那麼問題來了,在不同的時間節點,明朝人是如何評價元朝的?我查了一些資料,接下來跟大家簡單聊聊。
1)明朝中前期:元朝是“中國正統”王朝
1)朱元璋和朱棣的“元朝觀”
可能與大家想象的有所不同,實際上,明朝的開國君臣們,對於元朝的印象一直都比較不錯。
就拿明太祖朱元璋來說,他不僅宣稱“朕本農家,樂生於有元之世”,還說“(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統中華,生民賴以安靖七十餘年”,給予了忽必烈非常高的評價。
他多次強調,元朝一直都不是自己要推翻的物件,“(元末)盜賊蜂起,群雄角逐,竊據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圖自全….開拓疆域。當是時,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於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在《即位詔》中,他再一次表達了對元朝“正統地位”的認可,“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命真人(元世祖)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
與太祖朱元璋一樣,明成祖朱棣也認為元朝是“中國正統”。
1406年,明朝遣使致書蒙古烏格齊汗(明史料中的“鬼力赤”),“昔者天命宋主天下,歷十餘世,天厭其德,命元世祖皇帝代之,元數世之後,天又厭之,命我太祖皇帝君主天下。此皆天命,豈人力之所能也。”
簡言之,在朱棣看來,無論是“宋元更替”還是“元明更替”,本質上都是“天厭其德”的結果,“王朝更替”是“上天的旨意”。
2)忽必烈入圍“歷代帝王廟”大名單
如果說這些文獻記錄多少有統戰之嫌的話,那麼朱元璋“以元世祖入祀歷代帝王廟”的舉措,深刻印證了明朝對元朝“正統性”的承認態度。
始建於1373年的南京歷代帝王廟,“祭三皇至元世祖凡十六位,皆開基創業、有功德於民之主”。簡言之,在“開國”之初,明朝不僅視元朝為“中國正統”,更將元世祖忽必烈譽為“開基創業、有功德於民”的君主(拓展閱讀:忽必烈的執念:為什麼要一門心思“征服”日本?)。
後因歷代帝王廟失火,明廷於1389年改建新廟於北極閣。新廟建成後,文淵閣大學士宋訥(ne,1311—1390)在為新廟撰的《敕建歷代帝王廟碑》中,對入祀帝王的“入圍”標準,做出了極為詳細的解釋:
“正名定統,肇自三皇,繼以五帝,曰三王、曰兩漢、曰唐、曰宋、曰元,受命代興,或禪或繼,功相比,德相侔….皇帝王之繼作,漢唐宋之迭興,以至於元,皆能混一寰宇,紹正大統,以承天休而為民極,右之序之,不亦宜乎。秦、晉及隋,視其功德,不能無愧,故黜而不與。”

宋訥(1311—1390) ,洪武十五年超遷翰林學士,改文淵閣大學士,再遷國子監祭酒
簡言之,“入圍大名單”的標準是相當“苛刻”的。在新的歷代帝王廟中,從三皇五帝開始算起,一共僅有16人。其中,秦漢以後的帝王,僅有漢高祖劉邦、漢光武帝劉秀、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趙匡胤和元世祖忽必烈五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五位入祀的帝王中,忽必烈是如假包換的“異族(蒙古族)”,而“千古一帝”秦始皇和恢復“中原大一統”的隋文帝楊堅,卻因為“功德”的原因,均被排除出了大名單。
由此可見,明初君臣和當時的主流知識分子們,不僅對元朝的“正統性”不存在異議,對於“異族”皇帝忽必烈也有著非常高的評價。
3)“元承宋統”的官方史觀
在這樣的認知大背景下,由宋濂、王褘為總裁,汪克寬、胡翰等十六人全程參加纂修,最終於1370年定稿的《元史》,不僅將元朝視為“中國正統王朝”,甚至將元朝歷史上溯到了“大蒙古國”時期(《元史》首卷為“太祖(成吉思汗)紀”)。
除了官修史書之外,在明朝前中期的“科普性”歷史讀物中,這樣的認知在同樣有著淋漓盡致的體現。
比如初刻於1432年,屢次增修和重刻的“歷史教科書”《資治通鑑節要續編》中,對於元朝的評價是這樣的:“以宋為統,遼金分書之,元則直續宋統”,“元滅金、夏, 有中國,而猶分注其年,繫於宋統之下者,明天命之未絕也。”“元自世祖至元己卯滅宋方大書,承大統也。”
一言概之,此書不僅嚴格貫徹著“元承宋統”的準則,並明確承認了元朝“中國正統”的地位。有趣的是,這一觀點一度惹得錢穆先生頗為惱火:“所謂民族大義,光復漢唐舊統,誠千載難逢一機會,而明初諸儒似無此想。”
2)“排蒙心理”的發端與蔓延
通常來說,中原王朝每當受困於“外族”威脅或國內民族矛盾異常尖銳時,“華夷之辨”的學說通常會大行其道(拓展閱讀:“華夷之辯”的沉浮:10至13世紀中華世界的分裂與再統一)
1)全民“排蒙”心理的蔓延
學界普遍認為,“華夷之辯”學說在明朝的“死灰復燃”,始於15世紀中葉。至於“罪魁禍首”,無疑是被斥為“北虜”的蒙古勢力。
伴隨著土木之變(1449)和庚戌之變(1550)的先後爆發,不僅讓明蒙關係陷入了冰點,更給了“華夷之辯”學說的“野蠻生長”的,開闢了“極為廣闊的空間”。
拓展閱讀:
- 理性討論:“北狩”的明英宗,有沒有受到蒙古人的“尊崇”?
- 一文概覽:為什麼景泰帝和于謙“不得善終”?
- 一文概述:俺答汗之於蒙古,做出了哪些貢獻?
2)大受追捧的《諭中原檄》
在明朝全民“反蒙”的輿論大環境下,自弘治(1487—1505)時期開始,太祖朱元璋於1367年10月釋出的《諭中原檄》,因其慷慨激昂的陳詞,受到了知識分子階層的強烈推崇。原文如是寫道: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
這篇檄文,最早見於《明太祖實錄》(1418)。值得注意的是,在實錄中,本文不僅沒有作者,也沒有篇名。
直到弘治年間,學者程敏政(1446—1499)在編輯《皇明文衡》時,首次將該文納入其中,並命名為《諭中原檄》,文章作者署名為宋濂,更將文章排在《皇明文衡》一書之首。除《皇明文衡》外,佚名《皇明詔令》、高岱《鴻猷錄》等書,也將《諭中原檄》納入其中。
簡單地說,在這些知識分子看來,《諭中原檄》具有十分強烈的象徵意義,尤其是 “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一句,更是被賦予了鮮明的“排蒙”意味。
3)日益尖銳的“排蒙心理”
到了嘉靖(1522—1566)年間,明朝社會各界“排蒙”和“仇蒙”的情緒,達到了一個新的頂峰。歷史記載,因為不堪俺答汗所擾(拓展閱讀:讀書筆記:為什麼俺答汗要三番五次主動向明朝“納貢”?),嘉靖皇帝“最厭見夷狄字面....世廟晚年,每寫夷狄字必極小,凡詔旨及章疏皆然,蓋欲尊中國卑外夷也”。
與統治階層一樣,知識分子群體的“仇蒙”心理也頗為嚴重。士人李詡在《戒庵老人漫筆》中寫道:“餘家先世分關中,寫吳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字。想國初惡勝國之號而避之,故民間相習如此。史書無所考見,姑記之以詢之熟典故者焉。”
4)忽必烈被“開除”出歷代帝王廟
不過,說到明朝“仇蒙”情緒的終極體現,莫過於官方將元世祖忽必烈“開除出歷代帝王廟大名單”的事件。
1530年,明廷決定在北京(阜城門內保安寺故址)新建歷代帝王廟。次年,翰林修撰姚淶(1488—1538)便以元朝“為中國之大仇恥”為由,上疏“請罷元世祖祀”。不過,新的歷代帝王們建成後(1532),依然維持著”十六位神主”的格局。
不過,這樣和諧的局面並未持續多久。1545年,禮科右給事中陳棐(fei)兩度上疏,極言當黜祀元世祖以正祀典。
“胡元為中國之所當驅,是中國決非胡元之所當居矣;中國非胡元之所當居,是胡元決非中國之所當祀矣。故必除胡君之祀,而後駆胡之功彰。今欲存胡君之祀者,顧不自小聖祖驅胡之功耶….臣固知祀忽必烈於帝王廟者,非皇祖之本心也,是則當黜也。
在他看來,“必除胡君之祀”的舉措,既可以彰顯太祖朱元璋“驅胡攘夷之功”,也具有“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深刻意味。顯而易見,在明蒙關係陷入冰點,舉國“排蒙”的輿論帶動下,這樣的說辭迅速激起大多數人的普遍支援。
不久,入祀歷代帝王廟近二百年的元世祖忽必烈,被“攆出了”歷代帝王廟。與此同時,包括木華黎在內的著名蒙古將領和重臣,均被“驅逐了出去”。
3)“排蒙”背景下的“元朝印象”
1)“華夷之辯”在明朝
在明朝,最早拿“華夷之辯”說事兒的,非江南大儒方孝孺莫屬。他認為,“有天下而不可比於正統者三,篡臣也、賊後也、夷狄也”。不過,他的主張遭到了當時主流知識分子的“訾笑”和“詆詬”。
或許連他自己都沒有料到,他的“正統說”卻在百年之後,成為了支援知識分子們“正統觀”的最強武器。
2)元朝“中國正統”地位的動搖
伴隨著“全民排蒙”心理的蔓延,知識分子們對元朝正統地位的認識與評價,發生了180°的大反轉。
成書於1476年的官修史書《續資治通鑑綱目》,儘管依然沿襲著“元承宋統”的史觀,但在字裡行間,已經對元朝的統治,表達了些許不滿。
“若胡元之主中華,尤世運之丁極否。冠履倒置,天地晦冥,三綱既淪,九法亦斁(yi,有破壞之意)。第已成混一之勢,矧(shěn,有況且之意)復延七八之傳,故不得已大書其年,亦未嘗無外夷之意。”
在丘濬(1421—1495年)編纂的《世史正綱(1481)》一書中,有著比《續資治通鑑綱目》更為情緒化的議論:
“….自有天地以來,中國未嘗一日而無統也….而皆夷狄之歸,如元之世者也。三綱既淪,九法亦斁(yi,有破壞之意),天地於是乎易位,日月於是乎晦冥,陰濁用事,遲遲至於九十三年之久!中國之人,漸染其俗….忘其身之為華,十室而八九矣….”
與《續資治通鑑綱目》一樣,丘濬不僅視元朝的統治“三綱既淪,九法亦斁”,還痛心疾首地表示,“中國之人(明朝百姓)漸染其俗….忘其身之為華,十室而八九矣”(拓展閱讀:讀書筆記:明朝日常生活中的“蒙古風”)。
坦誠說,以上兩本書對於元朝的評價,與明初《敕建歷代帝王廟碑》中的“混一寰宇,紹正大統,以承天休而為民極”的認知,可謂大相徑庭。

丘濬(1421—1495),明朝著名的思想家 、史學家、政治家、文學家 ,被史學界譽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
3)元朝形象的徹底顛覆
到了嘉靖時期,元朝原本的正面形象被徹底顛覆。以周復俊(1496—1574)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們,對宋濂等人主持編撰的《元史》,進行了大肆抨擊,“(宋)寧宗開禧二年(1206),史臣大書元太祖,與宋寧宗並稱”,因謂“是書也賤夏尊夷,亂名沒實,蔑萬古帝王之正統,紊萬世是非之公議”。
由王洙主持編撰,成書於1546年的《宋史質》,更是徹底否定了元朝的“中國正統”地位。他將兩宋諸帝本紀列為《天王正紀》,而將元朝列為《天王閏紀》。
“按《通鑑》及《續綱目》俱以宋元並稱,祖宗號諡,視歷代帝王無異。今《史質》削‘大元’之號,而以閏紀名;去世祖皇帝等諡,而直書忽必烈等名;芟除其至元、大德等元,而概以一年、二年紀事。何哉?曰:所以辨人類而明天道也。”
由於《宋史質》裡的觀點實在是太過偏激,以致於同為“異族帝王”的乾隆嘲諷道,“....自有史籍以來,未有病狂喪心如此人者。其書可焚,其版可斧”(拓展閱讀:讀書筆記:乾隆是如何評價“遼金宋”“孰是正統”的?)。
4)結語
一言概之,“元朝印象”在明朝的“急劇惡化”,主要歸咎於明蒙關係的急劇惡化。對於“苦虜久矣”的明朝知識分子們而言,儘管他們很難藉助武力“幹掉”北元(蒙古),但完全可以從歷史和文化角度,對元朝進行徹底的清算和批判。
從近代“中國”的內涵演變看(拓展閱讀:什麼是“中國”:古代少數民族政權的“中國觀”),唯有強調“華夷一體”,進而構築更為與時俱進的“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才是維繫國家長治久安和繁榮昌盛的基礎(拓展閱讀:讀書筆記:黨和國家領導人,為什麼如此重視民族團結?)
另外,“元朝印象”在明朝的“奇幻轉變”,再次印證了那句耳熟能詳的“名言”——所有的歷史,本質上都是“當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