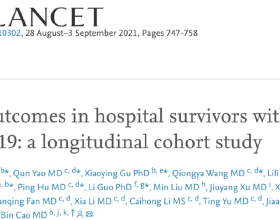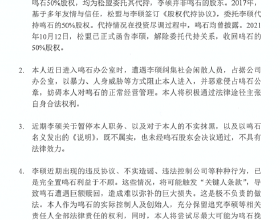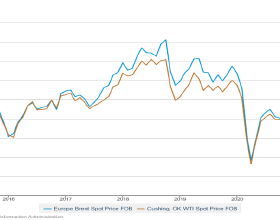保羅·費耶阿本德(1924-1994)認為,沒有科學方法之描述能夠廣泛到足以涵蓋所有的科學家所用的途徑和方法。他聲稱,在科學的發展中,不存在既有用又無特殊例外的方法論法則。費耶阿本德反對有意規定的科學方法,理由是任何這種方法會扼殺及鉗制科學進步。費耶阿本德聲稱“唯一不妨礙進步的原則是:什麼都可以”。
費耶阿本德認為,科學之始乃是一個解放運動,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越來越教條和剛性,因此已經越來越多地成為一個意識形態;儘管它十分成功,但科學已開始具備一些壓迫人的特性。他認為,不可能拿出一個明確的方法,把科學與宗教、魔法、或者神話區分開來。在他看來,科學作為指導社會的唯一主流思想,是專制和無根據的。這種認識論無政府主義(epistemological anarchism)的論調讓費耶阿本德從他的批評者口中獲得了“科學的最可怕敵人”之頭銜。
根據庫恩,科學本質上是一個集體行為,只能作為社群(科學界)的一部分被完成。在他看來,科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根本區別在於其社群的運轉方式。其他人特別是費耶阿本德和一些後現代主義思想家認為,科學和其它學科之間的區別沒有足夠的社群行為的差異來維持。在他們看來,社群因素對科學方法(之形成和改變)有重要和直接的作用,但區分不了科學和其他學科。根據此描述,科學是社會建構的,儘管這不進一步意味著科學事實是一種社會建構。
然而,有的人譬如蒯因仍堅持認為科學事實就是一種社會建構:
物理物件作為方便的中間物(中間變數)抽象地引入到(物理)情形中,不是根據經驗之定義,而是單純作為不可約之假定,在認識論上和荷馬史詩的眾神是平等可比的……對我作為業餘物理學家而言,我相信物理物件,而不是荷馬史詩的眾神;我認為不如此相信的話,便是一個科學錯誤。但在認識論的基礎,物理物件和神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區別,而不是在種類上。兩種型別的實體只是作為文化假定進入我們的觀念。
針對這樣的觀點,科學家一度公開地表示強烈反對,特別是在1990年代;這被稱為科學戰爭。
最近幾十年的一個主要發展,是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對科學社群的形成、結構和演化的研究,研究者包括大衛·布魯爾、S·巴里·巴恩斯(S. Barry Barnes)、哈利·柯林斯(Harry Collins)、布魯諾·拉圖與安塞爾姆·施特勞斯(Anselm Strauss)等等。來自經濟學的概念和方法(如理性選擇、社會選擇或博弈論)也已被應用於理解科學社群生產知識的效率。這個跨學科領域被稱為“科技與社會”(STS)。這裡的科學哲學的思路,是研究科學界實際中是如何運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