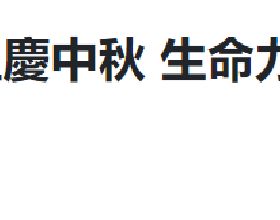雁鴨池為統一新羅時期文武王14年(674)修建的大型人工池塘。1975年,慶州文化財研究所發掘調查團在此處首次發現木簡,至今共出土木簡97枚(李柱憲《韓國木簡的考古發掘與整理研究》,《鄭州大學學報》2020年第4期),多為附札、荷札木簡,內容涉及東宮守衛及管理事務、食品帳簿、食物標籤及一些有關經典學習的習字簡。這些木簡是研究韓國古代歷史與東亞簡牘文化的重要一手史料。其中,雁鴨池213號木簡被劃歸為“門號木簡”。目前,學界對此木簡的研究集中於將木簡記錄的門號與遺址佈局相結合,復原東宮各宮門的位置,但對於木簡本身的性質及功用等方面的認知仍不十分明朗,存在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學界對雁鴨池213號木簡的研究
慶州雁鴨池出土的213號木簡為一枚雙面墨書木簡,長8.8釐米,寬1.45釐米,厚0.45釐米,其年代為統一新羅時代(668—901,即唐高宗總章元年至唐昭宗天覆元年)。
由於木簡字跡已經模糊不清,學界對其釋讀一度存在爭議。尹善泰曾比對7種關於雁鴨池213號木簡的釋讀文字,並指出木簡正反兩面書寫內容均為“策事門思易門金”,只是一面為草書,一面為楷書。這一釋讀結果得到了包括李京燮、李東珠、橋本繁等學者的認同。
而關於此枚木簡的性質,李文基認為此木簡與宮廷警備事務相關,而“金”代指掌管兩個門的人物的姓氏。但這一說法尚無確鑿證據,只是一種推測。隨後,尹善泰以日本木簡中的門號木簡作為“參照系”,指出雁鴨池213號木簡為一枚門號木簡,並指出“鎰”和“金”分別指“鎖”和“鑰匙”,這一結論得到了較為廣泛的認可。據此,李京燮、李海燕等學者認為,這是一件開啟“策事門”和“思易門”鑰匙的木楬附札。
就形制而言,木簡上端有兩個對稱的凹槽,可用繩子系掛於物品之上,這與國內出土的部分木楬較為相似。《周禮·天官》記載:“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汪桂海也曾指出簡牘中的籤牌應是繫結垂於案卷之外。但據此認定雁鴨池213號木簡即為鑰匙籤牌,似乎仍有難以理解之處。尹善泰在《雁鴨池出土“門號木簡”與新羅東宮的警備》(《韓國古代歷史》第44卷,2006年,第269—296頁)一文中列舉的四枚門號木簡內容分別為“器殿鎰”“東(殿)門鎰”“西門鎰/匙”和“南門匙”,由此可見這種標示某門鎖或鑰匙的木楬附札上理應只書寫有一個門的名稱。而“策事門”與“思易門”應為兩門,若此為兩門鑰匙的籤牌,那麼或一把鑰匙可以開兩門之鎖,或此籤牌上所繫為兩把鑰匙。如果是前者,則一把鑰匙對應兩把相同的鎖不合常理;如果是後者,則籤牌似乎並不能為分辨鑰匙提供方便,反倒更容易造成兩門的鑰匙混淆。因此,對於雁鴨池213號木簡的功用,可能還需要進一步討論。
由唐代文書行政制度看雁鴨池213號木簡
由於韓國傳世史料記載的缺失,較難找到能與木簡內容對應的相關記載。但鑑於韓國木簡上書寫的文字均為漢字,且已有包括李成市、戴衛紅等多位學者指出簡牘文化在東亞的傳播、流變路徑為由中國經朝鮮半島最終傳至日本,因此若要解讀韓國木簡的內容及功用,將其與同時代的中國古代史內容進行對照不失為一條路徑。
668年(唐高宗總章元年)9月,唐在平壤設安東都護府。據《舊唐書·地理志》記載:“總章元年九月,司空李勣平高麗。高麗本五部,一百七十六城,戶六十九萬七千。其年十二月,分高麗地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城以統之。”此外,《新唐書·地理志》也有記載,“總章元年,李勣平高麗國,得城百七十六,分其地為都督府九,州四十二,縣一百,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之,用其酋渠為都督、刺史、縣令”。從兩唐書的記載來看,唐高宗在平定高麗之後,唐代的職官制度、法律制度、文書制度等都對當地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因此,慶州市出土的與之同時期的雁鴨池木簡,其功用很可能與唐王朝內部用於宮門、城門的文書相似。
《唐六典》是關於唐代典章制度的一部集大成之作,據書中記載:
城門郎掌京城、皇城、宮殿諸門開闔之節,奉其管鑰而出納之。開則先外而後內,闔則先內而後外,所以重中禁,尊皇居也。候其晨昏擊鼓之節而啟閉之。凡皇城、宮城闔門之鑰,先酉而出,後戌而入;開門之鑰,後醜而出,夜盡而入。京城闔門之鑰,後申而出,先子而入;開門之鑰,後子而出,先卯而入。若非其時而有命啟閉,則詣閣覆奏,奉旨、合符而開闔之。
由此可見,唐代京城、皇城、宮殿諸門的開關有著嚴格的時間規定,若有特殊需要在非規定時間內開門,則需要皇帝旨意及相關的符類文書。李林甫等在作注時對此有進一步解釋,“殿門及城門若有敕夜開,受敕人具錄須開之門,宣送中書門下。其牙內諸門,城門郎與見直監門將軍、郎將各一人俱詣閣覆奏,御注‘聽’,即請合符門鑰,對勘符,然後開之”。由此可見,受敕開門之人所持之“符”上應書寫有全部需要開啟之門的名稱。
雁鴨池位於統一新羅時代太子宮遺址內,其宮門開閉可能也存在相類似的管理制度。213號木簡所記“策事門思易門金”,除具備木楬的功能外,很有可能還具有開門之“符”的功用。也即是說,當時持符人奉命需在非常規時間內開啟策事門和思易門,以此木簡作為開門憑證。如此一來便能解釋,為何木簡上會同時書寫有兩個門的名稱。因此,雁鴨池213號木簡很可能兼具“楬”與“符”的功能。
但需言明的是,這種出入憑“符”的制度在秦漢時期也能找到類似的痕跡。如龍崗秦簡中有“……于禁苑中者,吏與參辨券……”的記載。“禁苑”多指帝王的園林,雖與宮廷不同,但同為帝王所擁有的帶有私人性質的場所。依據簡文可知,在秦代便已存在出入帝王園林需持相關符券的措施。再如《漢書·成帝紀》記載,“(建始三年)虒上小女陳持弓聞大水至,走入橫城門,闌入尚方掖門”,顏師古注引應劭的說法指出,“無符籍妄入宮曰闌。掖門者,正門之旁小門也”。據應劭的解釋可知,至少在東漢時期,出入宮門也是需要有相關“符籍”的。據此可見,唐代的門符制度應是淵源有自。
由雁鴨池213號木簡看東亞文書行政的傳播
無論是依據形制還是書寫內容而言,韓國木簡都應是中國簡牘文化在東亞範圍內傳播的產物。李成市曾對木簡的傳播過程作出如下概括:中國大陸(A)→朝鮮半島(A’→B)→日本列島(B’→C),即簡牘文化在東亞的傳播路徑是由中國途經朝鮮半島,最終傳入日本,且在傳播過程中結合傳入地的歷史文化發生了一定的演變。但結合對雁鴨池213號木簡的討論,這樣的線性認知似乎仍略顯粗疏。
就目前已經刊佈的秦漢簡牘內容來看,符類公文書主要包括出入關符、吏及家屬出入關符、日跡符、警候符等,尚未發現如《唐六典》所記載的用於開門的符類公文書實物。這一現象意味著,文書行政制度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本身也是不斷髮展變化的。而文書行政制度由中國傳入朝鮮半島又是一個長時段的過程,因此其傳入與演變似乎較一個線性的過程更加複雜。這一傳播、衍變的經過或許可以概括為如下過程,即簡牘文化與文書行政制度在古代中國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也是在不斷調整變化的。在因革損益的變化過程中,不斷髮展的簡牘文化與文書行政制度陸續傳入朝鮮半島,經過與當地歷史文化結合後融合為古代韓國木簡文化與相應的文書行政制度,進而再經由朝鮮半島傳入日本,形成了古代日本木簡文化與文書行政制度。
(本文系韓國中央研究院韓國學資助專案“東亞文化圈視野下的韓國古代木簡研究”(AKS-2021-R-044)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