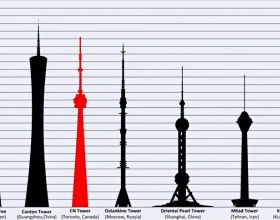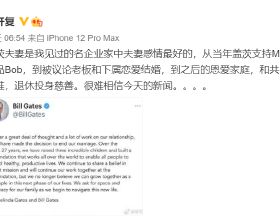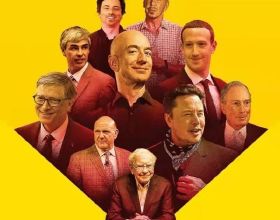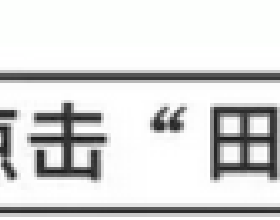“中國”一名,於三千年間沿用不輟,含義多有流變:從先秦的“中央區域”“城中”“邦國”“都城”之義,漢唐的“中土”“中原”之稱,再到近代演為與世界諸邦並列的民族國家之名,不僅詞形“中國”傳承不輟,“居中”詞義也一以貫之。
“中國”詞義的演繹,昭顯了中國人國家觀念以至世界觀念形成的歷史——從“天下中心”觀走向“全球一員”觀,這正是國人現代意識覺醒的標誌。
新的一年,讓我們重新瞭解“中國”!
文 | 馮天瑜 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聶長順 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編輯 | 謝芳 瞭望智庫
本文為瞭望智庫書摘,摘編自《三十個關鍵詞的文化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原標題為《中國》,原文有刪減,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1 “中國”得名
“中國”一詞較早出現於周初。1963年於陝西省寶雞縣賈村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銅器“何尊”(名“何”的宗室貴族之祭器),尊內底鑄銘文122字,記述周成王繼承武王遺志,營建成周(今洛陽),銘文轉述武王廷告辭雲:
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餘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
(武王克商後,在廟廷祭告上天曰:我要住在中國(天下的中央),由此統治民眾。)

2022年1月26日,“何以中國”展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舉行,觀眾欣賞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西周文物“何尊”。圖|中新社
這是迄今所見首出之專詞“中國”,意謂“天下之中央”。此“大邑商”指商朝(“邑”訓為“國”),因居中原,又稱“中商國”,簡稱“中國”,甲骨文學者胡厚宣說:“商而稱中商者,當即後中國稱謂的起源。”

故周武王稱自居“中國”,是對商代即“中國”的承襲。較早的傳世文獻《尚書·周書·梓材》亦有“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的用例,《詩經》《左傳》《孟子》等先秦典籍也多用“中國”一詞。
據學者統計,載“中國”一詞的先秦典籍25種,共出現178次——作“京師”義的9次,“國境內”義的17次,“諸夏領域”義的145次,“中等之國”義的6次。
“中國”初義是“中央之城”,即周天子所居京師(首都),與“四方”對稱,如《詩經·民勞》雲: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百姓夠勞苦的了,也該享受一下安樂了。撫愛這些京師人,用來安定四方。)
毛傳釋曰:“中國,京師也。”《民勞》篇四次出現“惠此中國”,其“中國”皆指京師。戰國時孟子追述,舜深得民心、天意,“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
這些用例的“中國”,均指居天下之中的都城,即京師,裴駰《史記集解》引東漢劉熙(約生於160年)之說: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
上例為本義京師的“中國”,以後又有多種引申:初指西周京畿地帶,繼演為諸夏列邦,即黃河中下游這一文明早慧、國家早成的中原地帶。如《春秋公羊傳》載“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這裡的“中國”即指中原一帶,西周時主要包括宋、衛、晉、齊等中原諸侯國,此義的“中國”後來在地域上不斷拓展,包括長城內外,北至漠河,南至五嶺、海南島,西及蔥嶺,東臨滄海的廣大區間。
此外,中國還派生諸義,如指國境之內;中等之國;中央之國;等等。
以上多種含義之“中國”,使用頻率最高的是與“四夷”對稱的諸夏義的“中國”。
如《詩經·小雅·六月序》雲:
《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南朝宋劉義慶(403—444)在《世說新語·言語》雲:
江左地促,不如中國。
諸例“中國”,皆指四夷萬邦環繞的中原核心地帶,即中央之邦。其近義詞有“中土”“中原”“中州”“中華”“中夏”“諸夏”“神州”“九州”“海內”等。近代通用之“中國”,指以華夏文明為源泉、中華文化為基礎,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國家。
2 歷史演繹之疆域
1.疆域變遷
“中國”是一個歷史概念,其所指範域在歷史過程中不斷異動。
中華先民心目中的世界,形態為“天圓地方”,古人把“中國”安置在這個“天圓地方”的世界之中央。以周代論,“中國”是以王城(或稱王畿)為核心,以五服(甸、侯、賓、要、荒)或九服(侯、男、甸、採、衛、蠻、夷、鎮、藩)為外緣的方形領域,作“回”字狀向外逐層延展,中心明確而邊緣模糊。
【注:“服”指祭奠死去親屬的服喪制,以喪服及服喪時間表示親屬之間血緣遠近及尊卑關係。】
在西周及春秋早期,“中國”約含黃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包括周王朝、晉、鄭、齊、魯、宋、衛等地,秦、楚、吳、越等尚不在其內,至春秋中後期以至戰國,這些原稱“蠻夷”的邊裔諸侯強大起來,便要“問鼎中原”,試圖主宰“中國”事務。至戰國晚期,七國都納入“中國”範圍,《荀子》《戰國策》諸書所論“中國”,已包含秦、楚、吳、越等地。
秦一統天下後,“中國”範圍更擴充套件至長城內外、臨洮(今甘肅)以東的廣大區間。班固(32—92)說:“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然西不過臨洮。”
漢唐以降,“中國”的涵蓋範圍在空間上又有所伸縮,諸正史多有描述,略言之,秦漢以下的大一統王朝,“中國”包括東南至於海、西北達於流沙的朝廷管轄的廣闊區間。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大體奠定中國疆域範圍:北起薩彥嶺,南至南海諸島,西起帕米爾高原,東極庫頁島,約1380萬平方千米。
19世紀中葉以後,帝國列強攫取中國大片領土,中國人民的英勇捍衛,使領土上避免更大損失。今中國陸地面積960萬平方千米,僅次於俄羅斯、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
2.“王者無外”
自先秦,已形成“天下一家”觀念,認為天子是諸侯共主,諸侯國(外)土地皆歸天子(王)所屬,這便是“中國”疆域的“王者無外”觀(帝王以天下為一家,四域皆在王者治下)。此語初出《公羊傳》:“天王出居於鄭。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
秦漢大一統,“中國”疆域“王者無外”說更為張大。東漢班固《東都賦》雲:“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晉葛洪《抱撲子·逸民》:“王者無外,天下為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其境也。”把“日月所照,雨露所及”之處皆納入中國之境。唐宋普遍承此認知,杜甫詩云“王者無外見今朝”;宋人田錫雲:“日南萬里,設都護以懷柔;漠北五原,化單于之獷驁。有以見王者無外,書軌大同。”
以文化一統,導致天下一統,是古華夏的一種流行觀念,認為凡有“向禮”之心,夷狄即歸向“中國”,這是“王者無外”疆域觀的一種思路;同時,華夏人又把文化普被四夷,達成天子“四海為家”,是“王者無外”疆域觀的又一種思路。
這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中國觀的鋪演。這種雖宏大卻模糊的中國觀,影響久遠,又在歷史程序中不斷修正,逐步規範進較具體真切的“中國”框架之內。
3 歷史演繹之文化
1.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
“中國”原指黃河中游(包括汾河、渭河、涇河、洛河等支流河谷)這一華夏族的活動區域,時人認為地處天下之中,故“中國”具有地理中心意味;因都城建此,又衍出政治中心義;由於文化發達,進而派生文化中心義。
戰國趙公子成駁斥趙武靈王(前340—前295)仿行“胡服騎射”時,如此論“中國”:
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
公子成在趙王室圍繞“中國”“蠻夷”關係的辯論中,闡發了“中國”的文化中心內蘊。此後兩千餘年間,人們多在這一含義上論“中國”。
自先秦以至漢唐以迄明清,這種華夏中心的世界觀念和華夷二元對立的國際觀念,一直延傳下來,並得到強化,“四夷賓服,萬國來朝”是“中國”歷代統治者的期待。直至近代遭遇工業化西方入侵,朝野還遲遲未能擺脫此種自我中心主義。
晚清記名海關道志剛(1818—?)1868年出訪歐洲(其時清朝已遭兩次鴉片戰爭打擊,被迫出使泰西),外人問及“中國”的含義,志剛答曰:
中國者,非形勢居處之謂也。我中國自伏羲畫卦已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所傳,以至於今四千年,皆中道也。
此言淡化“中國”的地理中心義,強化其文化中心義,將“中國”釋為“中道”,凡不符合中道者即非中國,志剛雲:“英吉利富強已極,頗有持盈之慮”,“法郎西誇詐相尚,政以賄成”,皆不合中道,故不為中國所尊敬。
2.文明中心多元論、文明中心轉移論
在“中國者,天下之中”觀念籠罩的時代,也有人以理性態度為自國作世界定位。
自周秦之際,華夏文明向東、西、南、北方向拓展,出現新的文明興盛區,固有的文明區有的退化,這使清醒的先賢意識到“中國”並非凝固不變的,中原並非永遠先進,如明清之際哲人顧炎武(1613—1682)指出:“歷九州之風俗,考前代之史書,中國之不如外國者有之矣!”
這裡將“中國”與“外國”對稱,而且“外國”(指周邊夷狄)有超過中國的地方。
與顧氏同時期的王夫之(1619—1692)認識到文明中心是可以轉移的,他在《讀通鑑論》《思問錄》等著作中,對“中國”與“夷狄”之間文野地位的更替作過論述,用唐以來先進的中原漸趨衰落,蠻荒的南方迎頭趕上的事實,證明華夷可以易位,“中國”地位的取得與保有,並非天造地設,而是依文化不斷流變而有所遷衍。
王夫之還指出,中國不是從一開頭便十分文明,中國也並非唯一的文明中心,他有一種富於想象力的推測:天地之氣,衰旺彼此迭相易也。太昊以前,中國之人若麇聚鳥集。非必日照月臨之下而皆然也,必有一方如唐、虞、三代之中國也。
認為上古時“中國”之人如同禽獸聚集,而在日月共照之下的某些地方也可能如同三代中國那樣擁有文明,這是理性的中國觀和多元的人類文明生成觀。
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1981年5月在“中國民族關係史研究學術座談會”上,就如何把握“中國”這一概念,有幾點說明:
其一,我們的祖國“是各族人民包括邊區各族所共同締造的,不能把歷史上的中國同中原王朝等同起來”;其二,“既不能以古人的‘中國’為歷史上的中國,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國範圍來限定我們歷史上的中國範圍”;其三,中國“是五十六個民族共同的,而不是漢族一家的中國”。其說有助於澄清關於“中國”的認識。
4 “萬國之一”的“中國”
以“中國”為非正式國名,與異域外邦相對稱,首見於《史記》載漢武帝(前156—前87)派張騫(約前164—前114)出使西域:
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乃令騫因蜀犍為髮間使,四道並出。
這種以“中國”為世界諸國中並列一員的用法,漢唐間還有例證,如《後漢書》以“中國”與“天竺”(印度)並稱;《唐會要》以“中國”與“波斯”“大秦”(羅馬)並稱。但這種用例當年並不多見。
“中國”作為與外國對等的國家概念,萌發於宋代。
漢唐時中原王朝與周邊,維持宗主對藩屬的冊封關係和貢賚關係,中原王朝並未以對等觀念處理周邊問題;宋則不然,北疆出現與之對峙的契丹及党項羌族建立的王朝——遼與西夏,是兩個典章制度完備、自創文字並且稱帝的國家,又與趙宋長期處於戰爭狀態,宋朝一再吃敗仗,以致每歲納幣,只得放下天朝上國的架子,以對等的國與國關係處理與遼及西夏事務,故宋人所用“中國”一詞,便具有較清晰的國家意味。
“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1005—1045)首次以“中國”作專論:
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
四夷處四夷,中國處中國,各不相亂。
石介雖仍持“內中外夷”觀念,但已經有了國家疆界分野,強調彼此獨立,“各不相亂”。宋以後,“中國”便逐漸從文化主義詞語向國家意義詞語轉變。
一個朝代自稱“中國”,始於元朝。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派往日本的使臣所持國書,稱己國為“中國”,將日本、高麗、安南、緬甸等鄰邦列名“外夷”。明清沿襲此種“內中外夷”的華夷世界觀,有時也在這一意義上使用“中國”一詞,但仍未以之作為正式國名。
時至近代,國人逐漸從“往日之觀天坐井”,變為“測海窺蠡”,中國觀發生變化。
清末鄭觀應(1842—1922)突破“王者無外”、中國在世上“定於一尊”的傳統觀念,指出,國人必須“自視其國為萬國之一”,方能改變“孤立無援,獨受其害”的窘況。
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梁啟超論及中國積弱“發源於理想之誤者”有三,其二為“不知國家與朝廷之界限也。吾中國有最可怪者一事,則以數百兆人立國於世界者數千年,而至今無一國名也。夫曰支那也,曰震旦也,曰釵拿也,是他族之人所以稱我者,而非吾國民自命之名也。曰唐虞夏商周也,曰秦漢魏晉也,曰宋齊梁陳隋唐也,曰宋元明清也,皆朝名也,而非國名也。蓋數千年來,不聞有國家,但聞有朝廷。”
同年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中再次痛議:
吾人所最慚愧者,莫如我國無國名之一事。
與無國名相聯絡,還有無國旗、無國歌等尷尬情形,至近代方逐漸得以改變,“中國”作為國名開始確立。
5 民族國家之“中國”
民族國家意義上的“中國”概念,是在與近代歐洲國家建立條約關係時出現的。
歐洲自17世紀開始形成“民族國家”(nation state),並以其為單位建立近代意義上的國際秩序。歐洲三十年戰爭結束,1648年西班牙、神聖羅馬帝國、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法蘭西波旁王朝、瑞典等國在今德國的威斯特伐利亞舉行會議,簽訂《威斯特法利亞和約》,承認諸國領土、主權及國家獨立。此為民族國家得以確認的開端,被譽為“影響世界的100件大事”之一。
遠處東亞的清朝對發生在歐洲的重大事變全無所知,卻因與全然不同於周邊藩屬的西方民族國家(如俄羅斯)打交道,須以一正式國名與之相對應,“中國”便為首選。這種國際關係最先發生在清俄之間。
彼得一世(1672—1725)時的俄國遣哥薩克鐵騎東擴,在黑龍江上游與康熙皇帝(1654—1722)時的清朝軍隊遭遇,爭戰後雙方於1689年簽訂《尼布楚條約》(俄方稱《浧爾琴斯克條約》),條約開首以滿文書寫清朝使臣職銜,譯成漢文是:“中國大皇帝欽差分界大臣領侍衛大臣議政大臣索額圖”,與後文的“斡羅斯(即俄羅斯)御前大臣戈洛文”相對應,康熙朝敕修《平定羅剎方略界碑文》,言及邊界,有“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為界:河之南岸屬於中國,河之北岸屬於鄂羅斯”等語,“中國”是與“鄂羅斯”(俄羅斯)對應的國名。
17世紀末葉清朝與俄羅斯建立條約關係還是個別事例,此後清政府仍在“華夷秩序”框架內處理外務,如乾隆皇帝(1711—1799)八十大壽時,與英王喬治三世(1738—1820)的往還信函中,英王國書恭稱“向中國最高君主乾隆致意”,多次稱清方為“中國”,而乾隆皇帝復喬治三世書從未稱己國為“中國”,通篇自命“天朝”。此種情形一直延及嘉慶皇帝(1760—1820)與英王喬治三世的來往檔案中。
可見,直至第一次鴉片戰爭前,中國朝野只有內華外夷的“天下”觀、“天朝”觀,沒有權利平等的國家觀、國際觀。
至19世紀中葉,西方殖民主義列強開啟清朝封閉的國門,古典的“華夷秩序”被近代的“世界國家秩序”所取代,“中國”愈益普遍地作為與外國對等的國名使用,其“居四夷之中”的含義逐漸淡化。
漢文“中國”正式寫進外交文書,首見於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四日(1842年8月29日)簽署的中英《江寧條約》(通稱《南京條約》),該條約既有“大清”與“大英”的對稱,又有“中國”與“英國”的對稱,並多次出現“中國官方”“中國商人”的提法。此後清朝多以“中國”名義與外國簽訂條約,如中美《望廈條約》以“中國”對應“合眾國”,以“中國民人”對應“合眾國民人”。
近代中國面臨東西列強侵略的威脅,經濟及社會生活又日益納入世界統一市場,那種在封閉環境中形成的虛驕的“中國者,天下之中”觀念已日顯其弊。具有近代意義的“民族國家”意識應運而生,以爭取平等的國家關係和公正的國際秩序。
而一個國家要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擁有一個恰當的國名至關重要,“中國”作為流傳久遠、婦孺盡知的簡練稱號,被朝野所襲用。梁啟超、汪康年(1860—1911)等力主揚棄中國為“天下之中”的妄見,但認為“中國”這個自古相沿的名稱可以繼續使用,以遵從傳統習慣,激發國民精神。
近代興起的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運動,更賦予“中國”以愛國主義內涵。
1900年9月24日,自強氏撰《獨立論》,稱“中國者,吾中國人之中國,非他人所得而保全也;保全中國者,吾中國人自己之責任,非他人所得而代之也”。此後,此一句式廣為使用。1905年還寫入《同盟會方略》:“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這便是在近代民族國家意義上呼喚“中國”,漸成國民共識。
梁啟超更作《少年中國說》,高唱:
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公元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成立,國際通稱Republic of China,簡稱“中國”,英文為China。自此,“中國”成為現代國家概念的正式名稱。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亦以“中國”為其簡稱。“中國人民”“中國政府”等短語亦隨之通用於世界。
“中國”一名,於三千年間沿用不輟,其詞義屢有遷衍:由初義“京畿之地”“四夷之中”,演為“中原”“中土”,乃至近代成為“萬邦之一”的正式國家稱號。“中國”詞義的演繹,昭顯了中國人國家觀念以至世界觀念形成的歷史——從“天下中心”觀走向“全球一員”觀,這正是國人現代意識覺醒的標誌。
《三十個關鍵詞的文化史》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本書擷取三十個關鍵詞,依生成機制,分為古典引申、語義假借、借形變義、新名創制、僑詞來歸、名實錯位六大類,在古今東西的時空座標上,追索其概念的生成、演變歷程,誠如陳寅恪所言“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