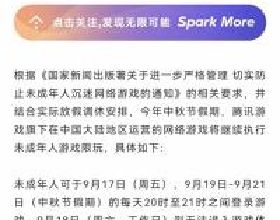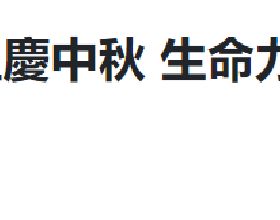郭剛堂“尋子成功”的事情,曾因“郭新振”的去留問題觸發輿論爭議。從某種層面上而言,郭剛堂在“郭新振”的去留問題上反倒比輿論層面的圍觀者們看得更開。之所以這樣講,一方面在於郭剛堂“尋子成功”後確實很剋制,另一方面在於郭剛堂“談團圓後首箇中秋”時心境很開闊。
就比如在專題採訪《不再失孤》的敘事裡,迎著中秋的氛圍,郭剛堂談及“失子”、“尋子”、“得子”的細節和過程可謂感概繁多,所謂回溯過去24年所發生的一切,就好像是在複述別人家的悲喜。
要知道郭剛堂曾在“尋子成功”後接受媒體採訪時稱:“找到固然好,找不到總還是要生活”。言外之意,那些絕望的“摩托尋子歲月”更像是“自我消愁”的過程。我們可以想象一個人兩個月瘦49斤,並且頭髮開始逐漸變白是什麼滋味。
然而這些維艱之苦卻並沒有把郭剛堂擊倒。按照郭剛堂的說法,從2006年開始就不再只是尋找自己的兒子,也就是從“郭新振”被拐的第9個年頭,他已經開始幫助更多失子(女)者們找孩子,緊接著在2012年還建立了“尋親網站”,2014年成立了“尋親協會”。
到此為止即便還不能說郭剛堂徹底放下自己的悲苦,但是卻可以確信他在悲苦之外正在尋找撫慰悲苦的意義。就如郭剛堂所言:“拐賣行為是一種超越謀殺的罪惡,所有被拐賣的孩子都是第一受害者”。言外之意,郭剛堂堅信被拐賣的孩子比親生父母更悲慘,基於此再去理解他尋子成功後的剋制,大概就更為容易些。
當然最為令人感到敬畏的是,當郭剛堂指著自己電腦裡儲存著的那些被拐孩子的照片時,卻感慨“這都是期望”,“這都是希望”,“這些人裡面有多少像你郭剛堂(郭新振)這麼幸運”,與此同時還較為深情地強調“找到找不到總有遺憾”,“即使沒有圓滿,但我們要找到自己的一個定位”。最後郭剛堂還發出宏大的樸素祈願:希望透過大家的共同努力,可以讓更多的孩子、更多的家庭在八月十五的時候,迎來更多的團聚。
要知道善意是人性,惡意也是人性。只可惜在現實的紛雜裡,談及人性是非總是更強調人性的惡意。以郭剛堂“尋子成功”的事情來講,輿論層面不自覺地指向兩極:“正極”、郭剛堂和妻子不容易,郭剛堂和妻子“很幸運”等等;“負極”、必須嚴懲“拐賣者”,養父養母也是“共犯”,“郭新振”只有離開養父養母才是正確的選擇等等。
一言以蔽之,人們雖然知道“正極”是當前最該被重視的事情,但是輿論呈現上反而更青睞“負極”。在這個問題上,輿論層面雖然強調血親彌合,強調親情補償,但卻並沒有設身處地的基於人本身的困境去考量。
好在郭剛堂十幾年前可能就已經想通,要不然很難在“尋子成功”後保持這般剋制(這裡強調認親後關係處理上)。只是回到感性的立場上,郭剛堂即便提前暗示自己“我不會哭”,但是在認親現場最終還是沒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緒,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到那兒就不行了”。
漢娜·阿倫特說:“意義永遠不可能是行動的目的,而在行動終止後,意義就不可避免地從人類的所作所為中產生了”。之所以要拿這句話註解郭剛堂的尋子故事,並不在於郭剛堂的“尋子行為”和“尋子結果”一定存有關係,而在於“尋子行為”讓“尋子結果”變得更為可貴,並且更為寫意的讓失子(女)悲苦顯現人間。
嚴格來講郭剛堂的“尋子行為”跟“尋子結果”關係不大(這裡指功效關係),甚至就《失孤》電影來講,也談論的不是“尋子行為”跟“尋子結果”的關係,更多是想剖開拐賣行為對於一個家庭的打擊有多重,與此同時也是為告訴人們血親之愛即是大愛也是大縛。
所以對於郭剛堂來講,他能從“自我救贖”轉向“救贖別人”,這就說明他已經從“尋子目的”轉向“尋子意義”,於此再去看待他對“郭新振”去留的剋制就更為容易。畢竟能在重擊中依然站起來的人,總還是有大徹大悟的精神存在。
只是回到專題《不再失孤》的公共敘事層面,就算郭剛堂發出再怎麼美好的祈願,那也只是他作為失子(女)者的一種希望,而對於那些依然在尋子(女)悲途中的失子(女)者們,還需要靠自己去掙脫大愛中的大縛。
就如郭剛堂談到每年中秋節的儀式感時,他說會放孩子那兒一份(碗筷)。言外之意,心心念唸的兒子不只是“具體的肉身”,更多是關係層面的缺憾。從某種層面上而言,這就跟親人逝世初期,生者不由得生出那種空蕩感很像,並且感受更為刺痛些。
於此在看待郭剛堂時就該分為“失子者郭剛堂”和“尋親者郭剛堂”。“失子者郭剛堂”主要強調尋子的悲苦和《失孤》的敘事,而“尋親者郭剛堂”顯然已經超越自身,他需要更剋制,也需要更溫暖。因為比起對於“尋子(女)成功的祝福”,可能那些尋不得的人們更需要撫慰和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