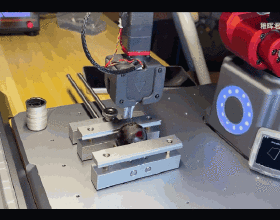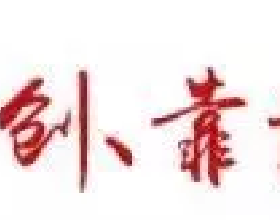□ 楊源哲 沈瑋瑋
因鎮壓太平天國戰爭之需要,清代將中央權力逐漸下放地方,這包括由皇帝所掌控的刑殺大權,以就地正法之制,旁落到地方各級督撫。《清史稿·刑法志》載“時各省軍興,地方大吏,遇土匪竊發,往往先行正法,然後奏聞。”因關於地方大吏具體包括哪些人等,律法並未規定,因此在天高皇帝遠的地方,除督撫以外的地方官員甚至到後來團練、紳民都可以行就地正法之權。例如咸豐三年(1853年)二月初八“福濟奏覆遵派委員嚴查渡口以防奸細情形折”記載“若搜出奸細實據,許民擅殺”。再如,同年十二月十八日“王茂蔭奏請降特旨準令脅從投出嚴禁官軍殺戮折”記載“釋放回籍之人,久染賊習,沿途復肆搶劫……苟有犯此者,則令各地方官拿獲即行正法,許各地方民格殺勿論,更復何惜。”清廷本想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治理地方亂世,以刑去刑,然而卻造成了皇權式微、中央失勢的後果,可謂因小失大。這是傳統中國社會秉承“亂世用重典”治理國家的反例,其主因在於就地正法之制在適用物件、適用程式、適用區域和適用方式上的全面失控,完全超乎制度常態,毫無制度理性可言,實為晚清國家失序之濫觴。
適用物件
就地正法主要針對的是太平天國起義軍,適用物件首先是太平軍高階將領和官員,以及太平天國的前身拜上帝教之頭目。在太平天國起義時,北方捻軍叛亂,自咸豐三年(1853年)到同治七年(1868年)才被全部殲滅。各地民眾也紛紛掀起了反清浪潮,如上海小刀會起義。清廷在鎮壓這些起義的過程中,自覺適用了就地正法,包括反清人士家屬以及提供幫助的民眾和清軍。即便是非暴力反清的,依然可以適用就地正法。如咸豐三年(1853年)五月十六日“論內閣著將妄陳圖讖搖惑人心之監生錢江斬首梟示”記載了已革監生錢江妄陳圖讖,蠱惑人心,後被訊明後立即正法。
各地匪盜乘機起勢,他們往往與太平軍、捻軍合作甚至加入到太平軍、捻軍中,使清軍遭受重創。地方督撫不得不用就地正法來打擊盜匪。咸豐元年(1851年)九月二十九日,廣西巡撫鄒鳴鶴奏報宜將匪分為盜匪、會匪和遊匪。對情罪重大的盜匪在訊供明確後即行正法,咸豐帝批示道:“知道了,嗣後仍著照此辦理。”會匪是指以反清為宗旨的秘密社團,以天地會最具有代表性,很多天地會成員都加入了太平軍。咸豐三年(1853年)二月初十“曾國藩奏覆遵旨會商撥兵募勇各事宜及嚴辦湖南會眾等情折”中便提到“去年粵逆入楚,凡入天地會者,大半附之而去。”故天地會成員是就地正法的物件之一。咸豐元年(1851年)十月二十日“塞尚阿奏報生擒會首何名科等並就地凌遲處死折”記載了廣東信宜天地會領導者何名科在被抓獲審明確認後,就地凌遲處死。除了天地會外,還有“串子會、紅黑會、半邊錢會、一股香會”等。遊匪則分為三種:隨處搶劫的兵勇、戰區隨時劫掠的民眾、混雜于軍營附近實施偷竊,假冒餘丁等遊手好閒者。咸豐三年(1853年)二月二十日“諭內閣著琦善等查拿沿途擾害之鄉勇就地正法並飭所過地方官一體嚴緝”記載了將沿途擾害鄉里的廣東各勇嚴行查拿,就地正法;允許團練紳民在遇到類似兇徒時可以格殺勿論。尋常痞匪,如奸胥、蠢役、訟師、光棍之類,也可以就地正法。咸豐三年(1853年)三月十七“崇綸奏報到任後籌辦善後防堵安擾等事宜折”記載了將實施焚殺搶劫行為的土匪、痞棍中積惡著兇者就地正法並梟示。就地正法已經成為整肅地方治安的主要甚至唯一辦法,地方治理已經完全超越法外。
太平天國兵勇每到一地便開啟監獄釋放囚犯,重犯往往與其結為死黨。為剷除太平天國,清廷需要先處決重囚。於是,咸豐三年(1853年)五月皇帝命令河南巡撫陸應谷將距離與太平天國交戰區較近的州縣查明在押犯人,將其中因搶劫以及用火器殺人而待決的人犯先行正法,秋審程式自動廢除。可以說為達到鎮壓太平軍的目的,就地正法已經凌駕於《大清律例》之上,成為特殊時期的一根“救命稻草”。
部分官員若在戰爭中失職、瀆職或者膽怯臨陣脫逃,亦適用就地正法。例如咸豐三年(1853年)二月初七“和淳奏請將現交刑部治罪之徐廣縉陸建瀛即在軍前正法折”認為湖廣總督徐廣繕在奉命剿辦逆賊時有意遲延,有瀆職表現;湖廣總督陸建瀛在奉命剿匪途中,聽聞前路失利後臨陣脫逃,以致城池失守,故請旨將其即軍前梟首。臨陣脫逃計程車兵也在就地正法之列,《就地正法章程》已經成為軍民混用的戰時特殊且唯一的訴訟程式法和刑法。
適用程式
逐級審轉複核製為清代常規的司法審判程式,這一程式複雜且漫長,無法應對戰時需要。於是,清廷制定了《就地正法章程》,“章程本為軍務而設”之說便來自於此。然而,即便是精簡過後的就地正法程式也需經過審轉複核,以防濫用。章程規定,發生在距省城較近的州縣案件,先由州縣審訊,然後押解到府道複審,再解審到按察使複審,最後解審到督撫,由督撫決定是否就地正法。發生在距省城較遠的州縣案件,罪犯不再被押解到省城,只是將錄供由府或者道,經按察使司詳稟督撫,最後由督撫決定。即督撫掌握了就地正法大權。在具體適用過程中,此法則逐漸淪為具文。
咸豐三年(1853年)正月十九日“袁三甲奏陳推闡諭旨關於軍務情形折”載,可將被生擒的結夥搶劫人犯,交由該府縣官審明正法,不需押解到省城。且允許民團在抓捕過程中正法反抗者。在太平天國時期,將犯人押解到省城的情形只是特例,正常情況下府縣一級都可審訊並就地正法。值得注意的是,不僅適用主體擴大化,適用物件也從太平軍首領大員,被有意擴大到各種借戰亂而滋事的盜匪。
官員適用就地正法的前提是要認真“訊明”,但連皇帝也帶頭公然違反。咸豐三年(1853年)八月初三“瑞昌奏報拿獲逃敵並請應否前往懷慶進剿折”記載了總協領奇凌阿報稱抓獲一名形跡可疑之人,在嚴加審訊後他承認姓廬名道談,以搶劫為生。因其供詞有疑,奇凌阿將該犯押解到知州衙門暫行監禁,然後請旨將其即行正法,咸豐帝卻批示道:“即應正法,何必交地方官,太屬拘泥。”這實際上是在鼓勵清軍將領只要懷疑其可能是太平軍或者其他反清人員,又或實施搶劫、盜竊等匪患都可以就地正法,而不需要訊明。
如此不依法就地正法,讓手握大權的地方官員草菅人命。《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記載了自道光三十年(1850年)至同治五年(1866年)共17年的處死犯人數量:明確標明就地正法的達到兩萬八千餘人,以先行正法等處死的達到了七萬六千餘人,共計十萬餘人。而據《清實錄·乾隆朝實錄》載,自乾隆元年(1736年)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共23年處決的人犯才6293人。以速戰速決鎮壓太平天國,成為清廷上自皇帝下到官紳的共識。
具體而言,在太平天國起義之初和即將失敗時,就地正法適用較少。據統計,道光三十年(1850年)僅686人、咸豐二年(1852年)747人、同治五年(1866年)974人。在太平天國起義興旺之時,就地正法便頻繁出場。最多的是咸豐五年(1855年),達兩萬餘人,其次是咸豐十一年(1861年)為一萬餘人。同時,咸豐五年(1855年)的十一月初一“胡林翼奏報會剿蒲圻獲勝並請分別獎恤出力陣亡人員折”中記載“生擒一萬七千餘名,就地正法。”這是檔案所見一次正法人數之最,就地正法在實踐過程中已經失控,成為殺人利器。
適用區域
就地正法的適用區域是緊跟著太平軍進攻時間和地盤發展而定的。從道光三十年(1850年)到咸豐元年(1851年),就地正法主要適用於廣西。因廣西是太平天國的發源地,在沒有制度依據的前提下,皇帝默許了地方督撫的就地正法之權。如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一月初五“鄭祖琛等奏報捕獲鍾亞春等並進剿金田等處情形折”記載“所有生擒各犯,飭據該委員許悙書,會都府縣逐一提訊,內有情罪重大及被擊格傷者……就地正法,以儆奸頑。”咸豐二年(1852年)四月五日,太平軍從永安突圍,五月十九日進入湖南。有一部分太平軍則進入貴州,該年湖南、貴州等地便開始適用就地正法。
咸豐三年(1853年)一月太平軍攻克武昌,三月攻佔南京,並定都於此,隨後北伐及西征。此後三年間,就地正法的適用區域便擴及到江蘇、河南、山西、直隸、山東、江西、福建、湖北、陝西等地。河南、山西、直隸、山東等北伐軍經過的區域,在北伐軍被消滅後,就地正法並沒有被大範圍沿用。而被太平天國西征佔領的江西、湖北,後成為太平天國21省之一,因此是適用就地正法的重要區域。除此之外,福建、陝西、廣東、湖南、四川、臺灣等省也適用了就地正法。
在天京事變後,太平天國的控制區域大大縮小,後來攻下江浙,轉戰川、黔、滇三省。因此,咸豐六年(1856年)至同治五年(1866年),就地正法就擴大到了浙江、廣西、四川、雲南、貴州等地。當然,在太平天國勢力尚未波及之地,只要存在反清分子甚至盜匪現象,地方就沿用就地正法,簡單省事。
適用方式
斬絞是清代執行死刑的常規方式,就地正法大多采用的也是這兩種傳統法典所認可的極刑或重刑,以此震懾敵匪。例如咸豐元年(1851年)六月初七“賽尚阿奏報綏靖官兵及壯勇等於中坪仁義等村三獲勝仗折”記載了九名賊匪“立時斬首”。咸豐三年(1853年)二月十八日“呂賢基奏報皖省股眾蜂起擬暫駐宿州剿辦折”記載了土匪被立即斬首梟示。同年三月十四日“周天爵奏報剿除陸遐齡等股四獲勝仗情形折”記載將李邦治等十二人全部駢首梟示。駢首梟示即兩頭相連懸掛於木上示眾,可謂晚清新創之法。
凌遲也被適用於就地正法。例如咸豐四年(1854年)閏七月十二日“向榮奏報師船續獲勝仗並陸路佈置防剿情形折”記錄了一百一十名賊人分別被凌遲正法。一些附加刑,如刺目凌遲等相繼被用於就地正法。咸豐四年(1854年)九月二十七日“曾國藩等奏報陸軍克復國水師於蘄州獲勝折”記載了生擒的一百三十四名逆匪被刺目凌遲。而且對捕獲的太平軍高階將領則開始使用剜心之法,如咸豐二年(1852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徐廣縉奏報查明敵首肖朝貴實被轟斃等情形折”記載了羅五等太平軍高官在被抓獲後被立即剜心致祭。除此之外,還有槍斃、淹斃、肢解、寸磔等上古時期的殘酷肉刑重現於世,不僅復古,而且不斷加碼,慘不忍睹。
晚清在鎮壓地方動亂之際,將特殊刑罰變成唯一刑罰,完全放棄了一般審判程式,故意曲解“亂世用重典”的本意,讓“亂世用亂刑”變得理所當然,失去了治理理智和制度理性,隨心所欲。此種為所欲為的用刑習慣和粗暴簡單的治理方法一旦養成,必會更加肆無忌憚,朝廷欲重新約束或規範談何容易。就地正法這一特殊時期的刑事政策之法,恰是晚清政府大勢已去的制度誘因。
(作者單位:廣東技術師範大學法學與智慧財產權學院;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
文章來源:智慧普法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