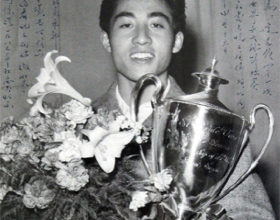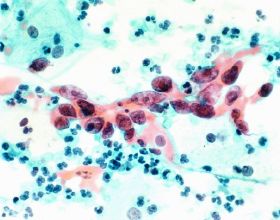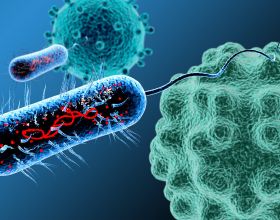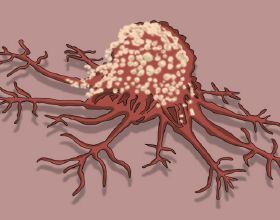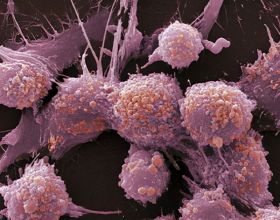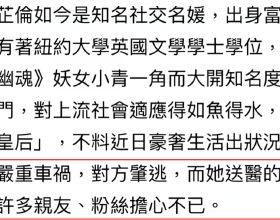一、
心無志者,而人則不立。
這句話中所說的“志”不是指關於事業的志向,而是內心修行正向意識的念頭,人生的很多問題都是以心為根本主宰,當內心存在正心正念的時候,外在的很多糾葛問題才能用這份正向力量去化解。
《孟子》之中有這樣一段對話: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
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有一天,公都子問孟子:“同樣是人,有的是君子,有的是小人,這是為什麼?”
孟子就說:“從心志上去用工夫的,就是君子;從耳目一類的小體上去用工夫的,就是小人。”
公都子又問:“同樣是人,有人從心志上去用功夫,有人從耳目一類的小體上用功夫,這又是為什麼呢?”
這個時候孟子就回答說:“耳朵、眼睛這類器官不會思考,所以被外物所矇蔽。耳朵、眼睛也只不過是物,它們與外物接觸,只能起到引導的作用。心的功能在於思考,思考了就會有所得,不思考就會一無所獲。這是上天賜予我們人類的功能。所以先把心志這一大的方面樹立起來,那麼,那些次要的方面就不能侵奪它了。這樣就能成為君子。”
其實孟子所說的這一番話,就是由內心培養正心正念之後,再由心去主導外在事物的道理。
從佛家的角度來說,人有眼耳鼻舌身意,去感知外在的色聲香味觸法,在此過程中,心中存在的貪嗔痴慢疑等本性問題,又會驅使自己在感知的過程中產生各種紛雜的思慮慾望。
一個人如果在此過程中,沒有正心正念作為主宰,那麼當這些思慮和慾望升起的時候,他的意識和行為就會隨著這些慾望而前行,那麼就會很容易做出背離道德和法律的行為。
就像孟子所說的,“耳朵、眼睛這類的器官它不會思考,所以它會被外在的事物所矇蔽”,其實被矇蔽的過程,就是因為心中沒有正心正念之後,被慾望主導了自身而已。
當一個人由自己的感官感知外界,同時因為自己內心弱點衍生出念頭與行為之後,那麼君子和小人之間的區別就出來了。
如果能夠控制住自己,守住自我原則,做出正確的舉動,這就是君子。反之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行為,任由自己的妄想意識指引著自己,去尋求一些世俗的歡樂和滿足,他無疑就會進入到小人的行列之中。
那麼解決這一切問題的根本在哪裡呢?就是在自己心裡要有主宰。
這個主宰可以理解為對道德的堅守,對於原則的奉行,也可以理解為對天地之道的敬畏,等等,不管這個心裡面存在著這是什麼樣的狀態,歸根結底,它一定是正向的,一定是有原則,有底線,有道德的。
二、
孟子在這裡,也把“在心上用功”與“在耳目上用功”分為兩者,一個為“大體”,一個是“小體”。“大體”就是仁義之心,而“小體”就是自己的耳目之欲,一個人只有把自己的“大體”培養起來之後,也就是把自己的心志方面樹立起來,那麼小體就不會偏頗,小體同時也就不能侵奪大體。
這也是我們在之前的一些文章中闡述過的“內心由正念主宰,外在行為才會不失偏頗”的道理。
這個時候很多人就會有一個疑惑,這個疑惑還是從世俗表象上出發所提出的,那就是修行正心正念正行的意義在哪裡?
因為在一個物慾橫流的時代,讓很多人形成了一種畸形的價值觀,就是人只有瘋狂斂取錢財,多行不義之事,好像才更能佔到便宜,那麼既然如此,心存善念,修行正心的意義是什麼?
這個問題,也是我們今天文章的核心。
其實人生心存仁德的目的,是為了發展自己生命的本來意義,這種意義包含著世俗認可的收穫,但同時也包含著高於世俗的價值。
當一個人以正心正念修正自我之後,他就能以這份正向的力量引導自己的思想與行為,從而為自己創造良好的生命結果。
因為,只有用正確的方式生活才能獲取正確的結果,所以能將這份力量融化在自己的心性言行之中,必然讓自己在符合天地之道規則的同時,自然獲取有益的力量,使得自己在生活與事業等人生的諸多方面越加平順。
反之,如果一個人內心存在的都是嗔心戾氣,私心妄念,那麼即便他能夠透過一些狡詐的手段獲得利益,那麼這樣錯誤的行徑,最後也需要讓他付出代價。
因為世間因果的道理是真實不虛的。
當一個人以仁德的狀態去生活時,他的這一份正向給他身邊的人,甚至給世間其他人所帶來的影響都是良好的,有幫助作用的。
而一個人生命的意義,本身就是在於他能給這個世界創造價值,不管作為一個家庭的角色,還是社會之中的角色,能擔負起自己的責任,對身邊的每一個人,每一件事情負責,那麼他的生命就是偉大的。
這就是我們要在自己內心下功夫,以正心正念正行修正自我,並且作用於人生的目的和意義。
作者|國學書舍
願將文章之功德,平等施一切;同發菩提心,生安樂歡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