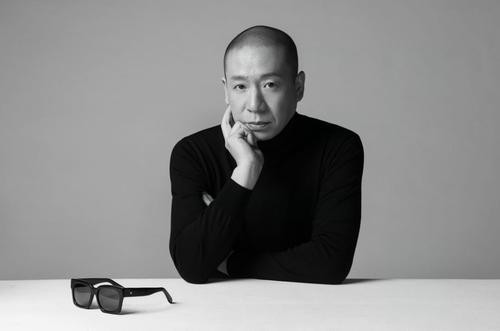20年前,名不見經傳的樑龍在舞臺上以一句:
“大哥你玩搖滾,玩他有啥用啊”炸開了落幕之下的京圈搖滾。
20年之後,樑龍又以“搖滾圈第一美妝博主”火遍全網。
綠色貂皮大衣,花色蕾絲旗袍裙,煙燻妝、紅嘴唇,這是樑龍“大鬧”54屆金馬獎時的雷人著裝。
而他這般“瘋癲”的行為在粉絲看來,卻是一種另類的藝術。
這也直接導致大眾對於樑龍的評價直接兩極分化:愛的愛死,恨得恨死。
你很難想象就是這樣一個人,卻是搖滾圈裡的頭號教母。
而為何自稱“搖滾教母”,樑龍說:
“因為搖滾界的教父太多了,我只好做搖滾界的教母。”
這個桀驁不馴,滿嘴大碴子味兒的男人,卻是繼“魔巖三傑”後京圈最另類樂隊“二手玫瑰”的主唱。
你很難在公開場合,找到第一個敢如此“興風作浪”的樂隊。
可是樑龍卻說:
“我就不覺得二手玫瑰俗,我覺得這就是藝術。”
可穿裙子、紅高跟、煙燻妝的二手玫瑰到底憑什麼能在搖滾圈獨樹一幟?
1.
1986年在北京工人體育館“世界和平年”首屆百名歌星演唱會上,崔健身穿清代長衫、身背吉他,褲管一高一低站在了舞臺之上。
上臺前的王迪什麼緊張地說:“太激動了,也不知道能否被人理解。”
而崔健那句:“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可你總是笑我,一無所有”一出口。
炸開了所有觀眾的心,那首改了又改《一無所有》拉上“中國搖滾”四個大字,即日啟程。
1986年的平凡一天,崔健帶著他的《一無所有》踏上征途,真正拉開了中國搖滾時代的帷幕。
那年,竇唯還在走穴,卻能日賺一百塊錢,唱流行歌、跳霹靂舞,與搖滾樂差著十萬八千里。
張楚則在陝西機械學院上學,離開了父母,與祖母生活在一起,在四處漂泊的日子裡獨自寫歌。
從小與崔健一同長大的何勇辭去了美術老師的工作,也玩兒起了音樂,還參加了一個名叫“五月天”的樂隊,但唱來唱去依舊沒什麼名氣。
那時,唐朝樂隊的“搖滾老炮兒”張炬輾轉三支樂隊當貝斯手,前途一片渺茫。
而8歲的樑龍還在豆腐坊旁邊看著一個農民美滋滋地聽《豬八戒拱地》的二人轉。
但出身於城市國企家庭的他,卻覺得那玩意兒丟份兒。
即便是家鄉的特色,樑龍卻沒怎麼聽過二人轉。
而他對於音樂的喜愛,來自比東北時尚的香港。
起初,他喜歡香港的歌星劉德華、張學友,但當搖滾席捲全國時,臺上的幾個生活在首都,留著長頭髮、目光犀利的歌手迅速俘獲了樑龍的心。
他騎著腳踏車,跑到音像店,買了一盒黑豹樂隊的磁帶,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他總覺得,搖滾歌手爺們、新潮,自己聽他們唱歌,就會變得與眾不同。
在讀職校的期間,樑龍認識了小三歲,卻同樣愛搖滾的孫保齊。
同樣是雙國企職工家庭,同樣面臨著按部就班的生活,兩人便成了知己。
那時樑龍與孫保齊共同的願望便是成為搖滾歌手。
那是搖滾界最為熱鬧的時候。
1994年,在香港紅磡演唱會上,舞臺之上站立的人來自於大陸搖滾界。
那一天,何勇穿著海魂衫繫著紅領巾站在臺上大喊:“香港的姑娘們,你們漂亮嗎?”
在香港紅磡演唱會之後,魔巖唱片徹底打響了自己的招牌,而“魔巖三傑”也迎來了自己的巔峰時刻。
而樑龍早已從職校畢業,在一家化妝品公司上班,每天蹬著三輪車,四處給人送貨。
同為好友的劉大剛常年混跡北京搖滾圈,總是繪聲繪色地向樑龍講述那個圈子裡五光十色的生活,還對他說:
“北京有一個學校叫迷笛音樂學校,專門培養搖滾樂手。”
這一句徹底點燃了樑龍的希望,但卻沒成想迷笛音樂學費要好幾萬。
他開始琢磨著做點野菜生意賺錢,但賠了個底掉。
走投無路之時,曾經的職校校長介紹給他一份工作,可樑龍去了才知道,是在一家賓館當保安。
為了生活,樑龍只能先棲息在哈爾濱的賓館裡,在這裡他認識了溫恆、馬春雨、馬金兵。
樑龍又叫來了老鄉孫保齊,五個人一起組建了“黑鏡頭樂隊”。
可是還沒等來樂隊發光發熱,就被長久以來的困頓衝散了。
孫保齊去了海南經商,溫恆、馬金兵、馬春雨去了內蒙走穴、而曾經混北京搖滾圈的劉大剛已經離開北京,再也沒人聽到過他的訊息。
而樑龍終於前往北京,追他的搖滾夢。
1995年,張炬車禍身亡,唐朝樂隊逐漸低迷。
而何勇調侃模範,闖下了大禍,從此被封殺。
想要在大陸締造搖滾神話的張培仁,卻因資金問題放棄了“魔巖三傑”,回到了臺北,開始做起了流行樂。
之後,想要拿到搖滾樂的批文,越發困難,那時的搖滾圈正如竇唯所唱的那般:“黑色夢中。”
可偏偏在這時,樑龍闖進了北京城,開始向著他的搖滾夢進發。
2.
在北京的樑龍,幾度想要將作品投給唱片公司,但是一提筆,卻發現自己什麼也寫不出來。
因為他已經在黑豹樂隊的影子裡“中d太深”,早已找不到自己的風格。
那時的樑龍已經22歲,父母下海經商後,賠了錢,將市區的房子搬到了郊區。
他覺得再掙不到錢,自己就沒臉見人了。
不僅他生活過的困苦,曾經的兄弟溫恆、馬金兵也過的不好。
三人重聚後,決定重新組攤,回到了哈爾濱的農村。
白天樑龍排練,或是在村裡紅白喜事上演奏歌曲,夜晚躺在農村的火炕上,聽著蟋蟀、青蛙的叫聲。
而他的內心也在悄悄變化。
還是平凡的一天,樑龍在院子裡排練,路過的一個小女孩隨口一說:“6、4、3”,幾人就開始隨意地扒拉著樂器,但沒過一會兒,幾人放下樂器,回屋看電視。
可是樑龍卻一直趴在院子裡,用了20分鐘,寫出了《採花》。
沒人知道在這20分鐘裡,樑龍心中想了什麼,或許是被神祗握住了手,又或是東北文化對他的耳濡目染。
總之在那一刻,樑龍找到了自己的語言,而曾經被他厭惡的二人轉在那一刻神奇的化用了。
這20分鐘成了樑龍的人生轉折點,他擺脫了二手的宿命,從黑豹的影子中走出,成了一手樑龍。
接下來,樑龍一口氣寫下二十幾首歌,錄製小樣、排練、錄音,只用了22天。
他們商量著給樂隊重新起一個名字。
而樑龍卻回憶起在北京的日子,那時所有人都在模仿曾經的京圈老炮,他將這種狀態形容成“二手”。
幾個被困在農村的年輕人對美好的嚮往,又被他稱為了“玫瑰”。
於是,1999年,這個風格迥異,只做一手的二手玫瑰樂隊誕生。
3.
同年年底,二手玫瑰收到了哈爾濱第二屆搖滾節的邀請。
演出那天,樑龍幾人穿得破破爛爛就去了現場,可沒人正眼看他們。
所有人都收到了節目組的肉包子,可二手玫瑰卻沒有。
這讓樑龍心裡窩了火,喝了一瓶白酒,對樂隊成員說:“我們今天一定要出彩。”
說完就拿起手邊的糖紙,編在了自己的頭髮上,又借來了化妝品,胡亂一塗,就這樣上臺了。
可這一上場,讓哈爾濱的搖滾老炮全都傻眼,誰都不知道二手玫瑰的風格如此與眾不同。
一首《採花》讓二手玫瑰在哈爾濱揚名。
但樑龍又一次孤注一擲前往北京。
因為那是夢開始的地方,不在北京成名,他怎麼都不死心。
但那是中國搖滾境況最差的時候,就連崔健都栽了跟頭,大批樂手都聚在遠郊地帶,吃掛麵幾乎沒演出。
而樑龍在北京的第一場演唱會,在豪運酒吧。
演出之前,樂隊找來了吹嗩吶的蘇永生,還給樑龍制定了反串形象:一個上海舞女。
為了一雙44碼的高跟鞋,樑龍跑遍了北京,而這次演出也基本塑造了他之後的形象:
二人轉與搖滾的混搭,大碴子味兒的歌詞,以及誇張妖嬈的反串扮相。
那一場演唱會只有100多人,但是二手玫瑰卻在北京傳開了。
就連樑龍曾經的偶像都來看他的演出,崔健認可他:“牛,音樂方向非常好。”
竇唯對他說:“哥們今晚不錯。”
之後的二手玫瑰又與唐朝樂隊的前經紀人黃燎原簽約。
在黃燎原的運作下,二手玫瑰出專輯,在只有崔健辦過演唱會的北展舉辦了演唱會。
那一年,樑龍幾乎拿到了當年所有與搖滾樂有關的獎項。
這讓樑龍有點暈頭轉向,那一刻有另一種聲音叫醒了他:玩世、低俗。
名氣也並沒有讓樑龍成為可以連住五星級酒店的巨星,反而收入平平。
而樑龍也說:“那個年代搖滾沒有市場,你有車沒有路。”
2004年開始,各種選秀節目開始在市面造勢,流行音樂依舊是主流。
隨著黑豹、唐朝淡出公眾視野,汪峰開始出面,發行了一張又一張雞湯專輯。
這時的樑龍不免有些心灰意冷,轉身將更多的精力投身搞藝術、做畫展上。
但吉他手姚瀾卻打電話給他:“你音樂不能扔,你當藝術家,我們怎麼辦?”
於是樑龍重拾音樂。
2013年,在黃燎原的操盤下,樑龍在北京體育館舉辦“搖滾無用”演唱會,被眾人評價為中國搖滾樂隊在商業上能達到的最高點。
可是隨著各種音樂類綜藝的出臺,再一次讓樑龍困惑了。
曾經樑龍也接到了不少音樂節目的邀請,但都被他以:不想被人評價,不想評價別人的理由一一拒絕。
而曾經的隊員迫於生活壓力退出,樂隊反反覆覆重組很多次。
為了生計,樑龍開始另闢蹊徑,2019年,曾經的搖滾教母搖身一變成了美妝博主。
這個四十多歲的男人開始在鏡頭前貼面膜,塗口紅,嘗試做下一個“口紅一哥。”
但是這也只是他的策略,樑龍依舊玩世不恭,二手玫瑰依舊是大眾口中的“不正經樂隊。”
人們都說:正經人誰聽二手玫瑰啊。
但正經的生活和快節奏,還是需要一些宣洩口。
而樑龍恰好就是那個願意為快樂買單的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