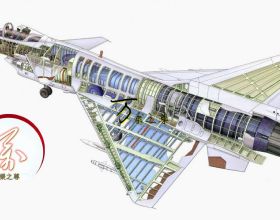研究聰明,不如研究愚蠢。避開愚蠢,就是聰明。
“蠢人固持己見,學者心存懷疑……哲人反覆思考。”
——亞里士多德以及……西科迪
我們能否科學地研究愚蠢之人?這是個很挑釁的問題。我們知道一些性質很蠢的研究(例如,放屁能在恐懼中起到防禦作用嗎?),還有一些針對無聊行業的很傻的研究,它們既沒有起到任何社會作用,也不能給研究者帶來個人滿足感。但如果我們“以人為本”,對蠢人本身進行研究分析,那又會是一種什麼情況呢?
事實上,在我們瀏覽心理學文獻時不難發現,整體而言,“蠢”這個概念早已被透徹地詮釋過了。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能得出如下結論:沒錯,我們確實能分析出什麼樣的人是蠢人,從各種不同的調研中選取一些變數引數,就能描繪出蠢人的類別和形象,進而我們的頭腦中也會由此映射出相對具象的概念(討人嫌的人、有點兒糊塗的人、情商或智商有限的人)。還會衍生出形形色色的愚蠢型別,比如自負粗魯、不可救藥的自戀以及沒有同理心等附加特質。
愚蠢和缺乏專注
與其把蠢人作為一個物件來研究,不如用心理學來詮釋:為什麼一些人的行為有時候像個傻子似的?
《指令碼、計劃、目標以及理解:人類知識結構調查》一書指出:大部分時間,人們在行動前都沒有充分了解身邊的環境,而總是墨守成規地做出習慣性舉動,在自身和環境的引數下自動進行條件反射,產生行為。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常常會注意到,當你哭泣時,總有個傻子過來問你:“你還好嗎?沒事兒吧?”此外,剛剛看過手錶,馬上再看一遍,也是很蠢的行為。
我們想知道時間,就必須看手錶,這是個機械化的行為。這個反射機制不需要我們花費太多的專注力,便能完成這項任務。然而正因為不需要花費過多的注意力,我們就會一邊想著其他的事兒,一邊忘了把手錶上的時間資訊輸入大腦,從而導致我們必須再看一遍手錶。這很傻,不是嗎?
在關於專注能力的研究中,心理學家指出,人們常常受制於對各種變化的失察,個人往往會忽視環境中某個重要因素的改變。大家可能聽說過:某人節食減肥成功,瘦身10千克後,總能遇到一個傢伙對此完全沒有察覺……我們也不難理解,人們在著急的時候,會像瘋子似的猛按電梯按鈕很多次。同樣的蠢事也會對社會環境產生影響。為什麼一個司機把車開入一條禁止通行的道路後,後面會有車跟隨?甚至有人在電視遊戲中被問到“圍繞地球旋轉的是太陽還是月亮”時,竟然會求助大眾的意見。
人們似乎經常會偏離絕對理性以及預期的價值。人的行為距離調研得出的預期中間值越遠,偏離指數越大,就顯得越蠢。總體來說,這種人看待世界的視角過於簡單,他們無法消化大量資料、平方根、複雜圖形,甚至看不懂高斯曲線,他們看到的僅僅是極端值。相較於透過精密統計所得出的科學報告,人們本能地對富有傳奇色彩的軼事更敏感一些。愚蠢之人就更迷戀那些天花亂墜的傳奇軼事了。有人甚至號稱認識一個從40樓墜落卻沒有喪生的人,還把這件事告訴了法國TFl電視臺的採訪部門。
愚蠢和信念
目前對於“信念”的研究,都是基於“公平世界信念”這一心理學概念之上的,它在全球廣為流傳。而蠢人也透過大肆宣傳信念的表現,比如“她確實是被非禮了,但你不看看她當時穿成什麼樣了嗎”,完美地證明了這一理論。圍觀者越愚蠢,受害者就越百口莫辯,從而也就越發顯得似乎應該自食其果……
蠢人有相信一切的“卓越”才能,他們幾乎什麼都能信。2017年5月28日,在法國A4高速公路上,行駛數公里的無人駕駛“鬼魅”摩托車被人拍攝下來。其實那隻不過是駕駛員在此之前不慎墜車罷了,但最蠢的一群人卻認為,這一幕是神幻的“白衣夫人”造成的。稍微還有點頭腦的蠢人則會說,這個畫面出自陀螺效應……對各種神秘力量的迷信,似乎都能和獲得諾貝爾獎的過硬實力形成南轅北轍的反向關聯。
我們繼續說信念。研究表明,因為負面記憶會隨著時間漸漸消逝,只有正面記憶會一直保留下來……所以,人越老,就越會覺得過去很美好,因此活在過去的老人會說:“以前可好了……”
人類不理性的方方面面在無數研究中得到過全方位的審視和解讀,這是出於人類企圖掌控環境的內心需求。其實,所有生物都有這種需求,只是程度不同。例如,門口有人敲門,狗會衝到門口,但這個行為並不是為了它自己。而人類甚至會因此做出荒謬的行為,例如,去諮詢占卜師。法國有10萬人自稱占卜師,他們每年的總營業額高達30億歐元(約合人民幣224億元)。儘管研究者並沒有發現這些占卜師身上有任何貨真價實的天賦,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發財致富。約有20%的女人、10%的男人,一輩子至少尋求過一次占卜。總體來說,占卜師們坦然地用詐騙術謀生,最終蠢人蠢事就成了這門生意的搖錢樹……
控制慾常會導致掌控的錯覺,蠢人的錯覺則會更勝一籌。人們作為乘客坐車時,會比作為司機駕車時更害怕車禍發生。生活中就有那麼一些人,在當乘客的時候會緊張得無法入睡,但在自己開車的時候,卻會不停地打瞌睡。
蠢人擲骰子很用力,覺得這樣才能擲出六;他們買彩票的時候愛選自己的幸運數字;他們喜歡踩在狗屎上,卻不喜歡走在梯子邊上(在法國,踩到狗屎代表好運,從梯子下經過代表厄運)。倘若他們的彩票中了獎,他們會解釋說自己連續6個晚上都夢見了6這個數字,好像6乘以6等於42似的,所以就買了42,果然中獎了。如此看來,我們可以相信,蠢人的精神狀態都很健康,因為腦回路複雜、容易抑鬱的人,就不怎麼相信這套幻象。
對那些自以為是的蠢人的研究
另一個深入的研究表明,蠢人更傾向於運用一套保衛自尊的戰略。關於“虛假同感偏差”的調查顯示,蠢人更有法不責眾的心理,會誇張地認為很多人和自己犯同一個錯誤。我們會注意到蠢人常常忽視停車標誌,還強調說“這裡沒人會真的停下來”。
蠢人還很愛使用“馬後炮”來標榜自己。孩子生完了,他們會說“我就知道懷的是個男孩兒”;看電視的時候他們會聲稱“我早就知道馬克龍會擔任總統”,甚至還經常會說“我就知道你會這樣說”。
這麼說來,蠢人很壞嗎?他們是魔鬼嗎?也不是。他們所謂的“我早就知道”,只是表達自己先知先覺、無所不知的戰略手段罷了。當然,我們不需要跟蠢人講大道理,因為他們根本不會認同。
為了保護自尊,蠢人總會高估自己的實際能力。這種偏執在諸多心理學實驗中得到了驗證。大部分研究參與者都認為自己的水平高於平均值,比如在智商方面。在愚蠢的種類中,還存在“笨鳥”型以及被指責缺乏自信的人。從先天的心理來說,這些人集聚了思想簡單、樸素卑微、平庸無奇這些特性,成了愚蠢的深化版。笨鳥往往會被其他蠢人利用。與此相反,我們還發現,一些取得了些許成就的人表現出了過度的自信。在現實社會中,這類蠢人會付出慘痛的代價。不管是上山還是下海,都有這樣一群自不量力的人,比如在雪道外滑雪,又比如高估自己超速駕車的能力,並對此津津樂道。
以自我為中心的偏執,讓蠢人對自己做的蠢事熟視無睹,更無法認識到自己做出蠢事的根源。一個蠢人離婚3次,就認為自己遇到了3個不同的蠢貨;自己行事失敗,卻歸咎於自己和一群沒有魄力的人共事;作為成年人,他們會堅持認為並不是自己的腳臭,而是襪子散發出一股異味;某日開車超速被攔截下來,他們會覺得自己的運氣實在太差了;他們無法理解,所謂的運氣,只是蠢人蠢事得到寬容的僥倖機率罷了。
美國康奈爾大學的社會心理學家鄧寧和克魯格當年無法發表《對那些自以為是的蠢人的研究》一文,因為這樣的文章無法被一本科學雜誌的評委會透過。然而,這個研究的結論其實非常精闢。這兩位專家發現,缺乏能力的人總會高估自己的能力,一個從來沒有養過狗的蠢人,會跟你解釋怎麼教育你的狗……鄧寧和克魯格把這種認知偏見歸結於自我評估的缺失。在某些情況下,這其實是對自己實際能力的認知不足。另外,根據心理學家的意見,一個能力有限的人會高估自己的才能,但同時也會無視自己本身擁有的其他能力。
透過這項研究成果,我們可以理解下列事件的箇中緣由:一個愚蠢的客戶,卻在指導專業人士該怎麼進行某項工作;當你丟了某樣東西時,總會有一個傻瓜對你說:“想一想,你最後一次看到它是在什麼地方。”此外,我們也能理解為什麼蠢人會發表“對律師而言法律很簡單,他們早就該背出來了”“戒菸?意志堅定就好”“開飛機?和開車沒啥區別”之類的言論。依此類推,蠢人在量子物理學研討會結束時,會注視著專家的眼睛說:“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鄧寧和克魯格甚至認為,當我們對經濟學、地緣政治、制度機構沒有任何瞭解,對電子程式以及“如何讓國家發展得更好”這些議題毫無概念的時候,應該保持謙遜的心態,不要胡亂發表太多的言論。然而,蠢人卻會在小酒館裡高談闊論:“我知道怎麼讓法國走出危機!”
不過,不少針對亞洲人的研究卻揭示了與鄧寧和克魯格所述相反的現象:亞洲人有低估自己能力的特質。在遠東文化裡,大家並不會急於抬高和突出自己,也沒有表現出對一切瞭如指掌的自信姿態……
愚蠢雷達
儘管有很多方式定義愚蠢,在這篇文章裡,我們會來說一下蠢人比其他人存在更多的“犬儒主義懷疑”。所謂犬儒主義,是關於人性和慾望消極態度的總和。蠢人往往是社會政治犬儒主義的受害者,他們生活在眾多的質疑中。一些沒有動詞的語句每天都在他們的思考中盤旋,比如,“腐敗的一切”“心理學者?騙子”“記者?馬屁精”。他們覺得讓一個人正直的唯一理由,是不被抓住把柄。蠢人生活在一個低能和爾虞我詐的世界裡。研究表明,抱有犬儒主義思想的蠢人絲毫不懂得合作,對一切都表示懷疑,以至於讓自己痛失職場上的良機,隨後猛然發現,自己的收入比別人低。
不同的心理學研究者都曾揭示過蠢人形形色色心理傾向的誇張表現。如果有人兼具各種誇張表現於一身,那簡直就是蠢人之王,蠢到登峰造極。
不過,我們還有一個本質性的蠢問題沒有回答:“我們能不能研究蠢人?”或者換句話說,“為什麼有這麼多蠢人呢?”確實,蠢人遍地橫行,不少科學文獻再一次給我們提供了答案。
首先,人其實是自帶“蠢人雷達”的。我們把這種特性稱為“負性偏向”,即相對於積極美好的事物來說,人們對不夠美好的事物總會有更強烈的關注和興趣。負性偏向的深度,引導了人類的意見,最終導致刻板、偏見、歧視和迷信。舉個例子,關於施工工程,對於那些尚未完工的專案,我們一眼就能看出,但對於那些完工的專案,我們卻熟視無睹……在複雜的社會環境中,正因為這種負性偏向,會讓人們覺察出一個蠢人比發現一個天才更容易。另外,這種偏執讓我們更傾向於探究負面事件的背後原因。如果我們在房間裡找東西,我們不會想“是我把它弄丟了”,而是“一定是別人把它放在了錯誤的地方”,滿腦子都是“誰動了我的東西?”。一件事情沒有達成,我們會想背後一定有人圖謀不軌,而不是自己把它搞砸了。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研究者還提出了一個“基本歸因錯誤”的概念,即觀察一個人,相比外因(情景性因素),我們更容易將其行為歸結到此人的本質(傾向性因素)上。在很多情況下,我們會得出一個簡單明瞭的結論:這是一個笨蛋。舉些例子:一輛汽車從我們身邊呼嘯而過,那一定是因為司機昏了頭,而不是他的孩子在學校裡受傷了;朋友兩小時內不回覆我的郵件,一定是他和我產生了矛盾,心存芥蒂,而不是他的網路出問題了;同事不交材料,那是因為此人很懶,而不是他的工作超負荷;教授回答我的問題態度很冷淡,那是因為他蠢,而不是我的問題蠢。這套看問題的機制,會讓我們發現我們周圍到處是數不清的蠢人。總之,負性偏向和基本歸因錯誤這兩個因素,是我們對蠢人如此敏感的兩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