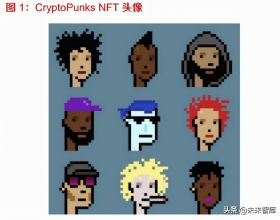光緒六年七月初七,清廷發出諭旨,以急需“老於兵事之大臣以備朝廷之顧問”為由,調遠在新疆哈密的左宗棠回京陛見。
清廷之所以在這個時候召左宗棠回京,有內外兩因。對外,清廷沒有對沙俄一戰決雌雄的魄力,主和派擔心左宗棠這隻雄鷹強硬過頭,擅自進擊沙俄,因此決定釜底抽薪,為議和鋪路;在內,朝中清流認為時局艱危,急需左宗棠這樣的重臣入贊樞密,主持大局,為此清流中堅御史鄧承修上折說:“觀今之大臣志慮忠純、暢曉戎機、善謀能斷者,無如督臣左宗棠”,若“委以軍國之大柄,使之內修政事,外攬兵權”,可望“拯今日之急,守宗廟社稷”。
接到這樣的諭旨,左宗棠難免有些壯志未酬,但上命難違,只得從命。
面對新疆這一片大好河山,返京之前,左宗棠拿出赤膽忠心,先是致書總理衙門,要求朝廷在和戰之間做出決斷,即便主和亦不可示弱以取侮。接著,他又召來西北事務及新疆軍務的後繼者劉錦棠,親手將欽差大臣的關防交了出去。
想當年,左宗棠為了西北大業,兵分三路,抬棺出征,轉眼十幾載春秋過去了,到了真要離開的這一天,老邁的左宗棠深深地知道,此去註定是一去不復返了。
他的內心有難捨之情。
西北的百姓更是如此。
《左宗棠年譜》有這樣的記載:在西北的每一個城鎮,甚至是在最偏遠的村莊,在那些日子裡,左宗棠的離去都成了人們談論的唯一話題。所有人都為他的離開而感到不安,因為只有他在這裡,人們才會覺得日子是安全可靠的。
到了左宗棠離開蘭州的那一天,所有的商鋪都歇業了,這個讓他們學會去信任、去畏懼、去尊敬的人,贏得了全城百姓的尊重和送別。百姓自發地排成一百多里的長隊,當他經過時,每個人都跪在地上,向他虔誠地磕頭。
這一幕,讓左宗棠老淚縱橫······
對於這樣的離開,左宗棠其實是早有預料的,對於離開後的歸宿,他也是有所安排的。就在這一年的六月,左宗棠曾給京城的好友徐用儀寫過一封信,信中談到了他離開西北後的具體打算——
“竊念時事多艱,義當養痾京寓,不可以乞身歸裡為自便之謀,陛見後,再肯開閣缺,以閒散長留京師,於心稍安耳。留京不可無住宅,已致函吉田廉訪、雩軒方伯於廉項下劃二千兩匯寄尊處,乞代買住宅一所。擬到京後,再飭兒孫攜眷北來,一便侍養,一便就近課讀應試也。能如京官住宅款段,即可相安,唯宅旁須有隙地可以畦蔬,庶有生趣,幸留意焉。”
左宗棠說,來京後,他多半是不能告老還鄉,回湖南安度晚年的,那就只能在京城買一處宅子養老了。有了這樣一處宅子,他可以將家人全部接來,一同生活,兒孫們也可以就近課讀應試。至於房子的地段、規模,無須按照一品大員的標準,只要和普通京官住得差不多就行了,唯一特殊的要求就是宅子最好能帶一塊空地,好拿來種菜。
為此,左宗棠給徐用儀匯去了兩千兩銀子,用來在京城買房。
然而,左宗棠並不瞭解京城當時的地產行情,區區兩千兩銀子在紫禁城附近根本買不到像樣的宅子。左宗棠得知這個情況後,由於再拿不出多餘的銀兩,最後只好打消在京城買房的念頭,當起了晚清的“北漂”。
堂堂社稷功臣、封疆大吏,怎會困頓到如此地步呢?
這跟左宗棠的操守有關。
左宗棠為官不像李鴻章,他非但不貪,從不中飽私囊,相反常年將俸祿拿出來補貼軍用、捐助好友,離開西北時,他曾跟掌管西師軍餉事宜的西安軍需局道員沈應奎仔細算過一本賬:他所有的積蓄只有三萬兩銀子,胡雪巖採買水雷、魚雷的款項、捐助蘭山書院的一千數百兩膏火銀、吳柳堂千餘兩贍家銀都要從這三萬兩中出,此外,湖南老家還有數千兩的欠債要還,北行盤川也需要兩三千兩,剩下的只能勉強應付留京用度,到時候可能連輿夫一項都得砍去。
光緒七年正月二十六日,經過兩個多月的長途跋涉,左宗棠終於抵達了京城。恰在這一天,歷時半年的中俄改約談判也落下了帷幕。雖說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透過改訂的《中俄伊犁條約》為國家爭回了一些權益,但論及實質,改訂的條約仍然是一個割地、賠款的不平等條約。
凱旋班師,卻在京城買不起房。
西北奮戰十三載,到頭來還是屈辱求和。
左宗棠抵京之日,內心的憂憤可想而知。
這些還僅僅是一個開始。
按理說,創下如此不世之功,左宗棠凱旋抵京時,朝廷應該給他相當的榮耀,相當的禮遇。可現實卻是另一番冷漠、腐化、墮落的景象。
當左宗棠抵達崇文門時,居然遭到了守門太監的阻攔。
守門太監告訴左宗棠,按照朝廷慣例,所有任期結束奉召回京的封疆大吏,都要在崇文門交納一筆銀子。
左宗棠問,你要我交多少?
守門太監說,四萬兩。
聽到這個說法,左宗棠火冒三丈,他耿直地質問守門太監,我是奉召入京覲見皇上,要我交錢是何道理?如果非要這筆銀子,也該由當今皇上出。
守門太監冷漠地笑笑,隨即跟左宗棠打起了冷戰。
據說,在崇文門外,左宗棠被守門太監擋了五天,最後還是恭親王奕訢暗自掏了八千兩進門銀子,這場風波才得以平息下去,左宗棠才得以透過崇文門,進入京城。
此事,表面上看是守門太監借慈禧權威為非作歹,實際上,這是朝中的某一種勢力以這種方式給左宗棠下馬威。
左宗棠是何等聰明之人,此中名堂他自然是明白的。
因此,進城之時,他頗為鬱悶地對身邊人說了一句,凱旋遭嫉,京城難為!
進城之後,第二天,東宮慈安太后召見了左宗棠,西太后慈禧因為生病,缺席了這次召對。
史書上記載,見到被西北風沙吹了十三年的左宗棠,慈安太后表現出了極為深切的關懷,左宗棠為此內心波瀾,最後竟失去鎮定,淚水奪眶而出。
那一刻,慈安太后是理解左宗棠的,自征戰以來,這位鐵血硬漢承受了太多的非議、責難、艱險、不易,他太需要關懷,太需要理解,太需要寬慰了。
但慈安沒有將這些表露出來,她只是柔聲地問了一句,你的眼睛不好嗎?
左宗棠說,是的,老臣的眼睛不好,一路上風沙又加以刺激,因而不禁流淚。
慈安聽罷,叫太監將咸豐皇帝戴過的一副墨鏡取來,賞賜給了左宗棠。
因為這一副墨鏡,左宗棠對慈安太后感念很深,但在無形之中,他也因此得罪了真正掌權的慈禧太后。
這次召對結束後,過了兩天,朝廷正式任命左宗棠為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並管理兵部事務,直接參與中樞決策。
左宗棠入職軍機,本是想有所作為的,然而,宮廷政治的險惡以及當權派對他的排擠還是大大出乎了他的預料。
就在左宗棠首次被召見後沒過幾天,宮中突然傳出噩耗,皇太后駕崩了。那一時期,慈禧因為病重,所以一開始眾人皆以為駕崩的是慈禧,等到確切訊息傳出,說是慈安駕崩了,眾人無不驚訝無比。
左宗棠得知這個訊息,與眾人的沉默表現不同,據史書記載,當場他就高嚷了起來,今天早上我還見到慈安太后上朝,說話和平日無二,清朗有力。太后這樣突然駕崩肯定有問題!
嚷完,左宗棠開始在院中怒氣衝衝地來回走動,彷彿一頭雄獅在抗議。恭親王見事態不妙,趕緊來拉,費了許多工夫,最終才讓左宗棠平靜下來。
此事很快傳到了慈禧的耳朵裡。
對於左宗棠,慈禧本是欣賞力挺的,但有了這一次當眾的質問,慈禧便不得不重新審視了,此人雄才大略不假,但如此直言不諱,狂妄不可控,留他在中樞,恐怕只會增添矛盾、麻煩,不能為自己真正分憂。
簡而言之,此人是國家的雄鷹,斷無可能是慈禧的私人鷹犬。
慈禧乃當朝實際的主宰,當左宗棠進了中樞,她尚且有如此警惕的看法,至於那些朝中的當權派,自然更是如此了。
事實上,當左宗棠進京時,正是李鴻章如日中天、權勢無兩的時候。想當初,這位權臣曾發起一場聲勢浩大的海防與塞防之爭,並斷言朝廷出兵西北,將不可能取勝,識時務當放棄新疆。
那一時期,李鴻章不僅向塞防大潑冷水,而且在左宗棠率軍出征後,竭盡掣肘之能事。但即便如此,李鴻章也沒有坐等來左宗棠的一敗塗地,相反左宗棠讓他看到了新疆是怎麼勝利收復的。
如今,左宗棠雄姿歸來,李鴻章之流當然知道,如果不能壓制左宗棠向上的勢頭,接下來迎接他們的就不僅僅是顏面掃地的尷尬了。
搞內鬥,李鴻章之流有很深的道行,為了壓制左宗棠,他們抓住其性格孤高的“缺點”,很腹黑地玩了一手肆意醜化的把戲。
不妨來看看李鴻章心腹薛福成是怎樣醜化左宗棠的?
薛福成對外說——
左宗棠入閣時,驕矜之氣,不可向邇。適有折交閣員會議,左每閱一行,則自陳其平回疆之功績,餘則力詆文正(曾國藩)不止。如是者數月,而閱未及半,同列者皆厭之,為藏去其折。
在當時,諸如此類的醜化之辭,一經傳播開來,李鴻章之流即有了侮弄攻擊的理由,左宗棠身處如此困厄之境,不說有所作為,就是在軍機處立足也是愈發地困難。
無奈,在隨後的幾個月裡,左宗棠只好做去修治直隸河道之類的芝麻實事,但即便如此,光緒七年九月初六,朝廷還是將他驅出中樞,外放到了兩江。
慈禧御下不遜於清朝任何一帝,將左宗棠外放到兩江總督兼辦理南洋通商事務大臣任上時,慈禧先是冠冕堂皇地說:“若論公事繁難,兩江豈不數倍於此,以爾向來辦事認真,威望素著,不得不任此重寄。”言下之意,此番你去兩江,並非是受到了排擠,也非我要驅趕你,而是兩江重地非你這樣的老臣坐鎮操持不可。
講完這些,慈禧又說,你這些年也不容易,手頭也沒有積蓄,兩江乃富庶之地,你去那裡,可以過兩天好日子。
最後這一句送行的話,慈禧說得很直白,你的功勞我是知道的,到了兩江,你儘可以搞些錢,過幾天好日子,朝廷是不會干涉的。
聽到慈禧這麼說,左宗棠無法多言,亦無法抱怨,最終只能苦笑而去。
古往今來都是這樣,歷經滄桑,心境愁苦的人往往會思念故鄉。這一次外放兩江,左宗棠即是如此。光緒七年十月十四日,左宗棠離京南下,但他沒有立即赴任,而是向朝廷請假,回湖南老家省了一次墓。
在湘陰老家,左宗棠住了七天,之後前往金陵,就任兩江總督。
此次外放兩江,左宗棠以為沒了朝中掣肘,自己可以放手做一些事了,可是到了金陵之地他才發現,李鴻章早已上上下下做了佈置,“倒左”勢力根本不容他再顯威望。
比起此前的輿論醜化,群起而攻之,這一回“倒左”,李鴻章將落腳點放在了打擊、壓制左宗棠僚屬、故交上,意在剪除左宗棠羽翼,造成其大勢已去的局面。
首當其衝,遭受滅頂之災的便是左宗棠最有力的一條臂膀,晚清紅頂商人胡雪巖。當年,胡雪巖為左宗棠新疆用兵籌借款項時,與匯豐洋行有約定,在海關不能按時支付新疆之役借款本息的情況下,胡雪巖的阜康錢莊作為擔保,必須代為墊付。李鴻章心腹盛宣懷透過掌控的電報系統探知胡雪巖的巨量資金積壓在蠶絲上後,李鴻章隨即授意上海道邵友濂,壓下八十萬兩本應轉交胡雪巖的款銀。此時的胡雪巖,雖然頭寸緊張,但為了遵守合約,最後還是使出全力從全國各地的阜康錢莊調集了八十萬兩現銀,先行交給了洋人。李鴻章得到這個訊息,立即透過大戶發動了針對阜康的擠兌狂潮。可憐那胡雪巖,昔日富甲天下的商業帝國一夜之間土崩瓦解,本人也含恨而亡。
在當時,除了胡雪巖成了李鴻章“倒左”的犧牲品,還有許多左宗棠的老部下也都跟著倒了黴。
周崇傅,追隨左宗棠在西北擔任鎮迪道道員時,因為作風簡樸、清廉,一日三餐通常只有炊餅、涼水,當地百姓都叫他“炊餅道員”。左宗棠就任兩江總督後,專門調周崇傅來整頓兩江鹽務。周崇傅上任後,革除各種弊政,打擊貪官汙吏,一年就上繳鹽稅二百多萬兩。但就是這樣一個在肥差上不撈錢,只知勵精圖治的清廉能吏,最後卻被李鴻章的人排擠到難以容身,不得不離職回家的地步。
王嘉敏,曾任浙江糧臺、閩浙糧臺、湖北陝甘後路糧臺,是左宗棠非常信任的人,論操守、才幹,更是當時官場中難得的人物。但左宗棠在兩江總督任上,兩次推薦他擔任道員,論官銜,王嘉敏是布政使銜,已屬於高階低用,結果都遭到了吏部駁回。左宗棠氣憤不過,一再力爭,清廷這才勉強同意王嘉敏署理該職,但強調了一點,此種情況下不為例。
臺灣道劉璈,是左宗棠的老部下,後來竟被羅織罪名,和他的兒子一道,發配到寧古塔,最終被迫害致死。
李鴻章暗自操控的這些打壓之舉,對左宗棠造成的影響是相當惡劣的。對於晚清三傑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無論是當時還是後世,大家都有一個評判標準,那就是他們手下出了多少督撫、多少提鎮。在這個方面,曾國藩門生遍天下,李鴻章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唯獨左宗棠孤零零的一個,為此大家都說左宗棠性格蠻霸,不容僚屬,一輩子只知自己為官,不願栽培提拔屬下。其實,這是官場“倒左”形成的錯覺,不是左宗棠不惜才不愛才,而是他不屑經營官場,不願陷入黑暗齷齪的官場纏鬥罷了。如果換個角度,一句話就能還左宗棠一個公道,左公身邊的確未出多少封疆大吏,但他帶領不知名的手下所創造的歷史功績並不比曾李二人差,這筆帳該怎麼算呢?
因為在兩江的官場處境依舊十分艱難,左宗棠在任期間,大事還是難為,但左宗棠有騾子的倔強性格與實幹精神,據《左宗棠全集》記載,“蒞事以來,以治水、行鹽為功課,而精神所注則在海防。”
在晚清的廟堂之上,論脊樑之硬,論眼光之宏,論胸懷之廣,左宗棠當屬第一人。昔日,他是塞防的倡導者,但這並沒有妨礙他真切地關注海防,他對權爭不感興趣,此一時彼一時,他始終服從的是國家的國防戰略需要。
左宗棠任職兩江兼顧南洋期間,因法國殖民者的侵入,西南邊陲的局勢日趨緊張,南洋各港口也處在危險之中,那時候,左宗棠的身體已經很糟糕了,左眼已經完全失明,右眼流汁不止,但即便如此,他還是不斷地巡視長江各港口、炮臺,努力佈置防務。
在長江門戶白茅沙口,左宗棠曾對將士們說:“能破彼船堅炮利詭謀,老命固無足惜,或者四十餘年之惡氣藉此一吐。自此兇威頓挫,不敢動輒挾制要求,乃所願也。”
同行的兵部尚書,受命巡閱長江水師的彭玉麟,聽到這一番話,大受感動,當場亦表示:“如此斷送老命,亦可值得。”
光緒九年四月十三日,劉永福率領黑旗軍在河內附近的紙橋大戰法國殖民者,陣斬法軍統領李威利,西南邊陲的局勢陡然吃緊。
眼見局勢緊急,清廷隨即發出諭旨,命請假回籍葬母的李鴻章迅速前往廣東“督辦越南事宜”,並節制廣東、廣西、雲南三省防軍。但李鴻章因為心存求和之念,竟公然拒絕趕赴前敵。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左宗棠立即表示要親率大軍“一往國之,為西南數十百年之計,以盡南洋大臣之職”,甚至說“衰朽餘生,以孤注了結,亦所願也。”
說下這一番豪言壯語後,左宗棠隨即命令部將王德榜回湖南招募士兵,組成恪靖定邊軍,開赴越南。
可惜,因為清廷缺乏力戰的決心,地方將領又多是貪生怕死之輩,在越南戰場,黑旗軍和恪靖定邊軍雖然奮勇抗敵,但終究是缺乏有效支援且兵力有限的孤軍。
聽聞戰局急劇惡化,左宗棠眼疾更重,整個人病倒了。朝中主和派為消除左宗棠主戰之聲,趁機批假四個月,由曾國藩的九弟曾國荃署理兩江總督。
歷史充滿了戲劇性。
就在左宗棠正式向曾國荃交卸篆務的當天,慈禧太后在京城突然發動”政變“,恭親王奕訢下課,醇親王奕譞上位,主持朝中大局,此一政變史稱”甲申易樞“。
醇親王奕譞,表面上是主戰派,但實際上,主戰只是他暗鬥恭親王的一種手段。上位之後,他立即祭出了左右逢源的兩手,一方面,他授意李鴻章繼續與法國殖民者媾和,另一方面,他將左宗棠再次調入京城。
調左宗棠再次入京,表面上是主戰派在朝中抬了頭,實際上,這又是釜底抽薪。左宗棠一走,恪靖定邊軍頓失兩江支援,處境更加艱難。
無奈,左宗棠在北上之時,緊急安排當時正在湖南的舊部、原浙江提督黃少春在原籍招募五營士兵,開赴廣西,增援王德榜。
光緒十年五月二十日,左宗棠抵達北京,清廷命令:”左宗棠著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並稱:”該大學士卓著勳績,年逾七旬,著加恩毋庸常川入職。遇有緊要事件,預備諮詢,並著管理神機營事務。“
重入軍機,左宗棠仍是一貫的做派,孤傲強硬,霸氣側漏,其間,他屢次上書,高聲疾呼,”中國不能永遠屈服於洋人,與其賠款,不如拿賠款作戰費“。
當時,朝中當權者對左宗棠的看法比較矛盾,一方面,當局勢惡化到一定程度時,朝廷需要左宗棠這樣的主戰派來增添信心;另一方面,主和是朝中的主要暗流,因此當權者又擔心左宗棠成為局勢惡化的推動者。
這兩種心理纏繞到一起,呈現出來的結果就相當的微妙了。
據沈傳經、劉泱泱合著的《左宗棠傳論》披露,再次入職軍機後,短短兩個來月,左宗棠受到的申飭、處分竟達到了三次之多。
第一次就是左宗棠調動黃少春。朝廷先是申飭左宗棠舉措不當,接著就令其交回印封,並剝奪了他對舊部黃少春軍的排程指揮權,實際上就是將他與越南戰場隔離了。
第二次所瀰漫出的政治味道很陰沉。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回國之後遭到壓制,左宗棠看不慣,於是站出來為曾紀澤說話,要求朝廷重用曾氏幹才,結果,朝廷不僅駁回了左宗棠的推薦,而且毫不客氣地進行了申飭。
第三次最為惡劣,足可見左宗棠在中樞難以立足的艱難處境。光緒帝壽誕,朝廷大員鹹往乾清宮叩賀,左宗棠因老病行動不便,未往參拜。朝中傾軋者抓住這個”可笑“的把柄,群起而攻之,先給左宗棠扣上了大不敬的帽子,跟著又對左宗棠生平進行了大肆貶低。此事激起了許多人的憤怒,但清廷最終還是將此事“交部議處”。次日,部議結果就出爐了,罰左宗棠俸祿一年。
然而,在左宗棠屢遭申飭的時候,西南局勢的發展卻一再證明了左宗棠的戰略判斷,洋人貪婪狡詐,唯有一戰,才是征途。
據說,隨著法國殖民者進犯馬尾,左宗棠在朝堂上再次鏗鏘有力地喊出那句著名的豪言:“中國不能永遠屈服於洋人,與其賠款,不如拿賠款作戰費”,慈禧聽罷,最終含淚同意了左宗棠的意見,並於光緒十年七月初六,正式對法宣戰。
鑑於福建在中法戰爭中的形勢,福建水師和福建船政遭到重創,光緒十年七月十八日,清廷釋出上諭:“大學士左宗棠,著授為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福州將軍穆圖善、漕運總督楊昌浚,均著幫辦軍務。”
此時的左宗棠已經是七十三歲高齡的老人了,但其威風不減當年。有目擊者回憶:“當其入城時,凜凜威風,前面但見旗幟飄揚,上大書‘恪靖侯左’,中間則隊伍排列兩行,個個肩荷洋槍,步伐整齊。”
然而,晚清的朝廷終究是沒有骨氣,也沒有氣力的,慈禧、醇親王將左宗棠派往福建,歸根結底只是想利用左宗棠的威信,安定福建地方民心,戰與和的實際運作大權,則還是握在李鴻章這一派的手裡。
在福建,見到昔日自己苦心經營的福州船政已毀於一旦,見到戰局的糜爛,七十三歲的左宗棠內心很痛苦,卻又無能為力。
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時光裡,他用盡全力寫下了一批奏摺,內容盡是關於船政、海防的。
光緒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左宗棠在福州行轅含恨病逝,逝去之前,他給清廷給後世留下了一份耐人尋味的遺折——
”伏念臣以一介書生,蒙文宗顯皇帝特達之知,屢奉三朝,累承重寄,內參樞密,外總師幹,雖馬革裹屍,亦復何恨!而越事和戰,中國強弱一大關鍵也。臣督師南下,迄未大伸撻伐,張我國威,懷恨生平,不能瞑目!渥蒙皇太后、皇上恩禮之隆,叩辭闕廷,甫及一載,竟無由再覲天顏,犬馬之報,猶待來生。禽烏之鳴,哀則將死!
方今西域初安,東洋思逞,歐洲各國,環視眈眈。若不併力補牢,先期求艾,再有釁隙,愈弱愈甚,振奮愈難,求之今日而不可得!伏願皇太后、皇上於諸臣中海軍之議,速賜乾斷。凡鐵路、礦務、船炮各政,及早舉行,以策富強之效。
然居心為萬事之本,尤願皇上益勤典學,無怠萬機,日近正人,廣納讜論。移不急之費,以充軍食;節有用之財,以濟時艱。上下一心,實事求是。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據說,左宗棠病逝那天,福州下起了暴雨,一聲霹雷響起後,東南角城牆頓時撕裂一個幾丈寬的大口子,而城下的百姓卻安然無恙,無一人喪命。目睹此景,當地百姓皆悲痛感嘆,此乃天意,毀我長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