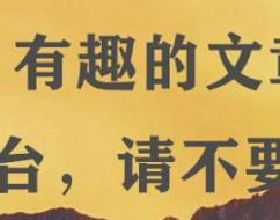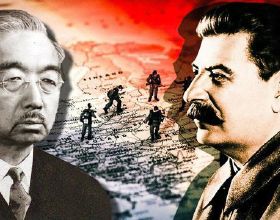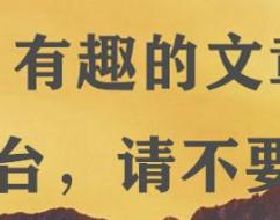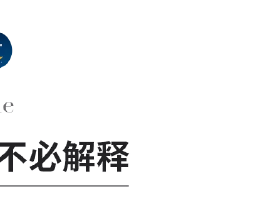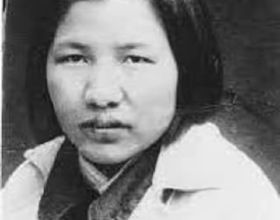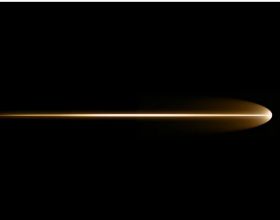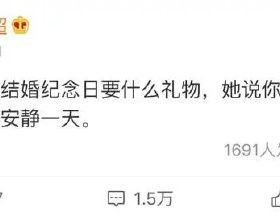#戰爭風雲#1941年12月7日晨(夏威夷時間、東京時間為12月8日),日本不宣而戰,突襲美軍位於夏威夷的海軍基地珍珠港。歷時90分鐘的轟炸,擊沉美軍4艘戰列艦和2艘驅逐艦、炸燬188架飛機,並給美軍造成2400餘人喪生,1250餘人受傷的嚴重損失。
坐在輪椅上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在華盛頓獲悉這一訊息後,面色陰沉地質問掌管情報工作的頭頭腦腦——
“當冰雹般的炸彈落在珍珠港之前,美軍情報部門是瞎了還是聾了?為何一無所知?”
經過徹查,美國人突然發現,他們忽略了一份來自中國的情報,這份情報簡要的通報了日軍短期內將有可能對美軍發起突襲,目標是美軍位於太平洋上的某個軍事基地,極大機率是珍珠港。
這份來自中國的預警情報是真實存在的,現位於美國路易斯安那州新奧爾良市美國國家二戰博物館(The National WWII Museum)的館藏檔案中確實存有這份情報的影印件。
那麼,中國情報系統是如何獲得這份情報的?
現存的史料對這份預警情報的來源有三種完全不同的記載。
情報來源考:軍統監測說
這份情報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透過對日軍的無線電偵測獲取,並破譯。
支援這種說法的證據有三:
1、白紙黑字,美國國家二戰博物館館藏的這份電報影印件,正是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發來的。
2、由於當時的日軍經常轟炸重慶,軍統自遷到重慶後,對監測、偵聽侵華日軍陸軍航空隊的電臺從未間斷過。對日軍陸軍航空隊電臺的收發規律很熟悉,並能迅速破譯。
3、珍珠港事件後,美國海軍情報部門曾派專員來華,與戴笠領導的軍統電訊處展開深度合作。
但是——
1、美方得到中方的預警情報雖然來自國民政府,但並不代表該情報就一定會是軍統所提供。
2、空襲珍珠港的日軍機群並非侵華日軍陸軍航空隊,而是日本海軍大將、海軍聯合艦隊司令官山本五十六麾下的航母編隊艦載機部隊。
軍統熟悉侵華日軍陸軍航空隊的電臺收發規律,並不意味著軍統也熟悉日本海軍聯合艦隊的電臺收發規律,並且還能破譯。
3、美國海軍情報部門與軍統的合作,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已經存在,乃至後來的“中美合作所”建立,都是在兩國政府的規劃之中,都是屬於戰時的、正常的雙邊軍事交流專案。
情報來源考: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二廳情報處長楊宣誠
楊宣誠(1890年—1962年),湖南長沙人。海軍中將,軍事情報專家。16歲赴日本留學,1913年轉赴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學習,1918年學成回國。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急需一批精通日語,具有留日經歷的人員作為情報人員,楊宣誠因此進入軍事委員會第二廳第一部情報處工作,後升任情報處處長兼對敵宣傳組組長。主持對日情報蒐集、策反等工作。
1941年初,由楊宣誠負責的情報處電訊科監測電臺偵測到日軍電臺一組新波段,但這組新波段發報頻率很低,電文卻很長。由於距離太遠,訊號非常微弱,無法破譯,但楊宣誠始終沒有放棄。
經過長期監測,第二廳電訊科海外組透過技術手段偵測發現:該波段來自太平洋日本海軍聯合艦隊。雖然知道出處,但仍然無法破譯。
時間來到了1941年5月,從這時起,第二廳電訊科海外組偵測到日本海軍聯合艦隊這一波段突然活躍起來,收發變得非常頻繁。
楊宣誠敏銳的感覺到:在太平洋某處重要的區域將會有重大事件發生。
於是火速上報,經過上級研判,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最終向美國政府通報預警。
情報來源考:延安中共中央社會部潘漢年
潘漢年(1906年—1977年),江蘇宜興人。我黨我軍隱蔽戰線的傑出代表、卓越領導人。抗日戰爭時期,潘漢年在上海、香港等地領導對日偽情報工作,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獲取日軍軍事動向的重要戰略情報,並通報重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
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期間,外務省在上海開辦了一所名為“同文學院”的學校,實質上就是日本外務省在上海設定的一處特務機構,其辦學目的是為了培養一批漢奸走狗為其所用。
潘漢年藉此機會安排了一批我方人員報考該學院,以備不時之需。其中順利考入的一名學員名叫鍾西公,該學員是日僑,更是一名反戰同盟的日本共產黨員。
鍾西公在“同文學院”畢業後被分配到哈爾濱外務省滿鐵系統辦事處工作,因本身就是日本人,所以很快成為了一名能夠接觸到本系統絕密檔案的高階職員。
1941年10月,鍾西公看到了外務省一份絕密級的《國際戰略形勢通報》,通報中明確寫道:在1941年11月底,日本將徹底終止與美國的談判,並能很好地應對接下來的一切結果。
鍾西公對這份通報極為警覺,馬上透過渠道直接將該情報傳送給潘漢年。延安中共中央社會部對這份情報進行了研判,並結合其他渠道得來的日本海軍各項情報資料進行綜合分析,最終判斷——
“日本海軍在太平洋上將有一次重大行動!”
隨後,由潘漢年將這一情報透過特殊關係轉給了軍統。但為了保護鍾西公,潘漢年並沒有說明情報來源。
中共中央社會部是軍統所熟知的,潘漢年的名字對軍統情報人員來說更是如雷貫耳。軍統因此不敢怠慢,迅速上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最終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將該情報通報美國政府。
結語——
綜上所述,這份本來足以改變二戰史,卻沒有受到美國重視的珍貴情報,究竟來源於何處,至今存疑。
以上資料分別出自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軍統興衰實錄:國民黨將領的親歷回憶》、新華出版社出版的《珍珠港事件前的日日夜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