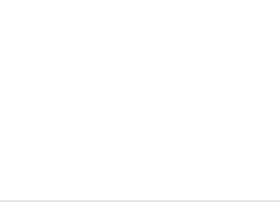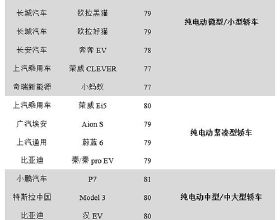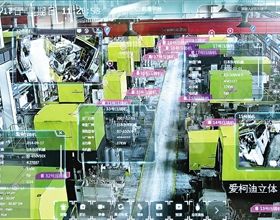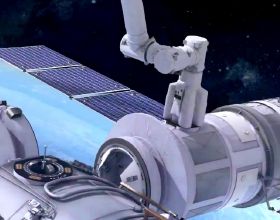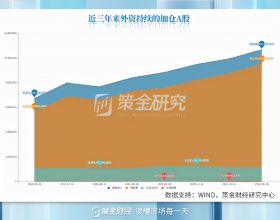2021年,一個叫“馬金瑜”的女人闖入了大眾的視線,她短髮圓臉,個子並不高,一張胖胖的臉上,被高原的風沙、太陽催得紅裡帶黑。她真正的出名,還是那篇《另一個拉姆》,在文章裡,她竭盡她的所能,爆料了丈夫扎西(謝得成)在婚姻幾年裡對她施暴、出軌的種種。文筆細膩,惹人垂傷:世界上真的有這種男人嗎?登時看得人很難受!
事實果真如此嗎?馬金瑜和扎西之間有著怎樣的愛恨情仇呢?為何一個有著絕佳文筆的“城市記者”和一個自小在草原長大的、“像山泉水一樣純淨”的、認識47天就閃婚的男人,曾經在世人眼裡那麼恩愛,會過到一種讓人人唏噓的地步呢?
馬金瑜的前世今生,新疆長大,是民生深度報道記者,具備對苦難和底層很強的共情能力
先說說馬金瑜。馬金瑜其人,是生長於新疆生產自治區建設兵團的兵團字弟,她家一家五口,有兩個弟弟,從小家裡也很貧困。她從小在“逃離大西北”的計劃中長大,在馬金瑜的記憶裡,童年時候的她就要經常撿棉花,幹農活,她很厭倦了這樣的農村生活,發誓一定好好學習。“新疆冬天的雪很厚,凍得土壤都是硬殼,但就算把腿凍壞了也要去上學。”
值得一提的是,馬金瑜的父親也打過她母親,但是她也沒有離開他,“就這樣磕磕絆絆過了一輩子”。
後來,馬金瑜果然走出了新疆,到上海上大學,畢業後,她本想留在上海工作,考慮到父親身體不好,她還是聽從了父親的話回到了新疆烏魯木齊,在一家媒體裡工作。
大西北的風沙沒有掩蓋住她的才華,她最擅長寫人物故事,底層故事,時常在邊城引起轟動。後來,北京的《新京報》看中她的才華,以高額的薪資僱傭了她,就這樣,馬金瑜從新疆來到了北京工作。後來,她又跳槽到廣州《南方都市報》,《南方人物週刊》等媒體,把奮鬥的戰場從京城轉移至廣州。任職期間,她收穫了包括“亞洲新聞獎”和“騰訊新聞獎”在內的幾個獎項,她最擅長底層人物故事,具備很高的共情能力。
但是生活中的馬金瑜,卻有點“二”,做事不得章法,且很容易在愛情面前犯“花痴”。比如說朋友在聊天,本來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口才非常好的她,一談到這方面的話題,她就很容易“犯二”。話都不會講了,需要“喝兩口水再說”,還有一次在報社突然想到一個很好的選題時,她不顧一切就直接衝進了主編室,把其他人嚇了一大跳。
初見愛情,47天即閃婚,父輩的奉獻犧牲,長姐的隱忍負重,讓相貌平平、個頭矮小的馬金瑜,骨子裡浪漫的英雄主義和濃郁的聖母情結,相互碰撞,交織生長
時間到了2010年,那時候,她有一個採訪蜂農的任務。此時已經32歲的馬金瑜,到了雲南、青海等地採訪逐蜂而作的蜂農。最後一個採訪任務,她到了青海海南自治州貴德縣,採訪一位名叫扎西的蜂農。
扎西,原名謝德成,1980年出生於貴德縣,從小母親去世,謝德成並沒有感受到太多的母親,之後他就跟著父親養蜂為生,也沒有學過文化知識。30多歲了還沒有結婚,這在草原上並不多見。
初見扎西的馬金瑜,已經是32歲的大齡剩女,圓臉短髮,沒有男朋友。她的外形並不突出。第一次見面,扎西就害羞臉紅了,他從來沒見過大城市來的女人。再加上從小和父親長大,很渴望有一個女人在他身邊。第一次見面,他就有種就對馬金瑜微妙的情愫和情感盪漾開,但他不敢輕易表白,害怕別人笑話他。
在扎西的心理,要“高攀馬金瑜是高攀不上的”,那為什麼後來,是什麼原因讓他鼓起勇氣表白呢?
原來,在第一次採訪結束後,馬金瑜回到了廣州組織稿件。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間,馬金瑜曾為扎西充過八百元的話費。馬金瑜是一個出手特別大方的女人,見不得底層的人尤其是不如自己的人受苦。而扎西原本充過最多的話費就是五十元,現在這個大城市的女人一下子就為他充了八百元話費!在他心裡,馬金瑜就是一個妥妥的大富婆!
馬金瑜回去後,扎西還是不斷的想起她,於是一個月後,終於趁著酒勁,扎西再也抑制不住心裡的情愫給馬金瑜打了電話,電話一接通,他哭了,他對馬金瑜說:“我喜歡你”,沒想到聽著他真誠的表白,馬金瑜也哭了。她對扎西說,過幾天來找他。
幾天後,馬金瑜果然來了。初次見面,兩個人就緊緊抱在一起。就這樣,兩個人開始談戀愛了。扎西覺得這樣的女友來之不易,當即向馬金瑜提出,希望能和馬金瑜結婚。馬金瑜倒也爽快,二話不說就同意了。
2010年9月8日,馬金瑜和扎西在貴德縣領取了結婚證書,兩個人從相識到領證僅僅才40天,就連馬金瑜自己都說,這樣的戀愛是糊里糊塗的。就連她身邊很多人,都覺得她嫁給他很不可思議,,甚至用了“amazing”這樣的形容詞來形容當時的感受。
婚後生活,困難壓力重重。看見網際網路的商機,辭職開網店創業風雲突起,家庭婚姻事業危機重重
結婚後,扎西仍留在青海當地養蜂,而馬金瑜,仍在媒體工作,仍然到全國各地去採訪。甚至有時候,還揹著孩子北京、青海的跑,覺得自己很奔波,但即便這樣,在2012年春節,扎西到廣州找他的時候,她也沒動過回青海的心思。
2012年,老大剛剛出生兩個月,因為黃疸嚴重,馬金瑜和扎西帶著他子從西寧趕往貴德縣,在快到貴德縣城時,遭遇了嚴重的車禍。而孩子重度受傷,在重症監護室住了19天,終於救了回來。醫藥費二十多萬,是馬金瑜找她的的同事們湊出來的。而且孩子腦部還受傷,造成了後來的發育遲緩以及一些行動上的麻煩。
2014年,扎西轉移蜂場,公公挖蟲草,馬金瑜只好把兒子放在揹簍裡,背到杭州,帶著一起去採訪物件家裡。
而彼時,網際網路帶貨正以一種新的經濟形式,悄然興起。青海富硒蒜被打上"防癌"的標籤,“談癌色變”的國人爭相購買。而青海蜂蜜、黃菇、花椒、牛羊肉、菜籽油、土豆被打上了“綠色”、“原生態”的標籤,敏銳的馬金瑜嗅到了這個商機,也看到了一條能讓她的家庭和事業兼顧的道路,她不難不動心。
2015年2月,她註冊了深圳扎西和卓瑪的家電子商務有限公司,自己任法人和董事,主要經營手工皂。
2016年,扎西也註冊了貴德縣草原珍珠電子商務有限公司,馬金瑜任監事,業務涵蓋他們微店的一切商品:牛羊肉、黃菇、洋芋、大蒜、花椒、菜籽油、青稞、燕麥……緊扣時代扶貧工程,號稱要帶動藏民開啟銷路,走上致富之路。
巔峰時期,馬金瑜的網店營業額曾一度達到500萬/年,還聘請了二十名女工為她的網店打包、發貨。按理說,她的生活應該順風順水,殊不知,離職創業的婚姻生活危機重重,暗流湧動,即使鼓勵女大學生愛情是個坑也要跳的馬金瑜,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愛情事業遭遇水土不服,被出軌、家暴、欠下鉅債、隨後離婚,苦心孤詣的馬金瑜,後悔了嗎?
據瞭解,有一次馬金瑜打算創業養臧雞,要以農民合作社的形式來發展。當時貸款了八十萬元,但是她沒想到的問題很多,例如“草原上有老鷹抓小雞”的問題,還有就是她以購買雞苗給農戶散養,最後再回收的形式來做此專案,初期竟然沒有與農戶籤任何形式的協議,也就沒有對農戶形成任何形式的約束。可想而知,這個扶貧專案以流產告終。損失估摸不小,這也為她後來的一系列失敗留下禍根。
扎西果真家暴她了嗎?在致富經2016年年對她的採訪《女記者嫁入青藏高原之後》,馬金瑜自己都忍不住調侃自己,很多人說她是被扎西的美貌“迷住了”,兩個人也曾經互打過,而且,扎西也向記者袒露,她曾四次向他提起過離婚,而扎西每次都不同意。而在很多時候,在扎西的眼裡,在草原上,"女人是不能做生意的,哪有女人說話的份”......
《另一個拉姆》爆出,朋友的傾力幫助,自媒體的討伐,馬金瑜果真是被家暴而離婚嗎?其實,擁有話語權的女性,沒那麼簡單。
直到後來,馬金瑜親手所寫《另一個拉姆》爆出,大家才看到馬金瑜的婚姻,並不像是她所描述的那樣,像“世外桃源”一樣,而那個在她心裡純淨無暇的男人,竟然也會打她,而且多次打得她小便失禁,也差點小產,事實是怎樣的呢?
在這期間,馬金瑜得到了很多善意的關注,有替她解圍的,要幫她上訴報警的,為她眾籌賠錢的(此時已欠下百萬鉅債)、給她的網店引流的,甚至有直接轉錢的,還有要幫她小孩上學的,為此,她的欠款很快還完了。
就在那個時候,她的一些朋友發的一份宣告,又把她推上了輿論,原來是她的朋友們聯合寫了一份債務清償申明,以及要籌錢幫他養幾個小孩,很多人就開始質疑她最初的發文的動機,是在炒作,營銷自己,博得同情,為網店引流,目的是讓人幫她還債,而且據貴德縣警方的調查,當時馬金瑜爆料被家暴,但是沒有出警記錄,青海當地的醫院也沒有治療記錄。最後,扎西也被爆出父母都是漢族,自己也是漢族,僅僅是為了立人設,馬金瑜才幫他取名叫扎西,穿上藏族的服裝賣貨。
一時間有很多人覺得馬金瑜說謊,為了博取同情讓人幫助她脫困,甚至還有人同情起扎西,覺得她不容易。因為那份爆料是2021年發出來的,而此時馬金瑜已經離開了三四年之久。
而當扶貧專案失敗,她在說明裡隻字未提欠債的事情,尤其當愛情也遇到了“豬隊友”,她更是有苦難言。儘管後來,她也釋出了另一篇《金瑜,還是那個金瑜》,承認了債務,也儘量爭取孩子撫養權,並且發聲這僅是個人案例,不代表地域和族群,讓人最為感慨的是,她在文末說,“也許會重回寫作,人的一生,能做好的事情,其實就那一兩件”。不管之前,馬金瑜撒沒撒謊。我相信這句話,她發自肺腑。
我傾向於認為,馬金瑜其實是立了一種人設,“為愛情不顧一切”、“扶貧”的標籤,她過早消費了她的愛情,哪知創業失敗,而債主的催促,讓她騎虎難下,於是寫下那篇《另一個拉姆》,不管主動還是被動,呈現在世人眼前。
生活不是講故事,避免過度營銷自己
苦難是博得同情的遮羞布嗎,我認為從來都不是。馬金瑜曾經供職於中國最有思想的媒體,而她失誤,可能也是高估了自己,高估了創業的難度。愛情也許看起來很美,婚姻過起來很苦。
所謂衝破世俗的一見鍾情,終將在柴米油鹽和賺錢養娃面前,露出痛苦的表情。而高原的生態不完善,鄉村社會複雜,她本身的經營不善,“而在那個地方做商業,需要更多的勇氣、智慧和擔當,需要更多的資源和幫助”,就像她說的,“人的一生,也許只能做好一兩件事”,最後,也許她也會迴歸寫作......
她曾什麼都想做,但最終什麼也沒有做好。擁有話語權的女性,不管是女記者還是女作家,都愛犯的一個通病,是過分暴露自己的情感。生活不是講故事,避免過度營銷自己。
馬金瑜事件,是一個受過創傷、受過教育的,理想主義女性向現實主義女性的跌落
而馬金瑜之於扎西,表面上看,是一個知識女性,愛上底層牧民的浪漫故事。但深層想,又何嘗不是兩個大齡青年的彼此拯救:一個懷著三毛式的浪漫,自認為找到了荷西般的真命天子,一個帶著對知識的嚮往,終於娶上有才有錢的女人。浪漫的外衣之下,是各自內在的匱乏,投射到對方身上的幻象。
也許,如果扶貧專案不失敗,馬金瑜還是會在高原上,繼續著她和扎西的“詩和遠方”,如果大兒子不受傷,也許她也不會放棄自己的工作,很有可能,會把扎西拐到城市,成為一名快遞員或者外賣員,抑或開一個特產店;也許,她們還是一直這樣分居著,一個記者,一個蜂農,直到彼此雙方退休。
可惜沒有可惜,如果沒有如果,馬金瑜根本就不是另一個拉姆。她始終都是她自己。
參考資料:1、《致富經》;
2、《澎湃新聞》對其的採訪;
3、《青海羚網》對其採訪;
4、《大河網》;
5、其本人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