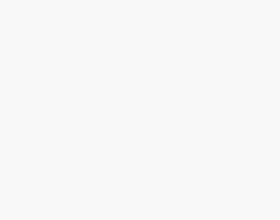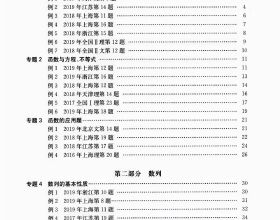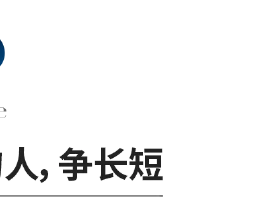吳放駒
第1012期
1977年10月,恢復高考的訊息席捲全國,報考工作緊接著一級級向下傳達佈署,公社隨之發出了鼓勵“知識青年”報名的通知。
我有幸算是“知識青年”中的一員,聽到這個訊息卻沒有驚喜。
我屬於響噹噹的“老三屆”成員,卻又是當時“知識青年”中讀書最少的一批:1965年秋入初中,1966年就開始了“文革”,我所在的涇縣中學是涇縣的“最高學府”,“鬧革命”當然就早於縣內其他中學,我們這一屆升到初二隻領了課本,一節課沒上,整天戴著個“紅衛兵”袖章,就知道“快快樂樂鬧革命”。我一個農村孩子,覺得跟“他們”耗不起,到1967年,乾脆跑回生產隊掙工分去了。
1968年10月,學校將我們召回,每人發了一張像獎狀的“上山下鄉狀”,我就成了一名“回鄉知識青年”,實際上就是正式農民了。這張“上山下鄉狀”後來就等同於初中畢業證書,可是名曰“初中畢業”,實際只是“初一生”,可笑的是當時的我們還沾沾自喜,認為撿了個便宜呢!
而“回鄉知識青年”基本上不被當“知識青年”看待,更倒楣的是我父親是“反革命分子”,戴著“四類分子”的帽子,受著“無產階級專政”管制。我也就只好老老實實當個“四類分子”子女,老老實實在生產隊做農民。直到1977年春村裡小學辦附屬初中班,那時下放知識青年大部分透過各種途徑和手段“上調”回城,剩下沒回城的也早沒心思在農村待著而跑回城裡“待調”去了,實在找不到人來教,於是我才被勉強當作“可教育子女”,當上了一名民辦教師。你想啊,初一學力、當上民辦教師也才幾個月,放到今天幾乎可算“半文盲”的一個人,敢參加高考?哪來驚喜?
我卻毫不猶豫地報了名,沒有奢望考取,只是為了逃婚。
1977年,我已經26虛歲,尚未結婚。在當時的農村,那可是“高齡”剩男了。父母很著急,我卻因為自己是讀過書的“知識青年”(別看只讀了個初一,在當時的農村那也是鳳毛麟角),不甘心在農村待一輩子而不願談婚論嫁。儘管作為“四類分子”子女的我當時並沒有看到絲毫希望,還是莫名固執盲目地“等”。
妹妹上年出嫁,做裁縫的母親一下子少了幫手,話計忙不過來,更是迫切為我張羅婚事,託人給我介紹了個也學裁縫手藝的姑娘,同時火力全開軟硬兼施逼我結婚。看著辛勞的母親,想著自己的處境,萬般無奈之下我只有答應了。正巧高考訊息恰逢其時地來了,我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向父母要求讓我考一下,考上了去上學,考不上就結婚。父母同意了。我知道這只是權宜之計,自己考取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也只有捱一時算一時了。
到底不敢報考大學,就報了箇中專。既然去參考,總得準備一番,考中專要考語文、政治、數學、物理、化學、英語六門,於是去找來了全部的初中課本。讀書時候,我的語文、數學成績都不錯,當時又正在教初一語文、政治,自信語文、政治可以應付;數學嘛,居然不太費力地在很短時間內自學完了初二初三的全部課程;可是物理是初二開始學、化學是初三開始學,我根本沒有接觸到過,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後物理算是學了點皮毛、化學是一頭霧水;英語嘛,只好考多少算多少啦。考試完後,就將此事丟到一邊,“黔驢技窮”地做著結婚準備。
沒想到的是,考後過了好多天,村裡的高音喇叭裡忽然響起初選上的考生去公社開會的通知,一遍一遍播了好幾次,我分明地聽到了自己的名字,當時簡直不敢相信。很多村人也聽到了,跑來告訴我,應該是真的了!
那一年,我們公社一共初選上了28個人,14個大學的,14箇中專的。接著是到縣城體檢,體檢地點設在當時的縣委黨校(與縣城隔青弋江相望的水西山上),時令正值隆冬,體檢出來已是下午,天上下起了鵝毛大雪,沒有車子,步行回家,我們村就我一個初選生,我也不認識別村的。
一個人撐個油布傘踽踽獨行,雪越下越大,油布傘一會兒就堆滿了雪,得不斷地抖落去,否則會沉重不支。走到公社所在地丁橋村對面青弋江邊,只見灰濛濛天地一色,迷了方向,找不著渡船位置了,覺得自己是那麼地無助,那麼地微不足道!正忐忑呢,見遠遠地兩把傘向河邊移動,我已顧不上認不認識,站著等近來搭訕,原來是丁橋的兩個初選女生,也和我一樣參加體檢回來,她們熟悉地形,我得以與她們同行,總算是沒有被大雪所“吞噬”。
又接著是政審,首先得生產大隊填寫意見,大隊“兩委”開會,經過研究後在我的政審表上“慎重”地填上了兩句話:“父親是反革命分子,本人勞動表現一般。”然後蓋上公章。十分的客觀真實,我無法否認,只能遞交,結果可想而知。
學雖然沒上成,但我已經發現了自己的潛力。那一年考試成績沒有公佈,也許不僅僅是政審問題,可能分數不夠呢,而且我們公社初選上的28個人,只有三分之一被錄取,大部分人都和我一樣落選。希望,已在前面出現。我決定投入複習,明年再考!父母沒有反對,結婚問題被擱置。
時隔半年,1978年的高考改為夏季,吸取理化未學過的教訓,我改報了大學文科。考後成績公佈,我考了306分,初選分數線300分,我又初選上了!這次我們公社初選上14人,正好是上年的一半。
體檢正值盛夏,地點仍設在水西縣委黨校,體檢中別的一切正常,唯量血壓,居然高了!激動?高溫?不得而知,恐慌油然而生。體檢醫生很同情,說暫不記錄,讓我過一會重量,並告訴我不要慌,要心靜。怎麼“心靜”?能靜得了嗎?半小時後再量,還是高!我真的慌了。體檢醫生連連安慰我,說還不記錄,再過一會重量。這時外面忽然下起雨來,同時來了風,我跑到屋外,張開手臂,將自己淋了個半溼,燥熱暫休,身上頓時涼快下來,進去又量,血壓終於退到了正常值,我和醫生都鬆了一口氣。
接在後面的政審比較順利,大隊沒有再為難我。現在就是等了,我滿懷希望等來的結果是,錄取分數線310分,我差4分。緊接著又傳來訊息,說要補招,300分以上全部錄取,希望重新燃起。但這個不是全國統一行動,而是由各省根據省情自定,結果好多省份都執行了而安徽省偏偏沒有,我被拒之大學門外,希望落空。我不甘心,鬥志不減反增,決心再戰明年!
1979年高考,經過了一年的艱苦複習,我對自己頗有了一點信心。沒想到考題比上年難了許多,考得很是辛苦,特別是地理一道大題,其中一個時區題,本有計算公式己經套算完成,我卻鬼使神差地不放心,於是在稿紙上用原始辦法畫岀時區來“扳指頭”數,考出來查書才發現畫漏了中間一個0時區,本來答對的,滿盤改錯了。
成績出來,我297.5分,與上年比,成績下降了8.5分,完了,沒指望了。可是結果公佈,我還是初選上了,這次初選分數線290分,我的成績超分數線7.5分,這樣計算,就比去年提高了1.5分,希望也上升了1.5分。可是畢竟只有1.5分,要是那道地理題不改就好了!可是沒有後悔藥吃。忐忑中等來的結果是,錄取分數線300分,我以2.5分之差又一次與“大學夢”失之交臂。
幾次三番名落孫山,失望、沮喪,自信心嚴重受挫。如果繼續再考,應屆畢業生已經接上茬,我們這些學歷殘缺的“老三屆”劣勢凸顯。可是放棄吧,三年的辛苦白費了;而且,自己也已年近“而立”,還有沒有再“跳農門”的機會和途徑呢?
猶豫中,同年迎來了我縣第一批民辦教師轉正招考。因為我的連續三年高考經歷,加上在民師的崗位上也做出了一點成績,得到了學校和公社領導的賞識和關懷,領導主動關照和熱心鼓勵我報了名。我當時的思想是,不好意思拂了領導的好意,但對考取並沒有抱多少希望,因為全縣有幾千民師報考卻只招錄幾十人,可謂“百裡挑一”,其難度較之高考有過之而無不及。沒想到卻考取了!而且是我們公社唯一考取的。我終於跳出了“農門”,成了一名正式的公辦教師。
教師轉正後,我立即被派往外村一所小學任負責人,三年後被調到鄉中心小學任教導主任,隨後擔任中心小學校長。期間,我因為沒有正規學歷,又參加了安徽大學“文革”後第一批中文專業函授考試,成為全縣數以千計的參考者中僅錄取4人中的一員(另有法律專業亦錄取4人),雖曰函授,教學卻相當正規,於我更算是接受了一次“正統”的大學教育,文化知識汲取收益頗豐。後來,我轉任鎮中學校長,任上又被提拔為鎮黨委副書記,從教師出口到了行政上。
回首高考,我算是嘗夠了艱辛,歷經了希望、失望、興奮、沮喪,三年考試,三年初選,三年未錄取。看似白費勁一場,卻意外地讓我在高考之外取得了至少三大收穫:其一,“逃婚”成功,父母再也沒有逼我結婚,那門親事也“黃”了,我一直到教師轉正兩年後才結婚;其二,高考複習的“知識儲備”無意中幫助了我民師考試轉正,因為是第一批轉正又是全公社唯一,為我後來任職校長積澱了重要的“資本”和“威望”;其三,高考“餘熱”又幫助我比較輕鬆地考上了安徽大學中文專業函授,這一段“大學學歷”不僅對我在職時的工作助力明顯,而且對我在退休後成為一個“附庸風雅”的“文人”也有著至關重要的基礎作用。
恢復高考,是我國曆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它改變了莘莘學子的人生命運,從它身上能夠透視到 那個時代的烙印,也看到了國家和民族的希望!我與高考“糾纏”三年,雖然最終被拒之門外,我還是要對它真心地道一聲:謝謝!
(作者系涇縣文旅局退休幹部,宣城市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
製作:童達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