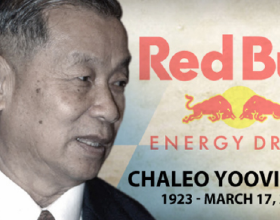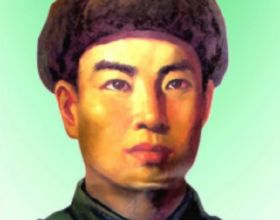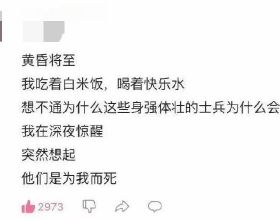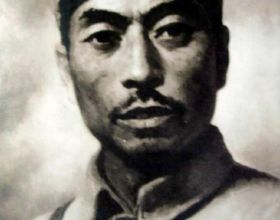1997年2月19日,一個舉國哀痛的訊息傳來——小平同志去世了。
“小平,走了啊……”聽聞訊息的夏伯根老人低聲唸叨,一向樂觀的她流下了眼淚。
圖1
從青年時期懷揣“工業救國”理想遠渡重洋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到數次革命戰爭中卓越領導,再到給新中國成立後的改革開放事業設計方針政策,小平同志為新中國的誕生與發展立下赫赫戰功,他是在艱苦的革命歲月中錘鍊成長的世紀偉人。
新中國成立以後,小平同志為國家和人民鞠躬盡瘁,將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國家建設中,這也使他對家庭的關心變少了,好在有妻子卓琳和另一個重要親人幫他打理家務,小平同志才能全身心為國家做奉獻。
這位重要的親人便是夏伯根,她是比小平同志大五歲的繼母,也是小平同志後半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位親人。
對於這位繼母,小平同志先後用了三種不同的稱呼,那麼這些稱呼都發生在什麼時候?
二人的緣分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夏伯根又是在什麼時候見到了小平同志?見面以後發生了什麼?他們又共同經歷了什麼呢?
一生都留給了鄧家
夏伯根在四川嘉陵江長大,父親是一位船工,家境貧寒的她沒有機會上學,也不認識幾個字。
夏伯根的母親在她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父親獨自一人將她撫養長大。
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夏伯根自小很懂事,從來沒有抱怨過生活的艱苦,吃苦耐勞,遇到困難的時候也總是樂觀豁達,從來不會哀嘆生活。
舊社會的婚姻多數是父母一手操辦,在夏伯根十幾歲的時候,父親便為她尋了一門不錯親事,早早地嫁了人。
夏伯根婚後的生活雖說不是富貴生活,但是日子也是過得簡單舒適,還生下了一個可愛的女兒。可惜好景不長,在她女兒剛幾歲的時候,她的丈夫就因病去世了。
一次偶然的機會,鄧紹昌與夏伯根在重慶相遇,兩人見面後對彼此都有好感。
後來,在熟人的撮合下,夏伯根帶著先夫的女兒嫁給了鄧紹昌。
鄧紹昌是小平同志的父親,小平同志的母親淡氏是他的第二任妻子。
小平同志有兩位母親,一位是他的生母淡氏,另一位是繼母夏伯根。
小平同志的父親鄧紹昌是知識分子家庭出身,早年在成都法政學校學過習,還在家鄉當過一段時間的教書先生,思想很開明。
作為家裡的長子長孫,小平同志自小便受到全家人的重視與寵愛,生母淡氏也總是將他帶在身邊,每當他出門的時候,母親淡氏常常在家盼望兒子歸來。
在小平同志十六歲的時候,鄧紹昌便決定將他送往法國學習,對此,生母淡氏十分不捨,曾經極力阻止,無奈父子二人心意已定,只好為兒子收拾好行囊送兒子離開了家鄉,這一次分別竟是母子二人的最後一次見面。
小平同志離家後,淡氏想念兒子,時常和鄧紹昌抱怨:
“娃兒才十六歲,就去那麼遠,怎麼忍心喔!”
1926年,小平同志離開家的第七年,淡氏得了肺病,不久後就病逝了,遺憾的是離世時沒有盼到兒子回來。
為了讓兒子安心學習,鄧紹昌並沒有將小平同志母親病逝的訊息告訴小平同志,直到小平同志回國坐地下工作時,小平同志才聽弟弟鄧先修說起母親離世的訊息。
淡氏是一位勤勞能幹的女子,將家裡打理得井井有條,後來,小平同志每每想起自己的生母,常常感嘆:“當時那個家能夠保持生活下去,全靠母親。”
淡氏去世以後,鄧紹昌娶了船工的女兒夏伯根。夏伯根嫁到鄧家的時候,小平同志正在國內為了革命四處奔波,還不知道家中有一位繼母。
夏伯根也只是聽說家中還有一位長子,早年間去國外留學,在革命戰爭時代,二人始終沒有見過面,但是夏伯根常常教育孩子們要向大哥哥學習。
夏伯根嫁入鄧家以後,勤勞能幹,將一大家子照顧得很好,雖然沒有讀過書,卻也十分明事理。
對於這平淡而又忙碌的生活,夏伯根感到十分滿足。然而,安穩的日子並沒有持續很久,在小女兒不到一歲的時候,鄧紹昌不幸離世,這讓他們原本平靜的生活變得難過起來。
由於夏伯根嫁入鄧家前有過一段婚姻,在嫁入鄧家後生下了三個女兒,沒有一個兒子。在當時的封建時期,人們重男輕女的觀念還很嚴重,因此村裡很多人都對她議論紛紛。
鄧紹昌的離世對於家裡打擊很大,孩子還小,家裡需要照顧,種種困難並沒有讓夏伯根就此退縮,她毅然挑起了家裡的重擔,決定一個人將鄧家孩子撫養長大,照顧好鄧家。
夏伯根熱情善良又聰明能幹,經常幫助他人,對於那些議論她也並不在意,也不會記恨在心,常常以德報怨。漸漸地,村民們對她的看法變了,也越來越喜歡她了。
就這樣,在往後近二十年的艱苦歲月裡,夏伯根洗衣做飯、織布、種田,用勤勞的雙手將鄧家孩子撫養成人,日子雖然清貧,但是她始終樂觀,從來沒有哀嘆過生活艱辛。鄧家的孩子們也在夏伯根的精心照料下茁壯成長,不僅健康,也十分懂事。
深明大義,冒險救助共產黨
夏伯根雖然並沒有讀過書,但是十分明事理。對於革命也是十分支援,一心認定中國共產黨好,也支援子女們參加革命。
1947年,夏伯根的女兒鄧先芙考入縣裡女子中學學習,在革命的薰陶下,參加過多次校內外的革命活動,早年投身革命事業中去。
鄧先芙和母親說起時,夏伯根十分支援,還連夜做了很多鞋襪,讓女兒送給游擊隊。
在一次中共地下黨領導的一次起義中,一支小隊伍和大部隊走散,後來聽聞大部隊正在三元寨戰鬥,便急忙趕去與大部隊匯合。不幸的是這支小隊伍趕到的時候大部隊已經撤離,聽聞這個訊息,他們便決定稍作休息再前去追趕大部隊。
小隊伍裡有一位戰士叫龍田煥,在戰鬥中受了重傷,在戰友的攙扶下跟隨小隊伍路過了鄧家附近,此時正是秋天,天氣已經漸漸轉涼,天色也漸黑了,忙碌了一天的夏伯根正在房裡喂蠶。
還在忙的夏伯根聽到小女兒急匆匆地跑回家,一進家門便跑到夏伯根面前說:“媽,院子那邊來了一群人,都拿著槍,有個人被攙著,看著快死了。”
聽聞此話的夏伯根感到事情不對,便在女兒的帶領下來到了林子裡。剛進林子,遠遠的就能看到躺在地上的龍田煥,雖然右腿的傷口被簡單包紮了,但是鮮血還是止不住的流了出來。
夏伯根一眼就看出來這是一支游擊隊,眼見龍田煥的傷勢嚴重,這支小隊伍也沒有安身之處,放任不管的話,恐怕這位戰士真的會死。沒有絲毫猶豫,夏伯根當下就決定將他們帶回家:“我是鄧家院子的夏伯根,他受傷太嚴重了,耽誤不得了,趕快背到我家去吧。”
一名戰士將龍田煥背起來跟著夏伯根向鄧家院子走去,路上游擊隊員疑惑地問:“大娘,你為什麼幫助我們?不怕國民黨把你抓起來嗎?”
對此,夏伯根說道:“我知道游擊隊是老百姓的隊伍,都是為了老百姓好,你們都是好人,我怎麼能不管呢?你們都不怕國民黨來抓,我怕什麼?”就這樣,這支小隊伍跟著夏伯根來到了鄧家院子裡。
在夏伯根的照顧下,龍田煥醒了過來。由於傷勢過重,龍田煥還吃不下飯,夏伯根就專門做好一點點喂他。龍田煥認為自己耽誤了部隊的程序,還麻煩了鄧大娘一家,內心十分自責,他覺得自己是個累贅,與其活著拖累大家,不如死了,也算是給大家減輕負擔。
夏伯根看出了他的擔憂,坐在龍田煥跟前,安慰他:“孩子,你還年輕,你和我的孩子一樣大,你到我家就像我的孩子回家吃飯。我給你做好飯,你不吃,我會安心嗎?”
最終,在夏伯根的真情勸說下,龍田煥開始好好吃飯起來,他想快快好起來,好儘快離開,不要拖累鄧家。
為了防止被發現,夏伯根將大家都安排到了其他房間,只留下了一名女戰士照顧龍田煥,還專門囑咐他們,讓他們以後以兄妹互稱,對外稱這兩人是她的侄子與侄女。
由於龍田煥傷勢太重,簡單地清理傷口無法使他痊癒,只能請醫生前來治療。
可是,多一個人知道就多一份風險,在這危機的情況之下,夏伯根如何化解這個危機的呢?
為了掩護游擊隊的身份,夏伯根稱龍田煥是自己的侄兒,在一次拉船的時候不小心被鐵桿子砸到了,特別疼。
前來醫治的劉醫生到了,夏伯根的說辭瞞得過普通人,卻瞞不過行醫多年的醫生,劉醫生一眼看出來龍田煥的腿上是槍傷。
對此,劉醫生堅決拒絕,還說道:“上級說了,對於槍傷的處理,一律不許醫治,要立刻上報,如果不上報的話,會治醫生的罪的!”
聽聞此話的夏伯根直接對著劉醫生跪了下來,苦苦哀求。看到夏伯根跪下,在場的其他人也跟著跪了下來。劉先生最終被眾人的真情感動了,冒著被治罪的風險為龍田煥治槍傷,將他腿裡的子彈取了出來。
在夏伯根的照料下,龍田煥漸漸康復,不過傷口並沒有完全癒合,因此仍以夏伯根的侄子的身份在鄧家院子裡住著。
忽然有一天,家裡幫工急匆匆找到夏伯根說道:“大嫂,不好了,王保長馬上帶人來搜查了!”聽聞此話的夏伯根立刻讓幫工將龍田煥背到蠶房的閣樓上,還把他放在了簸箕裡面,蓋上桑葉。忙完這一切,只聽院門傳來一陣嘈雜聲,王保長帶著人氣洶洶地衝了進來。
王保長進門二話不說就帶人搜了起來,所有房屋都搜了一遍,只剩下藏龍田煥的蠶房還沒有搜,王保長走進蠶房,只見夏伯根正跪在一個小桌子前面不停的磕頭,嘴裡還唸叨著什麼。王保長一時被弄得一頭霧水:“夏伯根,你在搞什麼?”
夏伯根慢慢起身,說道:“王保長啊,今年蠶發了病,我正拜一拜,求保佑呢。”
王保長說道:“聽說你們家來了游擊隊,我們過來搜查,最好抓緊把人交出來,被我們找到了,你可吃不了兜著走……”
一聽王保長這樣說,夏伯根立刻哭喊起來:“哎呀,我這倒是得罪了誰了?怎麼這樣陷害我?王保長你要是懷疑我藏了游擊隊,就儘管搜查吧。”
說著便指向了閣樓,還說道:“就從這裡開始找吧。”
去閣樓的樓梯是竹子做的,容納不了很多人,王保長很重,每上一層樓梯,竹樓梯都會顫動一下,對此,夏伯根不停提醒他,可他還是執意要上去。爬到最上面以後,往裡面一看,一個簸箕裡面放滿了桑葉,王保長覺得這裡面根本藏不下人,便下來了,由於樓梯本來就不穩當,王保長還急著下來,一不小心踩空了,直接從高處摔了下了,嚇出了一身冷汗,隨後帶著人匆匆離去了。
這次危難讓夏伯根淡定而又巧妙地化解了,雖然並沒有讀過書,但是她深明大義,看到游擊隊有危險願意挺身而出,冒險保護革命的“火種”,這種大無畏的精神讓我們十分敬佩。
“留下來,我們一起生活”
1949年11月底,重慶解放,小平同志被任命為西南局第一書記。時隔二十九年,小平同志再次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家鄉。
很快,小平同志回重慶的訊息傳回了四川老家。小平同志的親舅舅淡以興聽到訊息後趕忙去找夏伯根,想要帶她一起去看望小平同志。夏伯根一直非常想見一下這個素未謀面的孩子,但她還是有些猶豫,在淡以興的堅持下,最終夏伯根決定與淡以興一同前去看望小平同志。
淡以興是小平同志生母淡氏的弟弟,兩個人雖然是兩輩人,但是隻有四歲的年齡差,兩個人自小就一起玩,有著很深厚的感情。
自從小平同志離開家鄉前去求學以後,兩人就沒有再見過面,至此已有三十餘年。
對於夏伯根,淡以興打心眼裡佩服。夏伯根來到鄧家以後,十分勤勞能幹,把鄧家的孩子照顧的很好,而且都培養的很優秀。對此,淡以興都看在了眼裡,打心眼裡認可了她。
兩人收拾好行囊便出發了,來到了重慶,一路打聽找到了小平同志的住所。二人到門口後,告訴警衛員自己是小平同志的舅舅和母親。夏伯根只比小平同志大五歲,看著這個自稱是小平同志的舅舅與母親的兩個人,警衛員心裡犯起了嘀咕。
但是,兩個人說得情真意切,一點都不像謊話,警衛員半信半疑地報告給了小平同志。
得知家中親人前來的時候,小平同志正在開會,公務繁忙抽不開身,只得派人安排兩人住下。等小平同志忙完公務已經很晚了,趕回家以後,淡以興和夏伯根已經等候多時。
本來在等待過程中,淡以興越等越著急,見不到人就開始胡思亂想起來,想著外甥有了本事就忘了家裡人。夏伯根見狀勸說淡以興:“你這個做舅舅的要理解他的工作,不要一直打擾孩子,他工作忙。”聽聞此話,淡以興才慢慢消氣。
見小平同志回到家中,淡以興打趣道:“我們可算把你等來了,還以為你如今長本事了,家裡人都不認了。”
小平同志聽到這話,趕忙說道:“舅舅,那怎麼能忘呢。”
兩人隨即聊了起來,許久未見的兩人有著說不完的話。夏伯根就在一旁靜靜地聽著,看著鄧家的長子如此有出息,心裡很是欣慰。
說到鄧家這些年,淡以興趕忙小小平同志介紹夏伯根,還說起夏伯根來鄧家以後辛苦忙碌,以及在鄧父去世以後含辛茹苦的照顧一大家子,把鄧家的孩子照顧的非常好,還有夏伯根支援革命的事情也都如數告訴了小平同志。
夏伯根聽聞這些並沒有覺得非常了不起,她覺得這些都是自己應該做的事情,這次來也是為了見小平同志一面。
聽聞夏伯根的這些事,小平同志非常感動,眼含熱淚對夏伯根說道:
“夏媽媽,您受苦了,留下來!今後我們給您養老。
”就這樣,夏伯根留在了小平同志身邊,這是他們的第一次見面,小平同志親切地稱呼夏伯根為“夏媽媽”。
聽到這個稱呼的夏伯根眼角也溼潤了。兩人緊緊握住彼此的手,一時間也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鄧家的天倫之樂
就這樣,夏伯根留在了小平同志的家中,因為小平同志與卓琳每天工作忙碌,夏伯根便把全部家務都包攬了過來,把家裡收拾的井井有條。
此外,夏伯根還慢慢了解了他們的口味,每次飯桌上都是他們愛吃的飯菜,家裡都對夏伯根的手藝讚不絕口。
1952年,由於工作原因,小平同志被調回了北京。
剛聽聞訊息的夏伯根心中有些忐忑,每天忙完家裡便不說話了,卓琳看著婆婆整日悶著,像是有心事,便主動找到婆婆談心。
原來,聽聞小平同志要去北京工作,夏伯根以為又要就此分別,感到十分難過。
知道婆婆的擔憂以後,卓琳感到十分自責,平時忙碌忽略了婆婆,竟讓婆婆有了這樣的想法。卓琳握著夏伯根的手說道:
“您放心,我們在哪您就在哪。”隨後一家人一起收拾行囊,準備一同去往北京。
到北京以後,聽聞夏伯根是第一次來到北京,卓琳只要一有空就會帶著她到處逛逛,碰到熟人就會大聲介紹:“這是我的婆婆,小平的母親。”
沒多久,卓琳就成了小平同志的秘書,兩個人天天早出晚歸,工作十分忙碌。夏伯根便攬下所有的家務活,照顧一家人,天還沒亮就為大家準備好早飯,照顧好孩子們吃飯上學,把一家人送走以後又開始準備午飯和晚飯。
家裡幾個孩子都是她親自帶大的。平日裡,夏伯根非常節儉,能動手做的不會額外花錢去買,對自己不捨得花錢。卓琳怕夏伯根不捨得買東西,常常叮囑婆婆不要對自己不捨得花錢,有喜歡的東西就買。
小平同志教育孩子們:“我們家不分親奶奶和繼奶奶,都叫奶奶。”
在家裡,孩子們也非常喜歡這個對他們照顧得無微不至的長輩,經常跟在夏伯根身後喊“奶奶”,日子久了,小平同志和妻子卓琳也隨著孩子們一起稱呼夏伯根“奶奶”,一家人其樂融融。自此,夏伯根又多了個稱呼。
有一段時間家裡過得非常拮据,還常常接濟遠在廣安生活困難的淡以興。為了挺過這段日子,夏伯根省吃儉用,能動手做得絕對不買,能用的絕對不扔不換。擔心小平同志夫妻會因此有矛盾,她還常常和卓琳談心。
對於婆婆的擔心,卓琳告訴夏伯根:
“我是瞭解他的,您放心吧,不會的!”這才讓夏伯根放下心來。
後來,小平同志一家到了江西,由於日子清苦,怕夏伯根跟著受苦,又擔心她沒人照顧,一時難以決定。
夏伯根知道後,毅然決定一同前往江西,在她心裡,一家人在一起總歸有個照應。在江西,考慮到夏伯根年齡大了,便不讓她乾重活。
可是,夏伯根總想為家裡分擔一些,常常幫人縫補衣服賺些錢補貼家用。三代人每天歡聲笑語,也很幸福。
等小平同志回到北京,家裡的第四代也出生了。一家人在一起,夏伯根也開始照料起來第四代的生活,孩子們親切的稱她為“老祖”,小平同志也隨著孩子們稱呼夏伯根“老祖”,這是二人見面之後的第三個稱呼。
夏伯根為小平同志和卓琳不僅把家裡打理得井井有條,還把家裡的溫馨帶進了鄧家。一家人日子其樂融融,雖然也有艱苦的時候,但一大家子聚在一起也是快樂的。
縱觀夏伯根的一生都留給了鄧家,前半生為鄧家兒女操勞,後半生有小平同志一家陪伴,享受天倫之樂。
1950年,夏伯根與小平同志相見,自此二人相互陪伴彼此近半個世紀,兩個人雖沒有血緣關係,卻是彼此一生中非常重要的親人,這份母子情誼深深地感動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