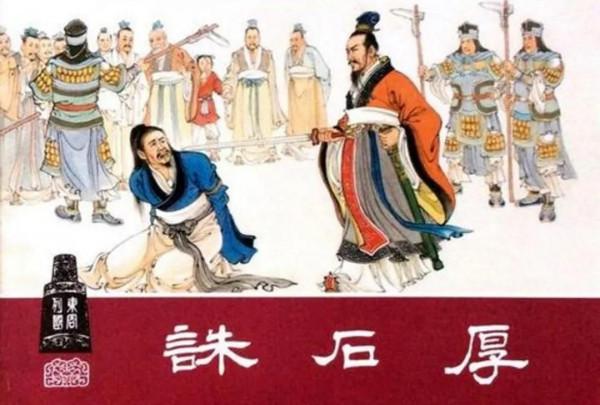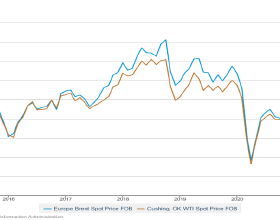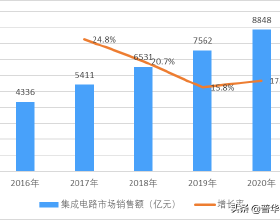公元前719年魯隱公四年,衛國公子州籲糾集黨徒襲殺了衛國國君衛桓公姬完,自己登上了國君之位。雖然進入春秋時期之後,屢屢發生弒殺國君上位的事件,但在春秋早期篡位者自身的威望要足夠高,可以得到精英集團的信任,否則只能等著被人趕下去。雖說春秋時期已經禮崩樂壞了,但還沒徹底崩壞,如果吃相過於難看,也會有人來打抱不平的。恰好州籲的威望就沒有那麼高,他在衛國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面對困局,他該怎麼辦呢?
樹立外敵
當一個團體內部矛盾較大時該怎麼辦?古今中外都“英雄所見略同”,那就是樹立一個強大的外敵,然後促進內部的團結,最後達到整合內部的目的。公元前499年到公元前449年在希臘半島爆發的波斯和希臘之間的戰爭就是這樣一個例子,面對強大的波斯帝國,本來打成一片混亂不堪的希臘諸城邦不得不聯合起來。他們有錢的出錢,有人的出人,有海軍的出海軍,有陸軍的出陸軍,歷經五十年的爭鬥終於把強大的波斯帝國頂了回去。面對強敵,地緣相近的團體會因為共同利益團結起來,這不僅發生在西方,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也是一樣。
州籲弒君自立之後,明顯地感覺到群臣的情緒不對,所以他急於採取措施穩定國內局勢,於是他將目光投向了國外。公元前722年魯隱公元年,在鄭國發生了一場決定鄭國未來的戰爭——鄢之戰。老奸巨猾的鄭莊公擺了弟弟共叔段和母親武姜一道,共叔段狼狽出逃,武姜被軟禁。而共叔段的兒子公孫滑則逃往了衛國。這時的衛國是衛桓公當政。衛桓公打抱不平指責鄭莊公囚母逼弟,帶領大軍主持正義,自不量力地討伐鄭莊公,把沒回過神來的鄭莊公打了一個冷不防。吃了虧的鄭莊公當然不會善罷甘休,處理好內部事務的後立刻組織王師,虢國和邾國以及魯國聯軍打到了衛國的都城。這時的鄭國可是春秋小霸,哪裡是衛國能招惹的,於是衛國便被按在地上打。如今公子州籲主持衛國大局,於是他便把目光轉向了鄭國。
宋國與鄭國的矛盾
宋穆公繼承了殷商時代的貴族傳統,把國君之位傳給了自己兄長的兒子與夷,同時把自己的兒子公子馮送到了鄭國。宋穆公覺得這樣做既可以對兄長宋宣公有所交代,又可以讓與夷和自己的兒子和平相處。這樣的安排看上去兩全其美,實際上卻隱患重重。由於宋穆公的良好品德,宋國上上下下對他的治理都很認可,同時也把對宋穆公的感情移到了宋穆公的兒子公子馮身上。所以公子馮的威望之大已經超過了宋殤公與夷。雖然公子馮出居鄭國,但他的影響力並沒有衰弱。
於是衛州籲給宋殤公寫了一封信,鼓動宋殤公進攻鄭國:
“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州籲的建議正中宋殤公的下懷,於是發生了東門之役(見本人撰寫的《春秋:宋殤公的腹心之疾與開啟中原之亂的“東門之役”》)。那麼衛州籲想透過樹立外敵團結內部來鞏固自己地位的目的達到了嗎?
效果
對於州籲鼓動攻打鄭國的的行為後果,魯隱公與大夫眾仲的對話給出了答案:
公問於眾仲曰:“衛州籲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籲,阻兵而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籲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眾仲認為應該“以德和民”,不應該“以亂和民”,想透過戰爭的手段鞏固自己的地位,必然會遭到反噬。事情的發展也正如眾仲所料,“九月,衛人殺州籲於濮”,很快州籲被衛國群臣聯合除掉了,州籲的統治連一年都沒能維持下去。
尾聲
春秋時代弒君奪位的亂臣賊子很多,為什麼州籲的統治如此短暫?雖說春秋時代已經禮崩樂壞,但也不是一點秩序也沒有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孔夫子提倡的禮義道德還是有用的。衛州籲沒有積累出很大的威望,於是他失敗了。所以在春秋時代即使內心不認同也必須豎起禮義道德的大旗,否則在春秋時代也是混不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