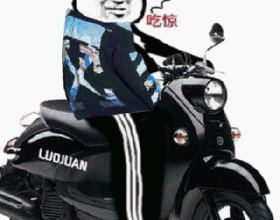“監獄中被刑滿釋放人員,想要透過一系列努力成為‘獄警’”
這是很多網友對於日本想要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一種調侃的比喻,雖然聽著有些詼諧,卻不失其中的道理。
想當初,中國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擁有令很多國家眼饞的“一票否決權”,卻有很多人不知道中國甚至在1943年12月在德黑蘭召開的最後一次會議上,連出席都沒有出席,依然能夠榜上有名,與日本遲遲“入常”屢屢失敗,原因竟然是一致的。
這其中的原因我們可以稍後來講,除此之外,令日本沒想到的是,攔住他不讓他“入常”成功的,竟然其中有他常年經濟援助的物件:非洲,這其中的原因又是什麼?
日本對非洲的經濟援助
我們先來說說日本對於非洲的援助,究竟是怎樣的援助,使得日本篤定了非洲各國會給予他們支援。
日本開始對非洲實施救助的時候,是日本最窮的時候,二戰結束沒有多少年,大概在1966年左右時,日本就開始向奈及利亞、坦尚尼亞及烏干達提供貸款援助。
自己窮還要做貧困戶,這打的是什麼算盤?日本求的就是“利”,求的就是經濟發展,抓緊把大蕭條的經濟發展起來,日本看上的就是非洲的原料市場。
從1945年到1960年這期間,日本推行吉田茂的“經濟立國”戰略,就是說把軍費開支收回來,全部用於經濟建設,他們需要非洲原料市場提供穩定的原料供應,需要和非洲保持貿易關係,不平衡的部分,日本以援助的方式加以平衡。
不過,這一時期日本援助的絕大部分份額在亞洲地區,非洲只佔一小部分。
我們知道日本能從二戰中緩過來,並且還能讓經濟迅速發展,躋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主要靠的不是“援助”做得有多好,是搭上美國的“順風車”,那麼為什麼幾年後,到了20世紀70年代,日本要突然加強了對於非洲援助的份額呢?
這就需要提到波及全世界的1973年發生的第一次石油危機,當時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石油輸出國組織為了打壓以色列,禁止了石油的出口,石油價格從每桶不到3美元漲到超過13美元。
前面我們講過,日本要經濟建設,要援助非洲,都是為了原料供應,石油在各方面建設都佔據著重要位置,中東不太平總打仗,不能在一棵樹上吊死,日本就瞄上了很多國家在石油供應上都“留著後手”的非洲地區。
從1974—1991年日本對埃及、肯亞、摩洛哥、迦納等十國的援助總額高達12838.58億日元,佔同期對非援助總額的近七成,日本對其的救助力度確實不容小覷。
總而言之,最開始日本對非洲援助的動機是為了經濟安全,之所以不考慮政治因素,主要是因為當時美蘇兩大陣營壓著“兩片天”,日本再想在政治舞臺上有所作為,一是戰敗國的影響,再就是多做的部分,不過就是給老大美國做了嫁衣而已。
不過從冷戰結束後,日本援助非洲的方向開始轉向了政治建設,就是說更講究“面上”的一些東西,幫助其建設國家基礎設施,總統訪問,展開對話會議等等,這是因為“天變了”,蘇聯在解體邊緣,國際局勢重新洗牌,經濟發達的日本當然想要政治上跟著“雙豐收”。
1983年開始,時任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了建立“政治大國”的構想,日本也將目光瞄上了此前和他們基本不搭邊的“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席位。
日本入常,意料之中的失敗
為什麼說這位置壓根和他們不搭邊?我們開頭講了,5個常任理事國就相當於是“國際警察”,當時“抓”的就是二戰中幾個興風作浪的戰敗國,姑且可以稱之為“犯人”。
日本不打著“軍國主義”的旗幟出來禍害世界人民,發展經濟各國管不著,但犯人要“當警察”,那仗不是白打了。
美蘇英中法這5個常任理事國,中國在參加完1943年10月由美國主導開展的外長會議後,最終在正式確定時,中國之所以會被選定,一方面是這幾個國家及盟國佔據了世界人口數的四分之三,一方面是中國為戰勝國,可以作為世界的和平代表,另一方面是平衡了英美兩個並不融洽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力量。
多年來,聯合國常任委員會的運作,充分體現他們“不缺人”,反而因為每個常任理事國都有“一票否決權”,而使得一些合理決策被無限擱置。
2020年,聯合國報告顯示,自聯合國成立以來,五常國家共計使用“一票否決權”293次,其中俄羅斯(蘇聯)佔了143次,美國佔了83次,中國用了16次。
德國總理默克爾曾說:”安理會‘過於經常’否決重要的決定,應當進行改革“,這要是再多加一些有一票否決權的國家,或是處在紛爭漩渦的國家,想必無論從決策的公正程度,還是透過率上都會大打折扣,安理會在很久一段時間內,是基本拒絕新成員的。
可並不證明沒有機會,前文提到的,被“非洲兄弟”攔住,沒能成功入常的那一次,也是被稱為入常名額最容易被“擴容”的,就是2005年的那次。
早在六七十年代,大批殖民地開始獲得獨立,第三世界國家總數增加,國際上也在給予他們應有的權益,這其中就有飽受爭議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
與此同時,呼籲安理會改革的國家也越來越多,當時非常任理事國席位數量已經從六個上升到十個,多個國家的積極加入,意味著越來越多的國家看到了其中的“甜頭”。
有能成的“苗頭”,經濟大國必然是要先出手,單打獨鬥有困難,德國日本印度巴西就湊成了一個”四國聯盟“,他們提出的要求是修改《聯合國憲法》。
“擴容”的提議容易被“一票否決”,修改《聯合國憲法》可是有明確規定的,只要有三分之二的國家支援,提案理應被採納,聯合國的成員國有193個,要想一下子“湊齊”這麼多國家的支援,沒有準備肯定是不行的。
日本對非洲的援助這時該是要派上用場了,其中非洲國家有53個,佔據聯合國成員總數的四分之一,可這時候非洲國家卻答應的沒那麼痛快,甚至開始批評起了日本援助的“居心叵測”。
同時,與“四國聯盟”同時出現的還有以義大利為首,韓國、阿根廷、巴基斯坦等國為主要成員的“團結謀共識”,也在世界範圍內瘋狂拉票,可以說,無論是主權國家,還是非主權國家,無論是“二戰”的戰勝國,還是戰敗國都想來“插一腳”。
這些“身家背景”不夠好,經濟發展比較強勁的國家出現在其中,總有不合時宜的意思,這時候“根紅苗正”的一批組團來了,掌握絕對票數的非洲國家,他們提出了“非盟方案”,要他們支援還不給他們席位那是萬萬行不通的,這是他們的底線。
“團結謀共識”不同意,經過協商,“四國聯盟”同意了非洲國家的方案,最後終於是湊出了三分之二的國家支援,但在最後協商細節的過程中,“團結謀共識”放棄是放棄了,可他們得不到的,對方也不能得到,開始瘋狂狙擊“四國聯盟”的方案。
先前”四國聯盟“根本沒想過接受”非盟方案“,雙方的要求也沒能達成一致,談判進展一度達到了瓶頸,最終導致“四國聯盟”提出的方案也失敗了。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這次“入常”失敗可以說耗光了日本的賭注,隨後幾年雖也在做著嘗試,但其力量大不如前。
一直到聯合國成立75週年的聯合國大會上,日本仍在試著爭取“日本做好了充分的準備,願加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並且履行相關責任。”結果可想而知。
那麼,為什麼能和中國保持長期穩定友好的援助關係的非洲,面對“老朋友”日本的幫助,能如此“忘恩負義”。
2016年10月非洲晴雨表釋出的報告顯示,近三分之二(63%)的非洲人認為,中國的影響“較為”或“非常”積極,而只有15%的非洲人認為較為或非常消極,贊成的觀點在馬裡(92%)、尼日(84%)和賴比瑞亞(81%)最為普遍。
很難從根本上改變當地貧困狀況的國家經濟援助,為什麼能夠在民眾當中獲得如此高的評價率,中國採取的方法是不斷研討新型援助方式,從最終援助效果倒推方法,力圖將援助與非洲公民生活領域緊密掛鉤,真正改善他們的民生問題,提高非洲各國的自主發展能力。
而不是去考察對方國家是否“尊重人權”。
眾所周知,以“人權問題”為藉口,從中“搞事情”,是資本主義國家最愛玩弄的把戲。日本援非原則中,就有明確的“關注發展中國家促進民主化、匯入市場經濟以及保障基本人權與自由的情況。
然而被“保護”的國民大多和我國的新疆棉農一樣並不會領情。
日本曾在1990-1996年,日本先後9次以民主、人權等問題為由,暫停對一大批非洲國家的援助,包括蘇丹、馬拉維、剛果(金)、獅子山、尼日尼亞、肯亞和甘比亞等國。
這其中的意圖,大家懂得都懂,非洲人雖然窮但不傻,打心眼裡也厭煩這樣一個彈丸之地對他們指手畫腳,只是迫於貧困的現實,只能寄人籬下,受人差遣。
同時,以第一產業為主的非洲與以第三產業為主的日本進行貿易往來,中間的貿易差以“援助”的形式進行補貼,也逐漸表現出不足,是誰想以低價掠奪原始資源,更是世人皆知。
這些還不是最嚴重的部分。
以“人權”干涉為代表的政治動因,與西方國家同樣,有意圖掌握非洲話語權,這樣的“政治滲透”才是最為險惡的。
有日本領域研究學者明確指出,日本顯然是想透過贏得非洲支援,塑造“大國”形象,進而推銷日本價值觀與發展模式,為其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拉攏人心。
在經濟方面,在東京非洲發展國際會議上,日本22家企業與非洲簽署了73項合作備忘錄,以此方式來攫取石油、礦產等資源,並搶佔市場。
在軍事方面,在南蘇丹以維和行動之名“鍛鍊”自衛隊,以實現“軍事滲透”。
相對於經濟援助,不如說日本是以金錢為砝碼,對非洲進行了全方位的掠奪,最終這”披著羊皮的狼“,終究還是沒能得逞。
同時,日本在近些年來進行的援助非洲的行動,有著明顯的“遏華色彩”,為此他們打出“高質量”的標籤,意圖諷刺中國對非投資質量低劣,無法在當地創造就業。
安培也在安全事務上激勵拉攏非洲國家,企圖在海洋安全方面合作,以此遏制中國。
這些都需要我們在對非援助方面多加謹慎,同時不斷最佳化對非援助的方式方法。
索性,直到2014年,中國對非貿易總額約2200億美元,是日本的7.5倍,國力發展的情況下,誰能夠穩定持續,誰最終鞭長莫及,不顧再過上數把年頭見分曉。
參考資料:《日本在非洲挑戰中國》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