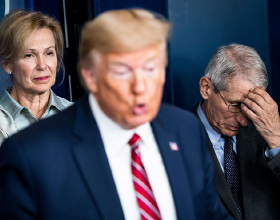中國搖滾教母樑龍:正是“不務正業”帶來無限可能
因為“美妝直播”意外在亞文化圈爆紅的樑龍,如今被越來越多的人熟知,與此同時,他所在的樂隊“二手玫瑰”這才被年輕一代所瞭解。
就像他歌詞裡寫的那樣,“前夜不忙後夜忙,夢完黃金我夢黃粱”,從保安到樂隊,從美妝博主到新晉導演,從藝術展到導師,樑龍擁有多重身份,不重合且精彩。
面對記者採訪問起他的不斷突破,樑龍回應:“因為生命太短了,我希望有各種嘗試。人生不是苦短,我們能幹的東西真的太少了,所以我想盡可能在這些裡面得到不同種的資訊量。”
就像他音樂裡唱的那樣,獨樹一幟的調子,誇張前衛的造型,搖滾且躁,唱盡了生活的本質,生命的沸騰。
也許這就是他的態度,不斷嘗試,不斷突破,不受年齡的限制,不受閱歷的捆綁,對生命和生活永遠保持熱愛和好奇,永遠願意探索和接受。
【一】
1977年10月18日,樑龍出生於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一個農村家庭,都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作為貧困子弟,他從小就比別的孩子更加理解什麼叫做生活。
樑龍很小的時候就在心裡埋下了走出去的種子,他想要去更大的地方,實現自己的人生夢想。
高中時期,樑龍開始接觸搖滾並開始學習爵士鼓和吉他演奏,美國涅槃樂隊(Nirvana)的搖滾樂傳入中國,這對樑龍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們用另類的風格進入了美國的主流文化,當時,還不到20歲的樑龍第一次覺得搖滾樂可以這麼自由,那個時候他的人生夢想開始從抽象變得具體。
可音樂的學習終究是個很燒錢的東西,家裡人沒辦法支援,樑龍只能選擇自給自足,就那樣義無反顧地朝著自己的目標努力,那個年輕人都想去的大都市,名字叫做北京。
年輕時誰不想看看天地,他渴望留在北京學習,更渴望留在北京生活。
1997年,只有高職學歷的樑龍為了攢錢去北京,在哈爾濱找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工作,開始當保安。1998年,他開始組建自己人生中第一支樂隊,“二手玫瑰”的雛形就這樣誕生了。
那一年,哈爾濱遭遇百年難遇的洪災,樑龍想都不想,就帶著樂隊扛著音響去松花江邊做公益演出,以慰問搶險官兵,他好像從來都是這麼一個行動力特別強的人。
舞臺是用沙子堆成的一個土堆,觀眾只有洪災中憂心忡忡地兵哥哥,雖然條件簡陋,但那是樑龍人生中第一次演出,也是那隻樂隊唯一的一次演出,當時他們唱了三首樑龍自己創作的歌,這支樂隊的開始即是結束。
因為和樂手發生爭吵,鬧醒了街坊鄰居,樑龍被炒了魷魚,工作沒了,樂隊也散了。
沒有錢,沒有工作,看不到未來和希望,樑龍決定不攢錢了,先去北京再說。1998年年底,他正式開始了他的北漂生活,那一年他21歲。
【二】
人在北京飄著,終是天不隨人願,夢想是美好的,可現實總是殘酷的,能怎麼辦呢,總得先填飽肚子呀,沒有學歷也沒有江湖地位,不出三個月,樑龍再次不得已的回了老家。
父母當然是希望孩子能有個穩定的工作,有個看得見的未來,可他想要做的事情在別人眼中有多“不務正業”,他就有多認真。
1999年開春,樑龍第二次來到北京,為了養活自己和夢想,他一去就先找了份簡單的工作,不需要收入很多,只求能混口飯吃。
他就那樣一邊打工一邊創作,後來的採訪中,樑龍說自己當時是真的享受創作過程,其實他也不是很專業,但創作的慾望總是澆不滅的,要說一開始的風格呢,其實也沒什麼核心,只不過用心去做。
有一天,他拿著自己的磁帶去北京東二環的一家錄音棚去錄歌,中途把磁帶放在桌子上去了衛生間,出來就聽到那個DJ跟朋友講他的磁帶,原話是“這叫什麼音樂?我給你聽人家這次才是音樂。”
隨後,那人放下他的磁帶給朋友放了那首《野孩子》,這是樑龍第一次在音樂上受到打擊,原來他做的東西在別人眼裡什麼都不是,他心灰意冷再次回到老家。
就算找不著北,可他並不想去模仿,他希望保留自己的原創性。但這次的返鄉給他的音樂帶來了方向,老話說得好,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他驚喜的發現在老家這種沒有鋼筋水泥的地方,天地廣闊,人與人之間善良互助,人情味兒催化了他的音樂靈感,讓他做出來的音樂不受任何東西的感染。
偶然間認識的農民蘇永生,可以說是樑龍重新開始的指路人,蘇永生吹拉彈唱什麼都會,鍵盤、嗩吶、笛子無一不精,村裡的紅白喜事從來都少不了他。
那時候的樑龍還沒有民族音樂的概念,在蘇永生家裡的那三個月,他寫出了自己的成名曲《採花》。
信心被找回來了,身邊又有了蘇永山這麼契合的夥伴,樑龍決定再次開始組建自己的樂隊,於是“二手玫瑰”就這樣誕生了。
反觀自己的北漂經歷,“二手”多多少少有些反諷和警惕之意,而“玫瑰”則是表達濃烈的愛和感情,前兩個字是樑龍對自己的反省,後兩個字則是他對音樂的寄託。
今年的《明日之子》大火,又讓另一批年輕人再次認識了一個全新的樑龍,在第一期,他就曾說,我的樂隊叫“二手玫瑰”,但音樂必須是一手的,做搖滾樂,他從來都是認真的。
【三】
1999年年底,哈爾濱舉辦第二屆搖滾音樂節,音樂人誇他們玩兒的東西很新鮮,市場上沒有出現過,於是“二手玫瑰”順利的迎來了自己的第一場演出,此後便一發不可收拾。
19天時間寫出了10首歌,這樣的激情再次觸發了他想去北京那根線,可好像這樣的激情也只有他有,其他樂隊成員有的在農村有穩定的工作,有的窮的豁不出去,只想呆在家鄉好好過日子。
就這樣,“二手玫瑰”再次面臨解體,只有樑龍一個人踏上了去北京的征程,而這次,將是他命運發生翻天覆地的一次。
不要輕視任何人的努力,因為所有的付出和堅持都不會辜負你我,樑龍第三次來到北京,遇到了他的第一任經紀人佳偉,佳偉幫他找了專業的團隊,“二手玫瑰”終於走上了正軌,這次的配置是樂隊第一次完整的配置。
可是好景不長,2001年魔巖唱片在國內撤資,“二手玫瑰”與佳偉的合作就此終止,樂隊又面臨解散的風險。
當時的樑龍著急找第二任經紀人,於是他遇到了生命中第二個貴人——黃燎原。“二手玫瑰”正式簽約北京藝之棧。
這次的合作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突破,“二手玫瑰”做了北展的演唱會,在當時的搖滾樂圈兒裡,算是真正的火了。
領導說他們是第四代第一個在北展做演出的樂團,說他們的音樂有不可替代的獨特性,鼓勵他們好好弄,堅持下去。
可搖滾樂圈子裡總是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經歷過大事情反而更容易傷了根本。
當時的樂隊成員大勁曾經跟竇唯合作過,王鈺琪是個小年輕又懂流行音樂,他們辦了大型演出之後卻變不了現,大家覺得樂隊沒有成長,搖滾樂看不到希望,好像做來做去也只能是那個樣子。
這次北展的演出讓樂手們更清楚地看到了問題,解決不了,“二手玫瑰”只能再次解體。
經紀人換了好幾個,樂隊成員幾次大換血,堅持下來的只有樑龍,“二手玫瑰”樂隊的演出費終於一次比一次高,名氣也越來越大。
東北二人轉的戲曲元素與現代搖滾樂不露聲色的嫁接,誇張的表演和樸實戲虐興奮的聲音,能感覺得到在北京的眾多搖滾樂中,“二手玫瑰”總是技高一籌,他們的潛力足以超越北京那些朽木般的老搖滾樂隊和他們同齡的新人。
在京圈紮下了根兒,“二手玫瑰”有了屬於自己的江湖地位,樑龍被稱為“中國搖滾教母”,對此稱號,他後來還自嘲,說中國的搖滾樂教父太多了,所以自己是“教母”。
【四】
名氣也有了,吃穿也不是問題了,樑龍那顆喜歡折騰的心又按捺不住了。
2015年,樑龍在北京凱德學府做了“紅配綠”的藝術展。他本人闡述:“本次展覽想表達的是人在生長與迴歸這兩條並行線之間的順從與背叛。”
對於藝術,他一直都有自己的追求。
後來新招進團隊的年輕人帶他走進了新世界,建議他去做美妝直播。樑龍稍一瞭解,發現那個叫李佳琦的男人賣個口紅都能月入過億,論起男人化妝他也算是祖師爺了吧,這下子心裡怎麼能服氣。
結果一開直播,他突然就在圈子裡爆紅,《吐槽大會》的舞臺上,他笑著說自己做了20年搖滾才攢了30萬粉絲,可開直播兩個多月就漲了7萬多粉絲。
但好的方面是,無論從哪個地方粉上他的人,都會去了解他的音樂,只要搖滾樂或者說民族音樂被越來越多的人認可,那都不失為一件好事情。
這還不夠呢,對生活充滿熱情的樑龍怎麼會辜負“不務正業”這個詞,就在大家以為他只是音樂導師兼老年美妝博主的時候,樑龍又突然在華語青年電影節2020“獵鷹計劃”創投年度的前35強名單裡出現。
這回可是把眾人嚇了一跳,電影專案叫《大命》,確鑿無疑的是,“二手玫瑰”的樑龍,搖身一變成了新晉導演。
其實樑龍與電影的緣分一直沒斷過,他也曾飾演過一些角色,比如《讀城記》裡憂傷的男人、《回南天》裡神秘的龍老師、《父子雄兵》裡兇狠的狗哥......
除此之外,他還做過很多電影配樂,並因此走了金馬紅毯。
【五】
在《大王酒館》裡,樑龍和臧鴻飛聊藝術,他說他希望音樂有收藏性,而藝術缺乏公共性,所以希望當代的好音樂,獨立音樂可以和藝術文化有機的融合在一起,使獨立音樂更加走入當代並且具有收藏性;而當代藝術也能更加鋪展開來,具有公共性。
聊到導演這個身份,他說自己其實對演員沒什麼興趣,不是特別想去塑造某一個特定角色,但一直有一個導演夢,並且一直覺得自己可以拍,只是之前比較懶。
他說,前兩年突然發現自己的記憶開始消失了,有些細節變得越來越模糊,而曾經聽到的一個詞“記錄”給了他很大的啟發。
他認為生存方式或者藝術表達就要有記錄感,而影像是最直觀的。
無論是這些年臺上誇張的造型和表演,還是臺下折騰不息奮鬥不止的點滴,那都是樑龍生命中不可或缺的。
臺上是壓抑已久的瞬間表達,臺下更多的是閱讀感,樑龍說自己沒有太多表達機會,在生活中也只是站在觀察者的角度。
正是這些年的“不務正業”造就了後來每一個綻放的瞬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