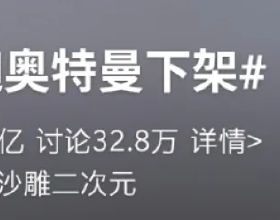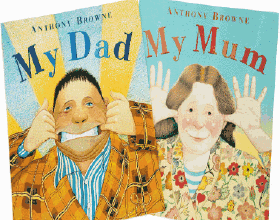■薛衛民
收在《遇見狐狸的小老鼠》裡的作品,都是從第二屆接力杯金波幼兒文學獎徵文中精選出來的。我想,這裡的每個作家當初決定參賽時,大概都有與我差不多的想法:這是一個專門為幼兒文學設立的獎項,以一位令人尊敬的中國作家的名字冠名,由一家多年來既腳踏實地又勇於開拓、既求真務實又引領風騷的出版社承辦,它有理由被矚目、信賴和期待。
長大和成長,不完全是一回事。幼兒長大並不天然地等同於成長。幼兒需要成人世界哺育。物質的“哺”和精神的“育”都好,幼兒才會既長大又成長。幼兒文學是一個具有獨立性、獨特性的文學體裁,這樣的意識不是自古就有的,就是在今天,它可能還是一個需要不斷普及和建設的意識。推動這個獎項的人們一定深知中國幼兒文學的任重道遠,深知所有功在當下、利在千秋的事業,都需要俯下身去紮實地做。
幼兒文學篇幅小、體量小,別的都不小。它豐富而又遼闊。
能夠走進幼兒世界的作家,再去進入大孩子、大人的世界,會發現遠比反向的進入容易得多。世事洞明可以學,天真清澈學不來,只能模仿。
小樹、小苗只要不夭折,大起來是自然而然的事。同樣,讓小人兒變成大人,交給時間就行。可大起來的人再想小回去,小成幼兒、嬰兒甚至子宮裡的胎兒,可能嗎?
小回去的不是肉身,是心理。走的不是物理旅程,是心理旅程。
每個人都在夢裡回過自己的童年、幼年,回過那座讓自己感到無比安全、無比溫馨、無比幸福的神奇宮殿。至少在夢裡,我們都走過那樣的心理旅程。
幼兒不用做那樣的夢。幼兒也不把夢與現實加以區分,他們的想象和現實沒有邊界。你認為他在“說謊”的時候,其實在他看來那是陳述事實;他說他是小貓小狗的那會兒,他真的通獸性;他說他是小花小草的那會兒,他真的在生產葉綠素和釋放大量的氧氣。那是成年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
為什麼“大”了還想再“小”回去?根源可能就是人類進入文明之後,一直都面對和思考並將永遠面對和思考下去的:我從哪裡來,我到哪裡去。對此,哲學家有持續的興趣,小小幼兒也有持續的興趣,從土裡刨出來的、從垃圾箱撿來的,只能矇混過他們探究的初級階段。
“到哪裡去”都是未然的,不具有實證性。而“從哪裡來”都是已然的,具有可溯性。
就像數學中用已知探求未知一樣,小回去,小回到幼兒、嬰兒甚至胎兒,巡視、檢視、審視自己走過的生命旅程,不僅能給自己以心安和慰藉,更能給“到哪裡去”以激勵和滋養。“從哪裡來”往往被冠以“理性”之名,其實它更是美學的和詩性的。美學和詩性,在一個人生命的厚度和幸福的濃度裡。
寫幼兒文學的人、幼兒文學作家,大概都是“小回去”的願望特別執著和強烈的人,因為那是創作幼兒文學的基本功課。他們同時又都是訓練得自己具有“小回去”之能力的人。既有執著和強烈的願望,又能得益於天賦和訓練,具備相應能力的人不多,因此,幼兒文學作家,永遠都不會像非洲大草原上遷徙的斑馬群那樣浩浩蕩蕩。
兒童文學以及其他一些文學,都有可能是兒童自己寫出來的,但幼兒文學不行,幼兒文學都不是幼兒寫的,都是長大了的成年人寫出來的。他們是一些自己不再是幼兒卻能經常回到“幼兒”的人,對幼兒的成長過程充滿著好奇和興趣的人;他們體認幼兒的喜怒哀樂、心理挫折,並且還能將其有效地捕捉到,很好地表達和表現出來。於是,有了幼兒文學。
僅僅因為幼兒文學,便使人類的幼兒既像其他動物的幼崽,又並不等同於其他動物的幼崽。人類“幼崽”從牙牙學語時便被傾聽,他們的心理健康時刻受到關注與呵護,幼兒的語言和思維能夠及時得到母語的沐浴,將為幼兒日後走向文字的世界奠定品位和格調。動物也有語言,但它們沒有文字,文字才標誌著文明和文明的高度,對一個民族和個人來說都是如此。養育幼兒的父母,從事幼兒教育的職業人員,從幼兒文學那裡得到增援;“從哪裡來,到哪裡去”不再僅僅是深奧的哲學,也是淺顯的、形象的、幼兒自己也能感知到的情景和過程;如果調整和最佳化相應的情景和過程,幼兒文學會讓“大人”們的努力方向更明晰、作為更恰當。
幼兒文學的“小”,因此與子宮裡一枚受精卵的小,互相輝映。
一粒種子。一枚卵子。所有的鮮花怒放,森林浩瀚。所有的男人女人,人類生活。
與其他文學一樣,幼兒文學也要有思想的核、理性的謹、文辭的魅,只是它的思想之核更講究大道至簡,它的理性之謹包容萬物有靈,它的文辭之魅更像尚未成器的蓬勃野樹。大道至簡的“簡”、萬物有靈的“靈”、木未加工謂之樸的“樸”,簡、靈、樸,在幼兒文學中最為飽滿和充沛。
它如元,如一。
《遇見狐狸的小老鼠》,薛衛民、沈習武等/著,接力出版社即出
來源: 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