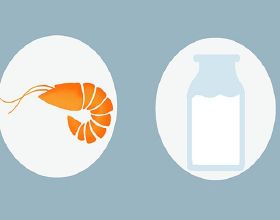她死於55歲的豔陽初秋
我不清楚她的名字,與她從未有過交集,只是母親常常唏噓她的人生經歷,唸叨的多了,她與我彷彿就是一個久未謀面的老朋友。
最後一次聽到她的訊息是在她死的第二天
父親載我路過老家的村子,我斜倚著車窗,眼睛于飛逝而過的窗外景色中,瞥到了一抹白,耳朵也瞬時聽過窗外傳來的哀樂聲,我問父親是誰沒了,父親說是她。
回家我與母親說起這件事,母親也呆住了很久,再一次向我講起她從前的故事。
她年輕時大抵是個美人吧。我年少時不多次的見她,也能從她暗黃的面板、細碎的皺紋當中窺見她五官的美麗和年輕時的風姿。
她年輕時肯定是一位美人,不然,大家談起她來總逃不開“高嫁”二字。一位沒上過幾天學的農村少女能嫁給一個吃國家糧的人,實在是村裡人人豔羨的高嫁。
她的丈夫我也見過,身高與相貌皆遜於她許多。在農村中行走,永遠都是白襯衣,西裝褲和一雙黑皮鞋,戴著眼鏡,文質彬彬卻又趾高氣昂。
我始終不明白她這一生的悲劇,究竟是因為高嫁二字,還是無論嫁給誰,結局都是如此。
她幸運地出生在一個獨女家庭,家中兄弟三人,父母只得她一個女兒。父親能幹,兄弟出息,在那個女性毫無地位的年代,她比村裡其她的女孩兒們有著更多的父母疼愛。雖未上過幾年學,但也沒有幹過太多農活。沒有被日頭曬過的白皙面板,端正的五官以及一個較為優越的家庭,她的婚姻自然也與村裡其它黝黑粗糙的女孩不同。用父母那輩的話說,她是嫁給了端鐵飯碗的人。更讓別人羨慕的是,她的外村丈夫不知用了怎樣的方法在村裡得到了一個宅基地,蓋起了二層小樓,也是村裡為數不多的樓房。
她剛結婚時也是神采飛揚的吧。從小就是同齡女孩中的佼佼者。結婚後,她更是與那些村婦們不同,工作體面的丈夫,闊綽的生活,滋潤的日子,他的臉上總是帶著甜蜜的笑。
可是生活並不是只有甜蜜,她的苦澀藏在笑容之後,隱藏的極深,又十分顯而易見。與她同時期出嫁的小夥伴們抱著孩子回孃家了、晚她一年結婚的弟媳婦兒肚子大起來了,她還是沒有訊息。苦的要命的湯藥,她不眨眼的吞了一碗又一碗一。母親為她找的偏方,藥引是生壁虎,她拿過來就吞下......苦頭吃了一籮筐,卻依然腰身纖細。
山裡的婆婆一趟一趟的到鎮上來,先是委婉含蓄,又是暗暗諷刺,最後破口大罵。
沒人知道她婆婆罵了些什麼,她是個驕傲的人,從不肯人前示弱。鄰居說,每次她婆婆來,她都要費力做一大桌子菜,飯點過後就聽見隔壁聲音越來越大,在她低低地啜泣聲中夾雜著不下蛋和絕後之類的字眼。
她臉上的紅光褪去了,她嘴角的笑容消失了,她滋潤的面板乾枯了。
最後讓她絕望的是一張又一張醫院的檢查單。我不知道具體病症是什麼?只是偶爾路過老太太們的茶話會,聽她母親感慨過一句“但凡能治,哪怕傾家蕩產”。
她的婚姻大概是從這開始不好的。“鐵飯碗”丈夫要跟她離婚。
她堅決不離,不知是捨不得如此優渥的生活,還是認為自己一個無法生育的女人離婚之後再無後路。當年的風波鬧得很大,鬧了很久。不知為什麼她的丈夫最後偃旗息鼓,聽說是她能幹的兄弟,找到了姐夫工作上的錯處,問他是要工作還是要離婚。為了“鐵飯碗”,他屈服了。
他屈服於飯碗,但並未屈服於自己此生不能有後的命運。從大人的閒言碎語當中,也能瞭解當時他為了不臣服於命運的各種事跡,但當年的那場離婚風波鬧得十里八鄉人盡皆知,又有誰會為他一個不能離婚的男人而孕育後代呢。所以他空折騰了十年,出了一堆桃色豔聞,卻也沒有折騰出一個孩子。
後來他好像是屈服了,不知從哪裡抱養回來一個剛出生的男孩,瘦骨嶙峋又生機勃勃。小孩滿月的時候我媽作為親鄰去吃桌。凜冽的冬天,她在院子裡,在冰冷的水中,洗著成摞的碗筷,笑容客氣,神色平和。
我媽上前對她道聲恭喜,她機械地笑著,紅著眼睛說“嫂子,你不知道我內心的苦呀,說都沒地兒說”。
大家紛紛勸她,如今有了孩子,你的人生也是有了希望,日子也是有了盼頭。孩子剛出生,你就養著,你就是他親媽。你好好地養他,以後有人給你養老,等著你的都是好日子!她擦了擦眼睛,低頭笑笑不再說話
她是真的很用心在養育這個孩子,腳踏車後座上鋪了軟軟的墊子,安裝了小孩可以做的小籃子,不管她走到哪裡都帶著這個孩子,像眼珠子一樣地看著他。
風言風語再起是在兩年以後,村裡人驚訝地發現,孩子跟她的丈夫越長越像。在幼時,人們總是調侃“果真誰養的孩子跟誰長得像”。隨著孩子的長大,再也沒人敢說了,抱養的孩子有一分兩分像她的丈夫是緣分,可是這八九分的......
後來訊息漸漸傳開,隔壁村在集上賣乾貨的那戶人家,家裡的媳婦兒肚子總是大了癟,癟了又大。只見大肚子不見小孩子。有訊息靈通的說那家媳婦兒就是專門給人生孩子掙錢的,家裡的那棟三層小別墅就是這樣蓋起來的,事先約好錢款,約好男女,生完之後銀貨兩訖。那個所謂抱養來的兒子,就是鐵飯碗跟那個小媳婦兒生的。
我母親和街上的嬸嬸們知道這個訊息時感慨唏噓了許久,她們終於明白為何她當時說出心裡的苦,不知如何向人說的那句話。
世人愛熱鬧,愛八卦,但沒有長性。
日子長了,大家也就不再討論小男孩的身世了。村裡人就這樣,聒噪好事,卻又善良。大家都是由衷的希望她能過得輕鬆幸福,就像以前一樣。
後來我們一家搬離了老家的村子也失去了她的訊息。
一次父母回老家賣樹,她過來同母親敘舊,並詢問地上的這些枯枝,能否讓她拉回家中燒柴。母親調侃她說“你如今也是會過日子的人了,放著天然氣不用要去燒柴”。父親在旁邊拽了一下母親,母親知意立刻閉嘴,抬起頭看,她的神色略微有些不自然。幹樹枝很多,她的三輪車要來回四五次才能搬完,地面坎坷不平車上的樹枝又橫七豎八,她只能賣力地推著車子向前走,春末的傍晚,整個人汗如雨下。說來也巧,我父母幫她把樹枝運回家時正好遇到了她午覺起來的丈夫。
父親說,她的丈夫在外面自在慣了,這十幾年的荒唐不是朝夕之間能戒得了的。這次不小心在外面惹出了亂子,將大半家產賠了進去,就剩下了這棟宅子。屋漏偏逢連夜雨,幫朋友貸款擔保,朋友跑了。銀行凍結了工資每月只發幾百塊錢工資度日。如今她們家都要靠她在敬老院做飯得到的報酬生活。現在的她過得比往常更要辛苦。
後面我再得到她的訊息,就是那天路過村子時她的死訊。
第二天,母親去了葬禮,送她最後一程。
回來時母親告訴我,她精心養育的那個小男孩現在已經長得很高很壯了,過幾天就要去上大學。他跪在靈前,誰同他說話都不理,只知道呆滯地流淚。
母親說,她死於乳腺癌。身體早有反應,她怕花錢一直拖著不去醫院檢查,確診時已是晚期,沒有治療的必要。
母親說她這一生都是滿腔苦痛不得開口說,氣鬱於心,集結肺腑,活生生憋出的癌
母親說,她兒子很愛她,她的一生辛勞總算有些許回應。
母親說了很多,我全然聽不下去。
我問母親,她這一生做錯了什麼,命運要如此苛待她。母親無言,她無法回答我。翻來覆去的唸叨著,好人不長命,好人不長命啊。
是啊,世間好人多苦難。
不要做好人,做個快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