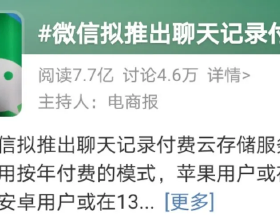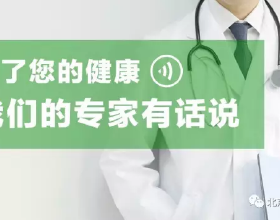咱們去捉魚
“何屁蟲,今天咱們去哪?”
小織蕩著河裡的腳丫,任清澈的河水吞噬著白嫩的腳趾,洗去娃娃渾圓的稚氣。
何屁蟲抱抱手:“捉魚咋樣?”
何屁蟲為什麼叫何屁蟲呢,他本名叫何小,說話總逗大人開心,比如今天誰家媽媽在街邊理髮店燙了新頭髮。他總一眼能看出來,會熱情的跑上去用甜甜的聲音說某某阿姨,頭髮可好看了,像年輕了十歲! 阿姨總會笑著說:“哎喲,小嘴真甜!”我們小孩子不關心大人的事情,他總跑上去問個究竟。那時候我媽媽總讓我學學他,口才多麼好,將來絕對有出息。我們別的小孩子都說,父母都對他們都這樣說,於是我們對此嗤之以鼻,暗地裡說他是個馬屁精!所以他的外號就這樣誕生了。
那時候的夏天,一群孩子在熱烈的陽光下奔跑著,任汗水從曬得發紅的脖子上滑落。平常他們會到河裡捉魚,而現在這個季節,他們最愛去小知那裡玩,因為,小知住在一個農村修建的土房子,一共有兩層,小知住在二樓,頂樓是一個大水塘,裡面是一樓人家養的小魚,夏天炎熱的時候總會下一場彩虹雨,來平息這股熱氣。池塘裡的魚就被溢滿,像順著天上的彩虹流下來,掉到旁邊的水泥地上,或者房子後面的田壟上。陽光下,蹦蹦跳跳的小魚像銀花花的小刀在跳舞,孩子們就拿著統一的小紅桶在下面撿魚,小知和何屁蟲更是爭著搶著最大的,最好看的魚兒。“喂!小知,左邊好大一條。”我猛的回頭,“對對!”一樓的叔叔粗著嗓子喊。他笑呵呵的,汗水順著額頭深深的抬頭滑落,笑起來時,又在眉毛處滴落。紋黝黑的脖子上搭了一條白色毛巾,時不時用來擦汗,翹著二郎腿坐在小板凳上故意說哪裡哪裡有大魚,好看我和何屁蟲爭搶。
何屁蟲在那個時候很外向,啥事都衝在前面,經常帶我上山摘果子追野雞,特別是抓魚。有一天早上吃完早餐,我們約好下午放學去河裡抓魚,但上課時,他被老師叫出去沒回來過。這一天兩個孩子的約定,變成了我一個人去河裡玩耍。從這天起,他變得不愛說話,曾經的跟屁蟲變得不愛找我,我找他他總是避而不見。我不死心,以為他和我躲著玩。我在他家樓下大喊:“何屁蟲咱們出去玩呀。“喂~”
”喂~”
我的聲音在院子裡迴盪,從圍牆外探進來的樹葉都微微震動。我在圍牆上拖著腮幫子,不知疲倦的喊。他的媽媽過了好一會兒從窗戶掀起藍色簾子一角,頭髮凌亂的披散著,浮腫的臉上帶著淚痕,她輕輕對我說,小知快回家吧,何小不在。我愣愣的點了頭,她媽媽就轉身回屋了。我不相信何屁蟲不在,於是我像貓咪一樣弓著身子悄悄翻過圍牆,簡直小菜一碟。扒開那扇窗戶簾子的一條縫隙,看見了令我震驚的一幕,何媽媽從低聲的啜泣,開始用手又掐又打何屁蟲,嘴裡伴隨著咒罵和哭喊。何屁蟲稚嫩的手怎麼經得住打,何媽媽的手落下去在起來時就會出現一個紫紅的印子,何屁蟲緊緊抿著嘴唇,沒有哭泣,一言不發。看到這,我害怕的翻出他家院子,我沒有看到何媽媽這樣過,好像和平常不太一樣,直到我回家時候,才從父母聊天中得知,何小爸爸在幾天前,有急事騎摩托車去隔壁村的時候,村路溼滑泥濘不堪,出事故人沒了。
我不明白,不理解生死的含義,年紀尚小的我懵懵懂懂。每天和我上學的何屁蟲沉默不語,他時常一個人背對著我看藍藍的天空,作為朋友的我也跟著難過。我想讓他心情好一點,就我問他我們去哪玩,他都會說,我不想去。我們不再抓魚,不再上學放學途中中打鬧,漸漸的,何屁蟲這個暱稱。只有我的跟屁蟲的意思了。他話多嘴甜的何屁蟲“消失”在兒時的那一天,他蛻了一次殼。長出了更堅硬的盔甲。變得靦腆起來。不像以前大大咧咧,越長大,做事越溫柔而謹慎。我們逐漸變成了兩個極端,我依舊是那個小知,做事時來雷厲風行。現在我們都長大了,我不滿小縣城低工資,跑去了大城市打拼。頑強的生存和打拼。只是不知什麼時候起,每次單位朋友聚餐,我總是第一個起來敬領導,對他們說這條領帶太適合你了,必須很貴吧?您是我的偶像。或者是如果誰能在你的手下工作,天天得到這麼多鼓勵和讚美,流再多的汗也無怨無悔。
而此時的何屁蟲留在當地當了一位中學老師,每日平平淡淡。卻也樂在其中。他和我仍然是好朋友,和村裡兒時的夥伴也常常聯絡。何小的媽媽和我的媽媽走的十分親近,並讓我的媽媽告訴我,她想撮合我和他兒子。過年時回去,她媽媽笑呵呵地拉著我的手說:“這姑娘和我兒子性子互補!合,合!”何小在旁邊尷尬的看著我。即使我們沒有這個意思,她媽媽也會當作沒看見。
有一次單獨出去走走時,漫步在青苔佈滿的臺階上,我問他,談戀愛了?他不好意思的笑笑,“對,是隔壁村的。”說著,用鞋底去撥弄青苔。“可以啊何屁蟲,談戀愛都在我前面了,叫什麼名字?帶來見見?”“會有機會的。”為了讓村裡夥伴都見見,過幾天何小就安排了一次聚會,村裡發小都在,吃飯時大家都不怎麼調侃,因為他的女朋友也是一個文靜靜的姑娘,紅著臉,跟在何小身後,給何小端水遞紙巾。我對他女朋友的第一映像就是一個不爭不搶的女孩,和何小性格差不多,兩個人在一起,大概過得會很安穩甜蜜。我們散場時我拍著他的肩膀笑嘻嘻的說:“好好對人家。”他看著姑娘的臉,輕聲說:“會的”
一年後,我和我媽微信聊天,她問我為什麼還沒有物件,我說不急,她說人家何小都要結婚了,叫我回去看看。而且村和隔壁村的土路即將被政府出資修成水泥路。聽到這條訊息,我有些難過,畢竟,何小的爸爸在那裡出過事,不知道他會怎麼想。聽到這些訊息,我提前請了假,從大城市回到這個小縣城,我先去看了那條正在修的水泥路,已經修了一半。回家一路上我都在想,他的日子已經好起來了,現在,他的朋友圈都是他和他女朋友的點點滴滴,這些幸福是藏不住的。在結婚前一天晚上,我們幾個發小喝的醉醺醺,她媽媽走過來和我打招呼,當著幾桌親戚朋友說:“”還是看著小知順眼,你們瞧瞧,多漂亮的姑娘,有獨立能幹。”我尷尬的笑了笑,希望酒席上的人都喝醉了,特別是新娘。我朝她看去,這會,紅紅的臉蛋靠在何小肩膀上,小何溫柔的看著他,手臂小心翼翼拖著她頭。我鬆了一口氣。
有些事情,我們是不能知曉未來的。
第二天何小半夜開始準備,在第一束陽光落下來時,我們一起長大的夥伴臉上都帶著紅暈,高高興興出發去接新娘,在回來的路上,出了車禍,在那條水泥路上。新娘在右後座當場死亡,是一輛拉水泥的大貨車側翻,正好壓在新娘身上,一個車的何小和駕駛員,一點事也沒有,大貨車車主下來跪地痛哭。可是,哭又有什麼用呢?何小沒有哭,他呆呆的望著新娘。這朵嬌豔的花,被抽取鮮紅的汁水,毫無生機,沒有枯萎凋零,而是突然整朵掉落。一瞬間沒有了生機。到現在,我對生死的含義多麼深刻!生命之花,之所以永開不敗,是因為它是存在的過程鮮活有力,經歷了多少滄桑。生命之花,當他凋零時,沒有血肉只有靈魂。所有的顏色都變成灰色,暗淡無光。
我們後面的車聽見前面的撞擊聲趕緊趕來,一路上何小媽媽都在哭喊:“命啊命啊!我都說了你和他不合適。肚子裡的孩子不一定是你的!看老天爺看不下去了!”她邊哭邊捶打兒子。何小被媽媽推搡一下子坐在地上,沉默不語,雙眼無神。和當初他父親離世時狀態一樣。我們幾個發小面面相覷,卻無能為力。我這才知道,他的媽媽是有多麼不喜歡兒媳婦。那個文文靜靜的姑娘,而且這場意外,原來是一屍兩命。
後來的何小一個人養他亡妻的老人,和他一直相依為命的媽媽。身上穿的衣服也變得皺巴巴,洗得褪了顏色。肩膀越來越厚,面板也越來越粗糙。這些事,逼著他成長致此,讓他憔悴,但是沒有摧毀他。我在城市逐漸穩定,今年夏天回老家,我打算把父母接到我所在的城市,順便來看看何小,力所能及的幫他,陪陪他。到的當天喊他來我家喝酒,我們在小紅桌上喝了幾杯酒,看見他把酒杯拿起來喝了一口,又重重的放下。我忽然聽見他哼起一曲悲傷的調調。不只是因為酒的辛辣還是往事的苦澀,他的眼眶紅了起來。“你說,生活為什麼沒有撤退這一步?”
“…”我不知道該如何安慰他,只好給自己倒了一杯酒,一飲而盡。
“出去走走吧。”我說。
田間的小孩光著腳奔跑著消失在金黃的油菜花裡。我和他並肩走在田間。他過舊的襯衫被風吹得鼓鼓的,在陽光的籠罩下生機勃勃。突然,雨下的很大,我和他又回到我家屋簷下躲雨,等著雨過天晴。果然不一會兒,雨勢小了,渾圓的小雨點在油菜花裡跳躍,突然,天上有魚兒掉下來。我和何小抬頭望去,銀花花的魚兒在刺眼的陽光包裹下,從樓頂跳落。我恍惚了一下,記憶和兒時重疊。
“何屁蟲,今天咱們去哪?”
“捉魚,怎麼樣?”
我們相視一笑,卻發現對方眼中都噙著淚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