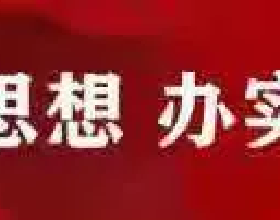衰老如入冬,漫長持久,冰凍三尺。死亡不是抗爭,而是單方面的殺戮。
《最好的告別》這本書我推薦丁克朋友看看。
書的作者說:“死亡通常是一連串毀滅的過程,本質上會使死者的人性崩解,在我見過的死亡中,有尊嚴的並不多。”“要使老年人的生活變得更好,需要抵制干預、修復和控制的衝動”。
如果只是追求延長時日,當然可以大量運用各種藥物和療法,在病人體內狂轟濫炸。卻忽略了患者對尊嚴和生命完整性的需求。
母親從患病到去世的全過程我陪護左右。
她被診斷出自身免疫性肝衰竭。接下來一個多月的時間,她從臉色蠟黃的衰弱中對我交代遺產的事,把身上的首飾摘下來給我;到肝性腦病出現神智不清的症狀,對我最好的媽媽,逐漸認不出我,甚至朝我及病房裡的人破口大罵;再到無法進食,無法排便,需要插食管、導尿管、曾經愛乾淨的她只能被剃成光頭,靠別人給她擦身體,依靠藥物才能排便,在床上。尿不溼、墊單輪換著用。抽了兩次腹水,穿刺,抽水,束腹,肚子還是鼓了起來。
病房裡充斥著消毒水的氣味和病人的哭號。一晚上護士來六七次,大概每隔一小時就來,測體溫,送藥,換輸液瓶,測血壓,抽血,每次來就哐地推開門,開啟所有的燈,或許她們也有夜班火。反反覆覆折騰就到了天亮。身體健康的我在病房陪床的第一晚就得了中耳炎。何況本就虛弱的重疾患者。
每次治療前後,要抽十幾管血檢查。因為手已經抽不出血,就抽大腿根的動脈,抽得大片青紫的淤血,她離世的那天下午醫生還要抽血化驗,被我阻止了,治不好,就別遭罪受苦。
從那時開始意識到醫療的侷限性:“有時治癒,常常幫助,總是安慰。”對死亡的恐懼和無助同樣是常態。“久病床前無孝子”是大機率。
BBC 紀錄片 《我死前的最後一個夏天》中一個身患絕症的女性選擇了在生命接近終點時放棄姑息治療,拒絕拍攝,擁有生命尊嚴地離去。
到底是應該體面地退出,還是痛苦地熬到最後?生命的延長和生活的質量哪個更重要?是需要抉擇的。
對我而言,在絕境下擁有質量地短暫生活,遠比受盡折磨地延續時間更具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