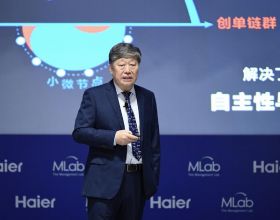1.
立秋過後,我常夢見他,夢裡他穿著純白T恤,一副喪家狗的模樣,手上沾著血。他望著她,她像夏花一樣怒放。我不知道她看到新聞時的表情是像突然散落一地的海棠?還是像被風吹落的葉子、踩在腳下清脆的一聲嘆息?
我在網上查了很久,至今沒有看到一審結果。我希望至少是無期徒刑,這樣我還能去看他。他一定還在解那個“四色問題”:為什麼地圖上只需要有四種不同的顏色?——而社會上卻有形形色色的人?這後面一個問題是我的追問,不曉得他在鐵窗後會不會也這麼想?
但我總是擔心,畢竟他殺的是學院書記,有頭有臉的人物。死者家屬恐怕不會輕易放過他。留給他的時間也許不多了,我不知還能否再見他一面,把他畢生的成果從鐵窗後面帶出來。
或許他會淡淡地說:燒掉吧,沒有價值,都是廢紙。就像我寫給她的信。
他最後還是沒有寄給她——那是厚厚的一本書,裡面全是寫給她的信。那時他們已經分手,我幫他仔細修改過,就在我要把這封長信改好時,她結婚了。我告訴他時,他就像秋天裡的第一片落葉,倏然無聲。
他是數學天才,語文白痴。寫那些信費了許多時間——而平時他連看個電影的時間都捨不得,一有空就解那個“四色問題”。有一次在飯桌上,她一臉天真地問,如果“四色問題”解決了,全世界的地圖是不是要重新印刷了?他笑著搖頭,說不太可能。我說,沒有誰會在意的,除非真的遇到需要五種色的情況。他立即一臉嚴肅地說,我認為所有的二維地圖都只需要四種色,雖然我還沒有證明出來。我笑了笑,說美國數學家好像用計算機證明出來了?他搖搖頭,說,沒有。不管我們看到多少隻白天鵝,都不能證明所有天鵝都是白的。我不知怎麼接話。氣氛有些尷尬,她連忙轉移話題,聊起了一家店裡的烤鵝肉,眯起眼睛笑著露出一對酒窩,問我們什麼時候一起去吃?我說,等陳老師把四色問題證明了,全世界的記者都會來採訪我們,到時候想吃啥就吃啥。他皺了皺眉,說也許我這輩子也證明不了,所有的草稿都會成為廢紙……
我已忘記,後來他們有沒有一起去吃烤鵝。我只記得他母親去世後的一晚,他一個人坐在那家店裡,我走進去,發現他沒有吃,呆呆地看著前面玻璃上細微的雨絲,眼底有許多血絲。那晚我才得知他們分手了。
剛聽說他倆談戀愛時,我有些意外,畢竟李曉還算漂亮。當然,陳老師長得也不差,臉很白淨,瘦高個子,但他老實木訥到有些“無趣”,而且家境差。大學老師收入不高,根本沒有在杭州買房的希望。
我是在學校踢球時認識他的,他話很少,總穿一件純白T恤,是個不起眼的後衛,拼搶非常積極,但是技術一般。如果不是有人告訴我他在金大讀過,我應該不會記住他。後來有一天在學校食堂吃早飯時,我看見他一個人在吃飯,就湊上去和他聊天,說我也在金大讀的碩士。他點點頭,沒有說太多話。
那時他在學校附近租了個單身公寓,每週來學校踢一次球。我勸他早點買房,我那房子漲價賺的錢,比我這些年所有工資還多。他咧了咧嘴,像是在笑,說,如果大家都不著急買房,房價也不會漲這麼快。
他是話題殺手。
有次李曉在操場邊看我們踢球。我下場休息時,她坐過來,扯東扯西繞了一大圈後終於怯聲聲地問我,你覺得陳老師怎麼樣?我說人挺好的,就是不靈活,好像還沒談過戀愛。
我是問你他球踢得怎麼樣?她眼睛瞪得老圓,故作生氣。
不靈活,對付別人前鋒就知道死纏爛打——怎麼,你看上人家了?
才沒有呢!她臉一紅,掉頭就走了。
後來我才從她那得知,陳老師是在耶魯唸的博士。我說那他應該拿了學校不少安家費,可以貸款買房啊!她說,他就是一根筋,說租房也可以。我說,我們高校老師收入可不咋的,每月還完房貸就沒多少錢了,陳老師家裡條件估計也不好。你可得想清楚嘍。
她白了我一眼,然後低下頭輕聲說,和他在一起,住哪都開心。
那時,一些桂花正好落到她肩上,我看著她有些臉紅的樣子。想起之前也聽過女孩說過類似的話,但最後她們沒有和所說的人在一起……
她說她以前也想學數學的,只是爸媽不願意,說學數學不好找工作,於是就學了會計,可是她覺得會計很無聊。
我是心理學老師,各種人向我傾訴心事,所以聽過上百個愛情故事。但是他倆的愛情真是數學的奇蹟,我永遠無法想象兩個人在一起聊數學是怎樣的畫面。但我覺得大多數人的愛好也就是業餘玩玩,沒幾個人像陳老師一樣當真。
可惜那些信後來都被陳老師燒掉了。我手裡只剩一些片段,是我當時堅決反對寄給她的——事實上,他的所有信我都做了很多修改和文學加工。我說如果你還對她抱有一絲想法,就聽我的。當然,我給他改那些信不是無償的,只是當我在朋友圈裡看到李曉的結婚照時,我把所有諮詢費都退回給了他。
李曉的朋友圈照片下面有四個字:“感謝領導”。我有些詫異,覺得不認識她了。和陳老師談戀愛的是另一個李曉嗎?到底哪一個才是真的李曉?是熱戀時那個天真無邪的女孩,還是朋友圈裡感謝領導的新娘?
於是,我重新翻開他寫的那一段信,被我改得面目全非的信。
2.
“過去我很少做夢。最近總是做夢。夢到你,夢到我換工作。
有時我在辦公室裡午睡,看到窗外天空上的雲,有時白,有時灰,有時我想起你,想起過去的十年,想起金大的夏天,似乎金大總在夏天,而你總在秋天。人對另一個人的回憶似乎總定格在某個瞬間,比如我十年前的夏天第一次去金大看到你時的天藍草碧、雲淡風輕。那時我猶豫是否要接受研究生調劑。那時,我從一個985大學的本科考北京的研究生,沒有考上,因為我那愣頭青的性格,我得罪了導師,只能從不那麼好的學校裡挑選、調劑。金大給了我機會,我猶豫著坐上了開往南方的列車。
我猶記得那個初夏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車,然後在杭州一個高中同學的宿舍裡住了一晚——直到那時我才得知,金大不在杭州,在更遠的金城。我原本想打道回府。我同學勸我,還是去看看吧,來都來了。於是第二天上午我離開同學宿舍,坐綠皮火車去了金城。
第二天我第一眼見到金大藍天白雲下青草漫生的模樣,看到你低眉時心事重重的模樣,這些畫面深深地印在我心底,未曾磨滅。我是這樣一個四處漂泊的人,偶然來到金大,偶然遇見你。
後來我同你聊起那次在金大校園裡的偶遇,你全然沒有印象。我們真正相識是在杭州的秋天,最終結束,好像也是在秋天。相處只有一年,於其一生,多麼短暫,我又有什麼資格去大書特書?而我在你心裡,到底有多少分量?我希望真的像你說的那樣,都過去了,沒有留存心底,不會像我一樣再度想起。
你我分手不久就爆發了疫情,感覺整個世界都陷入了深重的災難,感覺我們生活在某個歷史的重大轉折點上,前面就像深淵,我們看不見光。不知是不是因為鋪天蓋地的新聞報導,我那些時候夢見你的次數更多。有好幾次我想要給你寫信,說說家常,或者簡單的問候,但是想想又有什麼用呢?我也出不去,也搶不到口罩,而且這種無意義的關心,很可能只會打擾你的生活,而你也會覺得可笑。於是,我始終沒有說什麼。就像你也再沒有和我說什麼——大概有一年了。
我常常想起去年秋天你在西湖邊說,有時你想這一切其實都會過去的,所有的痛苦,其實都會消散的。我每回想一遍,心裡就難過一遍。我不知道我給你帶去多少痛苦,知道也沒什麼用,一切都過去了,只存在於另一個時空。
你曾經讓我寫一寫我們的故事,就叫《霧霾時期的愛情》。你說,我們相遇在霧霾深重的季節。你是真正愛文學的人,而且對文學有很深的理解——至少在我看來。我最喜歡初次加你微信時你的微信簽名:“一隻眼睛留給紛紛的花朵”,像極了你天真爛漫時的模樣。
其實文學是什麼呢?是貝殼的珍珠吧?是苦難像沙子一樣揉進了心裡,不得不長出珍珠來包裹它。《霍亂時期的愛情》是作者的摯愛,我分明從中讀到了他的心碎。我可以肯定,那個重聚的結尾是他憑空加上的,只讓這個心碎的故事變得更加悽美。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女主人公會突然不再愛他,驀然回首,看見分別多日的戀人,突然就看到不一樣的面孔,然後愛意全消?我無法用理智分析,難以相信這一段。讀到這段時我還熱戀著你,我害怕你也會像她一樣。我不喜歡你說你對我是一種“崇拜式的愛”,我覺得愛不可能是崇拜式的,愛只能是平等的,我害怕你像費爾米納,不是因為了解而愛,只是因為好奇。大概年少天真的人常常犯這錯誤。我去過名校,這名校的光環吸引了你,而不是因為我這樣一個平凡的人。那時,我問你最近在讀什麼書。你說你在讀這本小說。我於是就買來看了好幾遍。我一直看不太明白。我剛讀時總有些擔心,擔心故事最後是個悲劇。後來的一切,恰如我當時的擔心:第二年秋天,你覺得我是個怪人。
於我,那一年已經成為一個有些悲哀的故事,但也隨著時間的流逝變得越發美麗。有時,我不得不對自己說,你並沒有真正瞭解過我,你並沒有真正愛過我,有的只是好奇、幻想、天真的憧憬,以及失望後對我的嘲諷、對我母親的不屑、對我家鄉的鄙夷——我這樣說,是為了讓我不會因為惋惜而太過心痛,不至於覺得錯過了一生中最美好的伴侶。我試圖“理智”地分析:結束是歷史的必然。所以,我最後有些殘忍地對你說,我們的價值觀不合。
那時我還沒有意識到自己在社會現實中只是一個小鉚釘。那年夏天,我的國自然專案申請又一次失敗,而你也惱怒於我沒有告訴你我的母親要來杭州住一段時間……
你不知道呀,後來我終於申上了國自然專案,但也是靠了熟人的幫助——這些我都是後來才聽人說起的,想必能申上專案的人,大部分都有些關係;你不知道呀,我也給幾個名牌大學投過簡歷,後來都莫名其妙地沒了下文,滬大想讓我去,那是一個很好的大學,在很貴的城市。我算了算,收入還不如我現在的,而且我母親身體不太好,我嚐到了生活的艱辛——有時希望和你複合,卻也不希望連累你。
我母親說很難想象我這樣的人會有生氣的時候。於是我便想起,我曾經對你發火。
有時你說的話真是很傷人,但或許你也是很生氣,而這氣憤又是因為在乎。過去的日子都過去了嗎?有時,我在家裡、在辦公室裡看到你送給我的東西,突然想起你,然後心裡一沉。我在夜裡、在夢裡,有時會看見你,然後清晨醒來時會覺得悵惘。我在陽臺上種了很多的花,多肉長得非常好,比你種的還好。我出門騎單車,是載過你的那輛。地鐵已經修通了,你若再來,也不用那麼辛苦地擠公交了。但是,你或許不會再來了。
我希望時間能把這一切沖淡,思念也都像秋葉一樣凋零、消散。然而,這樣想時就覺得人生有些虛無。
關於人生的痛苦,胡老師說可以用寫作來療愈,我寫下這些,原本是為我自己,希望我不會再想起你……但或許,我不該希望忘記你。那原本就是一段寶貴的歲月,只能希望,想起你時不再難過。每個人都有安慰自己的方式,我不會像你一樣,想這一切都會過去,畢竟過去了的,是我的黃金時代,留下的,是沉甸甸的回憶。
畢竟,我是幸運的,與成千上萬在疫情中失業甚至失去親友的人相比,我不覺得有什麼大不了的,包括我們過去的故事,就算是有什麼遺憾和內疚,也真的沒有什麼需要刻意忘記的。很多年後,我可能還會記得,你我曾在校園裡談論命運的數理,也曾在某個夜晚比賽誰能解開那些謎題……這些,於生活來講,都是遠離油鹽的煙花,但如果沒有了這樣的煙花,生活恐怕也只剩下灰色。
謝謝你,從我的世界路過,那是霧霾時期,最閃亮的色彩。”
3.
我博導曾說,人一輩子有六個朋友就很富有。那時我經常和一群球友踢球、喝酒、聊天,覺得我豈不是世界首富?畢業後這些球友各奔東西,大多隻在婚禮上見過最後一面;有一個在杭州上班,後來也只是一起踢過兩次球。於是我才知道我也是窮光蛋。
人在時間面前總有一種挫敗感,曾經那麼要好的朋友,最後也會失去聯絡,消失在人海中。陳老師本該是“六個朋友”中的一個。而李曉和大多數女同學一樣,結婚後就消失了。
我最早認識李曉是在金大心理諮詢室實習時,那時她剛失戀,總是愁眉苦臉的樣子。我也就是個學生,諮詢也就是聽她聊天。她的初戀男友應該是個一米八的高富帥,一米六的我就沒敢對她動心。
時間是最好的心理諮詢師,等她臉上恢復笑容時,我才發現她是個熱心組織聚會的人。我總想在她組織的聚會上找個女友,但是無奈那些女孩都太漂亮了,沒人正眼看我。
人都有突然懂事、接受現實的一天。我是在那天和她們爬山時突然懂事的。我幫一個女生背了很多東西,走了很長的路,坐在石頭上休息時,猛然看見她和一個帥哥在一起聊天。李曉安慰我說他們不會長久的。果然,畢業後,那女孩就回家鄉和另一個人結婚了。
陳老師從來沒有在那些聚會上出現過,大概他研究生三年都在某個隱秘的角落思考數學問題。李曉最後也是和一個老鄉結了婚,她母親介紹的。如果不是我留著陳老師的這一段信,我真不敢相信他們在一起居然有一年——就像難以相信一根冰棒在太陽底下度過整個夏天。
在陳老師認識李曉前,他還去相過幾次親。在他和李曉分手後,就斷了結婚的念頭。是“曾經滄海難為水”,還是想清楚了:結婚不適合自己?
他們都沒有講為啥分手。有一次,陳老師愁容滿面地找我傾訴,說他爸很早去世,他媽獨自拉扯他長大不容易,想讓她來杭州一起住,不然太孤單、生病也沒人照顧,但李曉不同意。
我點點頭,問,想好買房了嗎?
本想買個大點的房子一起住。但是李曉不同意。
李曉家裡條件也一般。我嘆了口氣。
大概一個月後,他們分手了。半年後,陳老師母親病逝。一年後,李曉結婚了,新郎不是他。
往後他再沒找過我。他也不來學校踢球了。有一次我在學校食堂看見他,他穿著黑白相間的長袖格子襯衫,一個人坐在角落裡吃飯,比以前瘦了很多,瘦成了一根冰棒;眼睛窩在眼眶裡看不見,像兩個窟窿。我默默走過去坐到他對面,過了很久,他才抬頭看見我。
他說他在為學校的合同任務發愁。我說,你不是申上國自然了嗎?愁啥?他說,還有一個省裡的科研獎勵,沒申上。
我說,那東西很難申的,學校不會當真。這種獎勵在省裡沒有人脈的話不好申,你又不願意浪費時間做些別的數學題目好出論文成果。見他沒有說話,我改口問,還在解四色問題嗎?他點點頭。我說放心吧,杭大幾時能招到像你這樣的耶魯博士?他們不可能把你咋樣。中國人還是講人情的,不會像美國人那樣認死理。現在國內通訊這麼發達,人情世故也不用花太多時間。你像我,也就是在朋友圈裡給領導點贊,微信群裡跟著別人一起說好話……
他抬頭看了我一眼,沒有說話。我猜他可能還是更喜歡美國人那副死板的樣子,於是就把後面的話嚥下了。
再見他時就是最後一面了。他在校園裡喊住我,等我走近時說,他要去滬大了。我勸他還是別去。
你在哪不能解四色問題呢?杭大好歹給了你副教授的終身編制,雖然你沒完成合同上的任務,也就是取消了你的人才獎勵,把你收入降到和我一樣的二十萬一年,其實你就是不招領導喜歡,不然他們肯定還是按原來的三十萬一年給你。你要是去了滬大,那邊可是動真格的。尤其是現在“破五唯”了,光有論文還不夠,還要讓領導和學生們都滿意才行。你看你每年學生評分都很一般,不就是你太較真了,考試題目出太難、不懂放水。
陳老師說,滬大那邊學生也許會好點。
學生好不好跟你有什麼關係?你的人生目標不就是四色問題?你別惹那些麻煩,留在杭大一心一意把四色問題解開不好嗎?
也許我一輩子也解不開。也許只有我的學生能解開。也許我一輩子的意義只是教出一兩個真正喜歡數學的學生。說完,他騎上那輛“永久”單車走了。
幾天後,我打電話問他搬家要幫忙嗎?他說他找了個搬家公司,跟著貨車走的,已經在上海住下了。
最後一條微信訊息是疫情爆發後收到的,他問我在哪裡能搞到體溫計。我問他怎麼了?發熱嗎?他說不是,學校要他每天上報體溫,但是不知道哪裡能買到體溫計。我說你自己手摸一下不發熱填個37度不就得了?他就沒回我了。
37度的一天,我在網上看到新聞,說他因為合同到期沒透過滬大考核,一怒之下拿刀把學院書記殺了。我摸著自己的額頭,就像烈日下摸著一根冰棒,不知道是冷是熱。
4.
是李曉的Email,她特意申請了一個qq郵箱,暱稱是“駱暮”,或許是不想讓別人發現。Email是這樣寫的:
我看到新聞,哭了好幾天。我不敢相信那是他。他平時連一條魚都不敢殺。送外賣的把湯全灑了他都不生氣,明明應該給他的論文獎勵他也全不在乎。他怎麼會殺人?
他瘋了嗎?我心裡非常痛苦。有時我覺得是我害了他。如果我沒有和他分手,如果我們還在一起,他不會這樣。有時我夢見殺人的是我。
可是我那時真的很痛苦。我只想好好愛一個人,就這麼簡單的願望,為什麼就這麼難?一開始,我還安慰自己:將來數學的進步也有我的一份付出,可是那麼長久的痛苦之後,你也會懷疑,為什麼是我?為什麼我的幸福沒有一個數學問題重要?
他在親熱時還要想那個問題,有一次他突然在我的身上用手指寫寫劃劃,眼神空洞,像是局外人一樣!他居然在我們親熱的時候想那個四色問題!我寧願他心裡有另一個女人也不希望有這個問題!我太絕望了,我沒有一點勝算!就像一個人不可能打敗天空,我不可能贏得他的愛!
別的女人收到男人很多的禮物,精挑細選的衣服。可是他從來沒有送我什麼禮物!只有一次,他知道我喜歡音樂,送了我一個玩具鋼琴。我笑了。我逛了一天商場,給他買的衣服,他都不怎麼穿,說是怕弄髒!他就喜歡穿白色T恤、黑色絨服、黑白格子襯衫,根本找不到第四種色!這些我都認了。
我要的很少。我最後只想他能夠抽空陪陪我,一起過日子,慢慢變老。但最後連這麼卑微的願望都不能有嗎?他一定要把他母親接過來和我們一起住。我們本來就沒什麼錢,他本來就沒多少時間陪我!
你們可能以為我是因為不能忍受和他母親在一起才分手的。不!根本不是你們想象的那樣!
我想愛一個人就是不計較犧牲。我願意陪他一起,幫他照顧老人,承受生活的艱辛。真正讓我心寒的是另一件事。一件我從沒和別人說起的事。
是我堂姐的兒子。我堂姐命苦,她男人很早出車禍去世了,我堂姐一個人把兒子養大。他就在杭大上學,高數沒過不能拿到畢業證,需要回學校補考。我堂姐前年中風,她兒子又要照顧母親又要讀書,眼盼著畢業了能找個像樣的工作,就差這一門高數。我就求過他這一件事,我說這個孩子和你多像啊!你為什麼不能同情一下他?也不要你給他高分,給個60分就好了!可他一點都不心軟,我真沒想到他心腸這麼硬!他說要公平,我說這個世界對那個孩子公平嗎?別人可以專心讀書,而他要一邊照顧家裡一邊學習,哪有那麼容易!?學校是組織過幾次捐款慰問,但是自己生活的苦別人又能分擔多少?
是啊,自己生活的苦,別人又能分擔多少?只有自己嘗,沒人能夠分擔。我終於想明白,我不願跟這樣高尚的人、這樣冷冰冰的人在一起過一輩子!我感覺我是在跟數學公式談戀愛!我怕他對我以後的孩子也會像對待數字一樣!我更怕我的孩子像他一樣……
信很長,後面的內容不便道與外人。信裡,我彷彿看到冰棒與陽光的相遇,晶瑩剔透,美好又短暫,最後連淚水也都蒸發,成為天上的白雲。這封信我不知道怎麼回。我也不知道,以後是否會再遇到這樣一個朋友——一根烈日下的冰棒,在短暫的一生中思考亙古不變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