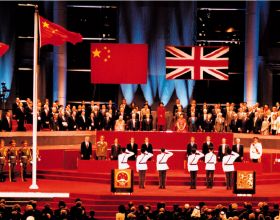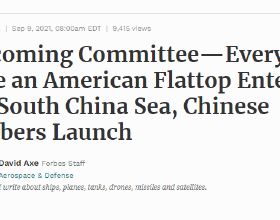從此,我離開了家鄉。後來,我和我的作品,又不斷回到家鄉。這時的回去,和過去的離開又不一樣。我想說的是,延津與延津的關係,就是我作品和延津的關係,也是世界跟延津的關係。換句話,延津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延津。
河南延津是我的家鄉。
延津瀕臨黃河,“津”是渡口。因水運便利,三國時,曹操曾“屯糧延津”。官渡大戰,更早的牧野大戰,就發生在延津附近。但黃河不斷滾動翻身,兩千多年過去,延津距離黃河,已有三十多公里,成了黃河故道。作為渡口,已是兩千多年前的事了。
《詩經》也產生在延津附近。其中的邶風、鄘風和衛風,在周朝,皆是我鄉親口頭傳唱的民謠。臺灣有個學者叫李辰冬,他經過二十年的艱苦考證,又說311篇《詩經》,不是口頭民謠,而有一位文字作者,這位詩人叫尹吉甫,是延津人。我提尹先生,並無攀附之意,我們家,自我媽往前輩數,都不識字。
我從小生活在延津縣王樓鄉西老莊村。黃河故道盛出兩種特產,一,黃沙;二,鹽鹼;我們村得到的遺產是鹽鹼。春夏秋冬,田野上白花花一片,不長莊稼。據說,我外祖父他爹,是西老莊村的開創者。他率領家族,在這裡落腳,看中的就是鹽鹼。一家人整日到地裡刮鹽土鹼土,然後熬鹽熬鹼,然後推著獨輪車五里八鄉吆喝:“西老莊的鹽來了”“西老莊的鹼來了”。新起的村莊,就著“老莊”的村名,顯得出售的鹽鹼有歷史傳承。得承認,這是一種智慧。
我們村距開封四十多公里。放到宋朝,就是首都郊區。那時的宋徽宗和李師師,口音都跟我們村差不多;說的都是普通話。我母親年輕的時候,曾到開封學過汴繡;這趟旅行,成了她多少年聊天的經典話題。“我當年在開封學汴繡的時候,曾去狀元橋吃過灌湯包;元宵節那天,還去馬市街看過燈市。燈市你懂不懂?那陣勢……”我不懂。後來讀了孟老元的《東京夢華錄》,懂了。
當我陰差陽錯成為一個作者,“延津”作為一個地名,頻繁出現在我的作品裡。為什麼呀?是不是跟福克納一樣,要把延津畫成一張郵票呀?這是記者問我的經典話題。我的回答是,我不畫郵票,就是圖個方便。作品中的人物,總要生活在一個地方;作品中的故事,總要有一個發生地;如果讓這人的故事,發生在延津,我熟悉的延津胡辣湯,羊湯,羊肉燴麵,火燒……都能順手拈來,不為這人吃什麼發愁;還有這人的面容,皺褶裡的塵土,他的笑聲和哭聲,他的話術和心事,我都熟悉,描述起來,不用另費腦筋。正如有人問,你好多部作品的名字,都是“一”字開頭,如《一地雞毛》《一腔廢話》《一九四二》《一句頂一萬句》《一日三秋》,是不是有意為之呀?我的回答是,有意為之是件痛苦的事,給每部作品起名字的時候,我真沒想這麼多;但走著走著,抬頭一看,它們像天上的大雁一樣,竟自動排成了行。我這麼說,估計人家也不信。不信就不信吧,一個作品名字,不是什麼經天緯地的大事。
我書中的延津,跟現實的延津,有重疊的地方,也有不一樣的地方;因為都叫延津,容易引起混淆。現實的延津不挨黃河,縣境之內,沒有自發的河流;總體說,延津跟祖國的北方一樣,是個缺水的地方。但《一句頂一萬句》中,卻有一條洶湧奔騰的津河,從延津縣城穿過。元宵節鬧社火的時候,津河兩岸鑼鼓喧天,人山人海;第二天早上,沿河兩岸,剩下一地鞭炮的碎屑和眾人擠丟的鞋。一些讀過《一句頂一萬句》的朋友去了延津,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在縣城走了一遍,問:河呢?塔鋪是延津的一個鄉,我寫《塔鋪》的時候,以“我”為主人公;在高考複習班上,“我”與一位清秀的女孩李愛蓮,發生了純潔的愛情。一些朋友去了塔鋪,四處打聽:李愛蓮的家在哪條街?《一日三秋》的開篇,從六叔和六叔的畫寫起。六叔畫的,全是延津和延津五行八作的人;六叔死後,這些畫作被六嬸當燒紙燒了;為了忘卻的紀念,為了重現六叔畫中的延津,我寫了《一日三秋》這本書——這是書中的話。一些朋友讀了這本書,常問的問題是:延津真有六叔這個人嗎?現在,我用六叔的畫作,統一回答這些問題。
“六叔主要是畫延津。但跟眼前的延津不一樣。延津不在黃河邊,他畫中的延津,有黃河渡口,黃河水波浪滔天。延津是平原,境內無山,他畫出的延津縣城,背靠巍峨的大山,山後邊還是山;山頂上,還有常年不化的積雪。有一年端午節,我見他畫中,月光之下,一個俊美的少女笑得前仰後合,身邊是一棵柿子樹,樹上掛滿了燈籠一樣的紅柿子,便問,這人是誰?六叔說,一個誤入延津的仙女。我問,她在笑啥?六叔說,去人夢裡聽笑話,給樂的。又說,誰讓咱延津人愛說笑話呢?”
不知我用六叔的畫,說明白這些混淆沒有。沒說明白也不要緊,文學混淆了一些現實,也不是什麼經天緯地的大事。
我的意思是,什麼叫文學?生活停止的地方,文學出現了。
其實,如果我只是以延津為背景,寫了一些延津人發生在延津的一些事,只能算寫了一些鄉土小說。鄉土小說當然很好,但不是我寫小說和延津的目的;欲寫延津,須有延津之外的因素注入,也就是介入者的出現。是誰來到了延津,激活了五行八作和形形色色的延津因素和因子,諸多因素和因子發生了量子糾纏,才是重要的。這是一個藝術結構問題。在《一句頂一萬句》中,有一個介入者叫老詹。有老詹和沒有老詹,《一句頂一萬句》的格局是不一樣的,呈現的延津也是不一樣的。老詹是義大利一個傳教士,不遠萬里來到延津。老詹的本名叫詹姆斯·希門尼斯·歇爾·本斯普馬基,延津人叫起來嫌麻煩,就取頭一個字,喊他“老詹”。老詹來延津的時候,不會說中國話,轉眼四十多年過去,會說中國話,會說河南話,會說延津話;老詹來延津的時候,眼睛是藍的,在延津黃河水喝多了,眼睛就變黃了;老詹來延津的時候,鼻子是高的,在延津羊肉燴麵吃多了,鼻子也變成一個麵糰。四十多年過去,老詹已是七十多的人了,揹著手在街上走,從身後看過去,步伐走勢,和延津一個賣蔥的老漢沒有任何區別。老詹在延津待了四十多年,只發展了八個徒弟。老詹在黃河邊遇到殺豬匠老曾,勸老曾信主。老曾按中國人的習慣,問:“信主有什麼好處?”“信了主,你就知道你是誰,從哪兒來,到哪兒去。”“我本來就知道呀,我是一殺豬的,從曾家莊來,到各村去殺豬。”“你說的也對。”老詹想想又說,“咱不說殺豬,只說,你心裡有沒有憂愁?”“那倒是,凡人都有憂愁。”“有憂愁不找主,你找誰呢?”“主能幫我做甚哩?”“主馬上讓你知道,你是個罪人。”“這叫啥話?面都沒見過,咋知道錯就在我哩?”兩人不歡而散。由於延津的天主教勢單力薄,延津辦新學的時候,教堂被縣長征作學堂,老詹從教堂裡被趕了出來,住在一個和尚廢棄的破廟裡;但老詹傳教的心仍鍥而不捨,每天晚上,都要給菩薩上炷香:“菩薩,保佑我再發展一個天主教教徒吧。”在延津被傳為笑談。
老詹和延津的關係,不知我說明白沒有?
《一日三秋》中,也有一個介入者叫花二孃。花二孃就是六叔畫中那個仙女。老詹到延津是為了傳教,花二孃到延津來,是為了到延津人夢裡找笑話。你笑話說得好,把她逗笑了,她獎勵你一隻紅柿子;你笑話沒說好,她也不惱,說,揹我去喝碗胡辣湯。但花二孃是一座山,誰能背得動一座山呢?剛把花二孃背起,就被這座山壓死了。或者,就被笑話壓死了。
一個笑話,與延津的量子糾纏。
我的意思是,如果只寫延津,延津就是延津,介入者的介入,便使延津和世界發生了聯絡,使延津知道了世界,也使世界知道了延津,也使延津知道了延津。
除了介入者,從延津出走者,對於寫延津同等重要。這是另一個藝術結構問題。在《新兵連》中,我寫了一群從延津出走的鄉村少年。他們在村裡,到了夏天,還是睡打麥場的年齡,當他們離開延津,到達另一個世界,馬上發生了困惑。剛到新兵連吃飯,豬肉燉白菜,肉瘦的不多,全是白汪汪的大肥肉片子。但和村裡比,這仍然不錯了,大家都把菜吃完了,惟獨排長沒有吃完,還剩半盤子,在那裡一個饃星一個饃星往嘴裡送。新戰士李勝看到排長老不吃菜,便以為排長是捨不得吃,按村裡的習慣,將自己捨不得吃的半盤子菜,一下傾到排長盤子裡,說:“排長,吃吧。”但他哪裡知道,排長不吃這菜,是嫌這大肥肉片子不好吃,他見李勝把吃剩的髒菜傾到自己盤子裡,氣得渾身亂顫:“李勝,幹什麼你!”接著將盤子摔到地上。稀爛的菜葉子,濺了一地。李勝急得哭了。事後“我”勸李勝,李勝說:“排長急我我不惱,我只惱咱村其他人,排長急我時,他們都偷偷捂著嘴笑。”這裡寫的不僅是李勝的難堪,也是延津在世介面前的碰壁。同時,“他們都偷偷捂著嘴笑”,是我那個階段的寫作水平,開始知道由此及彼。由延津到世界,也是由此及彼。
在《我不是潘金蓮》裡,主人公李雪蓮也走出了延津:她從延津走到市裡,走到省裡,來到北京。走來走去,只是為了糾正一句話,“我不是一個壞女人”;但她走來走去,花了二十年功夫,這句話還是沒有糾正過來。一開始還有人同情她,後來她的絮叨就成了笑話,沒人願意再聽她說話。當這本書出荷蘭文時,我去荷蘭配合當地出版社做推廣工作,一次在書店與讀者交流,一位荷蘭女士站起來說,她看這本書,從頭至尾都在笑,但當她看到李雪蓮與所有人說話,所有人都不聽,她只好把話說給她家裡的一頭牛時,這位荷蘭女士哭了。接著她說,當世界上只有一頭牛聽李雪蓮說話時,其實還有另外一頭牛也在聽李雪蓮說話,他就是這本書的作者。
這是李雪蓮和世界和牛的關係。
再說一位從延津出走者,便是《一句頂一萬句》中的私塾先生老汪。老汪有四個孩子,三個男孩,一個女孩。三個男孩都生性老實,惟一個女孩燈盞調皮過人。別的孩子調皮是扒樹上房,燈盞愛到東家老范家的牲口棚玩騾子馬。牲口棚新添了一口淘草的大缸,一丈見圓。燈盞玩過牲口,又來玩缸,沿著缸沿支岔著手在蹦跳,一不小心,掉到缸裡淹死了。那時各家孩子多,死個孩子不算什麼,老汪還說:“家裡數她淘,煩死了,死了正好。”轉眼一個月過去了。這天,老汪去家裡窗臺前拿書,看到窗臺上有一牙月餅,還是一個月前,陰曆八月十五,死去的燈盞偷吃的;月餅上,留著她小口的牙痕。當時燈盞偷吃月餅,老汪還打了她一頓。燈盞死時老汪沒有傷心,現在看到這一牙月餅,不禁悲從中來,扔掉書,來到牲口棚的水缸前,開始大放悲聲。一哭起來沒收住,整整哭了三個時辰,把所有的夥計和東家老範都驚動了。轉眼三個月過去,下雪了。這天晚上,東家老範正在屋裡洗腳,老汪進來說:“東家,想走。”老範吃了一驚,忙將洗了一半的腳從盆裡拔出來:“要走?啥不合適?”“啥都合適,就是我不合適,想燈盞。”“算了,都過去小半年了。”“東家,我也想算了,可心不由人呀。娃在時我也煩她,打她,現在她不在了,天天想她,光想見她。白天見不著,夜裡天天夢她。夢裡娃不淘了,站在床前,老說:‘爹,天冷了,我給你掖掖被窩。’”“老汪,再忍忍。”“我也想忍,可不行啊東家,心裡像火燎一樣,再忍就瘋了。”“再到牲口棚哭一場。”“我偷偷試過了,哭不出來,三個月了,我老想死。”老範吃了一驚,不再攔老汪:“走也行啊,可你到哪兒,也找不到娃呀。”“不為找娃,走到哪兒不想娃,就在哪兒落腳。”老汪帶著妻小,離開延津,一路往西走。走走停停,到了一個地方,感到傷心,再走。三個月後,出了河南界,到了陝西寶雞,突然心情開朗,不傷心了,便在寶雞落下腳。這年元宵節,寶雞滿街掛滿了燈籠,萬千的燈籠中,他似乎又見到了燈盞。
不知我說明白沒有?
我進一步想說的是,地域性寫作,和走出地域的寫作,不僅有外來介入者、從地域出走者的區別,更重要的是,背後還有作者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分野。魯迅與其他鄉土作家的區別是,鄉土作家寫一個村莊,是從這個村莊看世界;魯迅寫一個村莊,是從世界看這個村莊,於是有了《阿Q正傳》《祝福》《孔乙己》等作品。
我曾經說過,文學的底色是哲學。
接著我想說說幽默。目前我的作品被翻譯成二十多種文字,文字到達之處,讀過我書的人,都說我很幽默。其實這是一種誤會,因為他們沒到延津來過;到了延津他們就知道,我是延津最不幽默的人,我的鄉親,個個比我會說笑。這也是花二孃到延津來找笑話的原因。延津人日常見面,不以正經話應對,皆以玩笑招呼。張三到李四家去,李四家正在吃飯,李四邀請張三坐下吃飯,說的決不是“請坐,一塊吃點吧。”而是:“又是吃過來的?又是不抽菸?又是不喝酒?”如果是外地人,便不知如何應對,場面會很尷尬;延津人會這麼回應:“吃過昨天的了,不抽差煙,不喝假酒。”坐下一塊吃喝起來。兩個延津人,在一起討論非常嚴肅的話題,如張三與李四談一單生意,或李四想找張三借錢,也是以玩笑的方式進行討論;談笑間,已安邦定國;或者,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
延津人為什麼這麼幽默?這也是一些記者問我的經典話題。當然,幽默的源頭不該從幽默本身找;如果幽默只是幽默,就成了耍嘴皮子;幽默的背後,可能有更重要的現實和歷史原因;結論可能是:喜劇的底色會是悲劇,悲劇的底色會是喜劇;或者,悲劇再往前走兩步會是喜劇,喜劇再往前走兩步會是悲劇;幽默再往前走兩步可能就是嚴肅,嚴肅再往前走兩步可能就是幽默。《一日三秋》中不會說笑話的人,在夢中被花二孃壓死了,等於被笑話壓死了,也等於被他的嚴肅壓死了。一九四二年,因為一場旱災,我的家鄉河南被餓死三百萬人。三百萬人是什麼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被納粹和希特勒迫害致死的猶太人,約一百一十萬人;等於一九四二年的河南,有三個奧斯維辛集中營,缺少的是納粹和希特勒。這些被餓死的河南人,是如何對待自己的生死呢?逃荒路上,老張要餓死了,他臨死前沒有憤怒,也沒有追問:我是一個納稅人,為什麼要把我餓死,國民政府為什麼沒有起到賑災的責任?而是給世界留下了最後一次幽默,他想起了他的好朋友老李,老李三天前就餓死了,他說:“我比老李多活三天,我值了。”老張為什麼能用幽默的態度對待生死?那是因為從商朝到一九四二年,黃河兩岸發生的餓死人的事太多了。我寫《溫故一九四二》的時候,曾採訪我的外祖母:“姥娘,咱們談一談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二年是哪一年?”“就是餓死人的那一年。”“餓死人的年頭多得很,你到底說的是哪一年?”當嚴酷成為一種日常的時候,你用嚴肅的態度對付嚴酷,嚴酷就會變成一塊鐵,你是一顆雞蛋,撞到鐵上就碎了;如果你用幽默的態度對付嚴酷,嚴酷就會變成一塊冰,幽默是大海,這塊冰掉到大海里就融化了。
關於幽默,不知我說明白了沒有?
延津有一種地方戲,叫二夾弦,大家再去延津的時候,建議大家聽一聽。這個劇種管絃節奏急,唱腔語速快,從頭至尾,像兩個人在吵架,讓人目不暇接和耳不暇接。有什麼事,不能慢慢說嗎?急管繁弦,難說煙景長街;但它就是這麼快,不給人留半點間隙和喘息的時間;就像我們村的人吃飯,個個吃得快,生怕吃了上頓沒下頓一樣,大概也是歷史留下的病根。急切的戲劇,你聽著聽著就笑了,也是一種幽默。
至今想來,延津讓我第一次感到震撼,正是我離開延津的時候。我當兵那年,在新鄉第一次見到火車。那時的火車還是蒸汽機。我隨著幾百名新兵排著隊伍往前走,上到火車站的天橋上,一列綠皮火車鳴著笛進站了。在火車頭噴出的蒸汽中,從火車上下來成百上千的陌生人,又上去成百上千的陌生人,這些人我一個都不認識,我不知道他們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過去我在村裡,村裡的人我都認識;熟悉沒有讓我感動過,現在為了陌生和陌生的震撼,我流淚了。排長問:“小劉,你是不是想家了?”我無法解釋熟悉和陌生的關係,我只好說:“排長,當兵能吃白饃,我怎麼能想家呢?”
從此,我離開了家鄉。後來,我和我的作品,又不斷回到家鄉。這時的回去,和過去的離開又不一樣。我想說的是,延津與延津的關係,就是我作品和延津的關係,也是世界跟延津的關係。換句話,延津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延津。
謝謝延津,也謝謝每一個讀過我作品和去過我家鄉的朋友。
2022年1月
關於作者
劉震雲,漢族,河南延津人,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曾創作長篇小說《故鄉天下黃花》《故鄉相處流傳》《故鄉面和花朵》(四卷)、《一腔廢話》《我叫劉躍進》《一句頂一萬句》《我不是潘金蓮》《吃瓜時代的兒女們》《一日三秋》等;中短篇小說《塔鋪》《新兵連》《單位》《一地雞毛》《溫故一九四二》等。
其作品被翻譯成英語、法語、德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瑞典語、捷克語、 荷蘭語、俄語、匈牙利語、塞爾維亞語、土耳其語、羅馬尼亞語、波蘭語、希伯來語、波斯語、阿拉伯語、日語、韓語、越南語、泰語等20多種文字。2011 年,《一句頂一萬句》獲得茅盾文學獎。2018 年,獲得法國文學與藝術騎士勳章。根據其作品改編的電影,也在國際上多次獲獎。
作者:劉震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