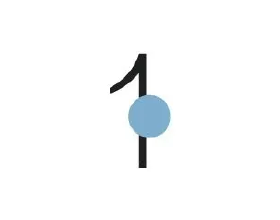作者 | 別角晚水
1
劍子嶺開始落雨的時候,溫杏正哼哧哼哧地爬到半山腰。這裡前不著村後不著店,她布裙荊釵,蹬一雙水一浸就軟趴趴的草鞋,站在空曠的野地裡一籌莫展。薄薄一個紙囊,包著小份金貴的胭脂,原被她小心翼翼地收在懷裡,此刻經雨一澆,淋淋漓漓染了她一身的紅。
溫杏一屁股坐下,把揹著的藤箱往地上重重一擱,捏著已然無用的胭脂生悶氣。
這是她凌晨趕至鎮上,喊破喉嚨賣掉攢了半月的草藥,又在雲翠軒門口排了整整兩個時辰的隊才換回的寶貝,不料就這麼斷送了。她越發氣不過,抬手便拍了那藤箱一巴掌:“都怪你!若不是你不安分,偷跑出去又被野狗追著咬,我就不用費時救你,那咱們這會子早就回了小梅村!”
說這話時,她唇不點而紅,眼睛也紅,宛如被雨水打溼的一朵杏花。藤箱原地彈了彈,蓋子被頂開,探出一隻白兔的圓腦袋,三瓣嘴一聳一聳的,倒像是比她還要委屈些。
“臭小八,看我回去怎麼收拾你!”溫杏提溜著罪魁禍首的長耳朵,將它撈過來擦手。這是她救下的小野兔,性子甚是活泛,成天裡喜歡給她惹麻煩。
“一會兒招狗一會兒招雨的,你這麼厲害,倒是給我招個如意郎君來呀!”她拈一把小八前額被胭脂染紅的毛,想起話本子裡白兔化形的清朗少年,雨天眉間點著硃砂、飄著白衣,擎一柄八十四骨紫竹傘,跋山涉水地趕來對恩人以身相許。她已是待字閨中的年紀,少女情懷如詩,豈會不憧憬未來夫婿的模樣?可她自幼父母雙亡,又被小梅村的村民們看作天煞孤星,冷言冷語聽慣了,打小便躲著人堆走,除了小八這類小小生靈,無人敢與她親近,更別提什麼紅鸞星動了。
罷了,姻緣之事,人力難及,又何必為難一隻小兔子。她揉揉懷裡的毛團,剛要把它塞回藤箱裡,忽聽一聲“姑娘”響在耳後,如水激冰玉,還是個男子音色。
溫杏嚇得魂飛天外,一把把小八丟出十丈遠,頂著一腦門的雨水發矇,想破頭也不明白好好的一隻母兔子怎麼就原地成了精,還修了個男身?戰慄心口緩緩浮上一陣奇異的戰慄感,她正兀自晃神,小八跳上側方山石,伸出前腿蹭蹭擋住小紅眼睛的紅毛,後腿蹦了三蹦,似乎在極力引起她的注意。
又是一聲“姑娘”傳來,不過這一次,溫杏看得很清楚,小八的三瓣嘴紋絲不動。她狐疑地走上前,只往石下望了一眼,原本就不甚清楚的腦子更暈了——那兒臥了個白衣少年,更巧的是,他眉間果真綴了顆硃砂痣。雨還在下,天空灰濛濛的,偏他一個瑩潤潔白,宛若淌著光的明珠,從額頭、眼睛、鼻子、唇齒,再到指甲蓋兒,無一處不亮,無一處不美。
溫杏如墜夢中,盯著他眉心那一點硃砂許久,胭脂、小八、話本子、白兔少年……走馬燈似的在腦子裡來回穿梭。鬼使神差地,她走過去,揮著溼淋淋的袖子,二話不說便去擦那少年的硃砂痣,一下,兩下……少年雙眸含波,好脾氣地任她胡鬧,待她盡興了,才帶著笑意咳了咳:“這是天生的,抹不掉。姑娘若玩夠了,可否勞駕搭把手,除去在下這身汙穢?”
他目光溫暖,聲音卻虛弱,溫杏從羞赧中驚醒,這才發現他右手持劍,左手無力地垂在身側,自膝而下,盡是蜿蜒的血跡,顯然是腿部和左手都受了重傷,亟待止血又苦於沒有力氣,這才求助於她。
“別慌,我還有一些白芨沒賣完,止血很靈的,這就來幫你!”溫杏嘴上鎮定,說著幫忙,手忙腳亂的卻是她自己。傷口堪堪包紮好,她便忙不迭地抬頭去看那少年,這一瞧,便不小心鼻子對鼻子、額頭對額頭地與他撞在一起,傷口上剛打好的結又鬆散開。少年禁不住悶哼一聲,轉眼見溫杏兩頰紅熱,泫然欲泣,又是一怔。他微微笑了笑,溫聲道:“無妨,多試幾次就好了。”
說這話時,他眉眼低垂,那點兒溫軟的笑意纖塵不染,教溫杏挪不開眼。她長到如今,從未有人對她假以辭色,更別提如今日這少年一般,忍著一身傷痛,仍不忘好言相慰。她攥著白芨,驀地想起臨出門前被她匆匆掃過又撇在腦後的皇曆,上面寫的是“忌遠遊,宜嫁娶”。
她的臉在這一瞬間燒得更紅。
2
劍子嶺山勢險峻,一如其名,待到日暮後還總是野獸蛇蟲齊出,其中不乏毒物。眼見這少年之傷片刻不能耽誤,溫杏強自回神,絞著小八的紅毛問:“你傷得很重,必須臥床靜養,可最近的歇腳之處就是小梅村了,你願意跟我回家嗎?”
少年聞言一愣:“你不問問我的姓名、來歷、為何會受傷在此,就肯帶我回家,不怕我是壞人嗎?”
溫杏滿不在乎地擺擺手:“誰都知道如今大月國不太平,皇帝老頭終日沉迷長生不老之術,派了那些不把百姓當人看的爪牙到處尋訪神藥,欺凌弱小,攪得天下人心惶惶的,哪裡都亂。世道兇殘,你是遇上土匪也罷,被仇家追殺至此也罷,定是無處可避了,才會跑到咱們這麼偏僻的地方,相逢即是有緣,你有傷,我有藥,幫你一把是應該的。”她頓了頓,按捺著心口愈加強烈的戰慄感,把目光從他臉上移開,不好意思地舔舔唇,“再說,我一個孤女,沒財沒勢的,你能圖我什麼?倒是你……”
生得這樣好看,讓人一見便從心底湧出歡喜。
回村之路遠比想象中艱辛。溫杏本以為,大雨滂沱,村民們都會躲在家裡,無暇再同往日一般欺負她,可即便她偷偷走了小路,依然被在泥地裡打滾的小喇叭逮著了。小喇叭祖上三代都是村霸,手一拍、腳一跺,嗓門震天響:“掃把星迴來咯!還帶了個野男人!”
村民們立刻蜂擁而至,喊著她的名字咒罵,汙言穢語蓋過雨聲,溫杏胡亂地抹了把眼睛,把她的白兔少年擋在身後。少年靜靜地望著她的側臉,她雖面無表情,似乎外界的辱罵根本無關痛癢,可臉色蒼白如紙,剛剛被她抹去的,分不清是雨還是淚。
這樣年紀的小姑娘,本該被父母親朋捧在掌心嬌寵愛惜,為何今日連哭笑都麻木,卻還敢毫不猶豫地護在他身前?
“小妖女!”不知是誰先起的頭,擲了石塊過來。溫杏眼一閉,意料之中的疼痛卻沒有降臨,只聽“當”的一聲,緊接著,是小喇叭哭天搶地的哀號。那少年不知何時已長劍出鞘,將那石塊擊落,還順勢還了小喇叭劈頭一記。
“滾。”他語聲淡淡,可頭破血流的小喇叭怎敢再鬧事,捂著腦袋一溜煙地跑了。溫杏愕然睜眼,少年腿上再度滲出鮮血,手中之劍卻紋絲不動,他挺著腰板直著脖頸,目光凜凜地看向眾人,沉聲道:“我倒要看看,從今往後,誰敢再欺侮她?”
溫杏咬著唇,見他劍穗上那塊似某種玉石的冰藍色物正輕輕晃動,那股莫名的戰慄感再次翻湧而來,可這一回,令她真正茫然無措的,是她此刻無比紛亂的心跳。她藏了多年的心頭小鹿,終於揣不住了。
隨著人群散盡,少年也在同時跌落在地。溫杏知道他傷得有多重,慌忙扶住他,瞪著眼睛“你”了許久,想埋怨他為何要將僅有的力氣用在替她出頭上,又恍然驚覺自己甚至連他叫什麼都還不知道呢。
他被她帶回家裡,按在榻上不讓亂動,於是只得從她一口氣蓋上的三大床被子裡慢慢地抬起頭來:“我身上揹著的事並不光彩,若貿然道出姓名,只怕會連累姑娘。若你願意,隨便給我取個貓兒狗兒的名字都好,只要你喚,我必答應。”
溫杏圍著藥爐子搖蒲扇,注意力全在藥上,隨口嗯一聲:“我撿過不少小傢伙,鳥兒兔兒都有,你是第九個,要不我以後便喊你小九?”
她只當是說笑,話音未落自己都繃不住咧了嘴,不想他也笑了,屋內彷彿進了春天,他說:“好啊,阿杏。”
剛才鋪天蓋地的辱罵聲裡,他只聽見了一朵杏花的名字,她是眾人口中生而不祥的妖女,此後,卻是他一個人珍之重之的阿杏。
3
溫杏很快就意識到,名字這玩意兒不能亂起。她收養的小傢伙們排行越小性子就越跳脫,本以為到了小八這兒已然是巔峰,不料小九橫空出世,傷還沒好透就整天提著他那把唬人的劍在村子裡瞎溜達,月上梢頭才肯回來。溫杏既不知這一窮二白的小梅村有何特別之處,值得日日閒逛,也不知小九原是這個好動的性子,和他的模樣倒是南轅北轍般不相符。
她自小心大,習慣包容身邊一切苦楚,不然也不會樂呵呵地長到今日,因此也不甚在意小九的舉動。只在又一晚替他換藥時,才後知後覺地凝視著他遲遲不愈的傷口,皺眉嘟囔道:“為何這麼多天都不見好?定是你瞎折騰的緣故,一天天的只知道往外跑,也不好好休息,如此不消停,傷勢怎麼恢復?”
小九坐在榻上,輕輕眯了眯眼睛:“你很希望我的傷好嗎?”
“那當然了。”溫杏脫口而出,心想這問的是什麼話。
小九嘴角抽了抽,久久沒有說話,兩頰像是暈開了一片紅。溫杏更納悶了,剛要懷疑自己是不是產生了錯覺,小九從榻上跳下,衣袂搖搖,恰恰從她發頂拂過:“我傷一好,也就是要離開的時候。你很希望我走嗎?”
溫杏微張了嘴。小九已走到門口,回身望了望她:“我‘瞎折騰’的這幾天,全村人都知道了,溫杏身邊多了個護衛,練家子,不好惹,見了就得繞道走。阿杏,只有你不懂。”
溫杏一夜沒睡。小九那幾句話翻來覆去地在她耳邊迴盪,連帶著他獨有的清香氣息似乎都清晰可聞。她徒勞地安撫著心口的酥麻感,捫心自問,如果當日受傷的不是小九,而是一個相貌鄙陋的粗人,或者跟小八它們一樣,只是一些同她無親無故的小動物,她還會不會出手相助?
她當然會。可她不會像對待小九一般,挖空心思地想著如何能讓他儘快痊癒,更不會像面對他的時候似的滿懷欣喜。她只願他好,以至於從未想過他好之後是否會離開。自打他來,她冷清的屋子裡才開始有了暖意,他幫她照顧兔子們,替她揀選草藥、加固房梁,縱容她喋喋不休地傾吐十餘年來未曾袒露人前的委屈,待她說累了、說倦了,再小意溫柔地把她抱回房裡。已經嚐到溫暖滋味的人,該如何才能回到過去的冷寂中去?
天光乍破,已是黎明。溫杏口乾舌燥地踢掉被子,跑到灶間想舀碗水喝,低頭時無意瞥見臺上那盆虎刺長得鬱鬱蔥蔥,還隱隱抽出了花苞。真是奇怪了,平日裡任憑她如何悉心蒔弄它都無精打采,怎麼這會子她不搭理了,它反而自己茂盛起來?心念微動,她俯身去聞,霎時便清醒了:好大一股藥味兒!敢情她費盡心神為小九熬的補藥,一滴不剩地全進了這盆虎刺的肚子,難怪他的傷好得這麼慢!
他於此間落難,本是意外,遲早都要走的。如今卻不惜自傷其身,只是為了留在她身邊嗎?溫杏連水都喝不下去了。
行吧,都到了這一步,誰愛頂誰頂,反正她頂不住了。
她現在就想見到他。
4
小九不見了。
被褥齊整地疊在床頭,屋裡一覽無餘,彷彿又回到了從前雪洞般的素靜寒涼。溫杏攥緊了衣裳,呆了一瞬,拔足便往外衝。
她要把他追回來!
已近寒露時節,山氣砭人肌骨,溫杏只著一件寢衣,漫無目的地在村子裡奔跑。起早的村民們見狀紛紛掩起門窗,誠如小九所言,再無人敢當面給她難堪。找著找著,她越發掛念起他來,前路順暢,可該往哪裡去才能尋到他?
焦灼感不由自控地急劇升騰,溫杏腳步卻是一滯。不遠處的田埂上,小喇叭正耀武揚威地舉著什麼物什蹦來跳去,底下一幫黃毛小兒拍手的拍手、吵鬧的吵鬧。她看得兩眼發痛,只因被小喇叭耍玩的東西,她再熟悉不過——那是小九劍穗上的冰藍色飾物,石質通透,世所罕見,只配用來襯他。
“你怎麼會有這個?”她劈手奪下那塊飾物,用力之大讓小喇叭險些摔倒。小喇叭發矇地看了看自己的空手,沖天的羞惱讓他忘記了小九的警告,尖叫著狠狠撲向溫杏:“掃把星,你敢推我!”
若是擱在從前,溫杏根本不會和小喇叭起衝突,從她的第一件東西被肆意踐踏開始,她就學會了忍耐。可是今天不行,這是小九的東西!她用最原始粗魯的方式,不顧外界一切指戳,和一個小孩子扭打在一起。她不會打架,只本能地又抓又咬,瞪得溜圓的兩眼漸漸被水汽潤溼:“小九的東西為什麼會在你這裡?他去哪裡了?你把他怎麼了?”
她緊緊捏著那冰藍色的薄片,死死抵在小喇叭脖間,一遍遍地厲聲問。小喇叭垮塌下來,他向來跋扈,又認準溫杏盡人可欺,怎知她骨子裡竟是這樣的倔強脾氣,連著捱了幾下揍,眼淚鼻涕都出來了,此刻脖上冰涼,更是嚇破了膽,嚷著要找爹去。場面混亂無比,卻聽一聲“阿杏”,溫杏渾身一顫,心臟幾乎停跳。
手背被溫潤的掌心牢牢覆蓋,手中物被緩緩取下,溫杏偏過頭,望見小九的那一刻,瞬時淚眼迷濛。好奇怪啊,明明也沒發生什麼讓人撕心裂肺的傷心事,怎麼就能這麼委屈?她一直以為,只有幼年的病痛能讓她這麼難過,可原來小九也能。她不管不顧地撲進他懷裡,環抱住他的腰際,哭得上氣不接上氣:“我還以為你走了……”
熊孩子們早已作鳥獸散,小九錯愕地撐住她的身體,心想剛不過是出村給她買新出的胭脂去了,除此之外他一時半會兒也不知道該怎樣哄她,她才不會趕自己走。怎麼才離開了一會兒工夫,回來就能抱上晨起後軟綿綿、香噴噴的小姑娘了?
真值!
眼風掃到她身上的單薄,他眉間硃砂微動,解了披風將她整個裹入懷中,確定她不會再受風后,才敢繼續低聲哄慰。溫杏抽抽搭搭的,語無倫次地說著話,一會兒問他去哪兒了,一會兒又問他,她剛才的模樣是不是特別兇悍,讓大家瞧了很不喜歡。其實,哪有什麼大家,她只在意他一個人喜不喜歡。
小九又心疼又好笑,微微彎腰,貼近她耳根,難得輕快地笑了笑:“我很喜歡。”
她卻撇著嘴哭得更兇:“要是擱在以前,我必定是不敢同小喇叭搶的……”
他在她背上輕撫的手一頓。他記得她說過,小梅村十步一梅,故而以此為名,可溫杏是誰啊,襁褓之中便隨著父母貿然闖入這個小小世界,打從一開始就註定了彼此的格格不入。小梅村不需要杏花,村民不需要溫杏,她的人生不甜,甚至是澀的。她不知該信誰,每每受了委屈,若是同小八它們都說不明白,便會跑到村頭的一座舊祠堂裡,對著那尊慈眉善目的神像拜上三拜。她至今也不清楚那是哪位神仙的雕像,只曉得神仙慈悲,這偌大的天地間,想必也只有神仙不會嫌棄她生而為人。
好在,現在多了一個小九。
“那麼,為何方才又敢了?”他心裡堵得慌,連自己都沒注意到此時眼中流淌著的是怎樣的溫柔。
溫杏蜷縮在他懷裡,吸著鼻子搖頭道:“我也想不明白。”
他勾起唇,不動聲色地將那塊被溫杏搶回的冰藍色飾物藏入袖中。溫杏忘了問,他便也沒有說,這東西本就是他故意丟掉的。他把下巴抵在她發頂上,輕輕搖晃著承諾:“因為,以後有我保護你了啊。阿杏,從前可以只信神,今後,你只需信我。”
5
劍子嶺遙遙在望,小九揣著胭脂疾走,白衣幾乎要飛起來。他眼角眉梢盡是藏不住也根本沒想藏的笑意,以致被蘇葉攔下時,那笑容來不及收斂,就那樣掛在臉上,倒讓蘇葉抖了三抖。
“少宗主,宗主交代的事辦得如何了?”蘇葉硬著頭皮開口,想到自己這一路尋主的艱辛,蘇葉心裡苦,蘇葉沒人說。
小九的臉色沉了下來。蘇葉,他忠心耿耿的侍從,一聲“少宗主”,將他刻意按壓在心底許久的秘密驚動。
“你先回去,事情若有進展,我自會親自向父親覆命。”他不自覺地握緊了劍。
“那塊藥爐碎片呢?”蘇葉駭然望向他光禿禿的劍穗,“沒有藥爐碎片,您拿什麼去找皓丹?”
皓丹。終於,還是躲不過去了嗎?小九閉了閉眼。
“少宗主!陛下兵圍藥王宗已有月餘,老宗主整日愁眉不展,身體一日壞過一日,全宗上下就指望您了!”儘管已是在極隱蔽處,蘇葉依然壓低了聲音,“您既有餘力出門採辦,想必皓丹已有下落,那您還在等什麼呢?莫不是皓丹已為他人所有?您是樓家獨子,身負重任,萬不可婦人之仁,壞了大事!”
“大事?”他心思本不在此處,聞言卻笑了起來,“昏君誤國,自比神明,為求不死之身貽害百姓,公然兵圍藥王宗,要父親交出那顆遺失多年且無人知曉是否真有長生之效的皓丹,逾期便血洗全宗,這算哪門子大事?不過私慾罷了!”
大月國以月為尊,他出身時纏綿數日的大雨驟停,清月素光籠罩了整個藥王宗。
老宗主喜不自禁,為他取名“首月”。他怎麼敢告訴溫杏,她的小九,原是光耀藥王宗的第一輪月亮。
禁衛軍闖入藥王宗時,老宗主年事已高,顫巍巍地握著他的手道,十餘年前,藥王宗的確按照古書記載之法煉出了傳說中的不死藥“皓丹”,可尚未來得及探究其實際藥效,皓丹便不翼而飛。樓首月自然不信這世上當真有什麼長生不死藥,可為了保住全宗上下性命,他自請尋找皓丹下落。臨行前,老宗主往他的劍穗上繫了一塊冰藍色的薄片,據說皓丹是有靈性的,而這就是當年煉出它的藥爐的碎片,有了它,便可感應到皓丹所在。
說來也怪,他從幼年起便身體康健,連風寒也不曾患過,心底卻總是隱有悸動,似乎有某種未知的力量時刻將他牽引,又不知要將他領往何處。而等到他握上那塊藥爐碎片,一切彷彿有了答案。他之所以千里迢迢奔赴小梅村,正是順從藥爐碎片帶來的感應,猜想皓丹應該就在那裡。為了能在小梅村常住以便查訪,他在必經之路上使了苦肉計,然後,大雨變得不再令人著惱風也漸漸靜止,他等來了自己命定的姑娘。
再度睜開眼,蘇葉已經消失不見。眼前湧起團團迷霧,樓首月一陣猛咳,舉著劍在空中劃拉,白茫茫的一片裡,慢慢聚起溫杏的影子,她無比雀躍地喊著“小九”朝他奔來。他額上立時滲出層層冷汗,藥爐碎片發出顫音,一如他此刻心跳。他不願騙她,可他確實隱瞞了自己終日閒逛的真實目的——撇開震懾那些欺負她的村民,更多的,是為了儘快找到皓丹。
都說天不絕人願,可他的蒼天,只知同他開傷人慾死的玩笑。藥爐碎片對全村人都毫無反應,除了他的阿杏。皓丹,就在溫杏身上,竟然如此,原來如此。把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小姑娘帶回藥王宗是多麼輕而易舉的事,何況這個小姑娘無父無母,人人只盼對她落井下石,誰會在意她的死活。
他會啊。
說到底,樓首月再聰慧絕倫也不過是個少年,大難臨頭,他也只知將那塊會為阿杏招致厄運的碎片遠遠丟開,只想把心愛的姑娘藏得嚴嚴實實,任誰也不能傷害。可陰差陽錯,小喇叭卻把它撿了回來。他沒有擅動,劍鋒卻不聽使喚地向前一刺,大片寒光激起,他擋著刺目的亮色,卻發現溫杏笑靨如花,即將撞上他的劍……
“哐當”一聲,他慌得丟下劍。
緊接著,這場夢到了盡頭。
樓首月冷汗淋漓地從夢中驚醒,忽聽窗外人聲鼎沸,他一下子就聽出了溫杏的聲音,她帶著哭腔,聲嘶力竭地喊他“小九”,卻不是讓他救她。
她喊的是,小九,快逃。
6
她在這裡,他如何能逃。
樓首月奪門而出,一把扯過溫杏護在身後,周遭一片狼藉,禁衛軍們拉滿銀弓,對準了手無寸鐵的村民們。
“妖女任憑你們處置,只求能放過我們!”村長帶頭哀求,求完禁衛軍,又轉頭去求溫杏,“阿杏,我們不是故意出賣你,可誰讓你帶來這個災星,給我們惹出這樣的禍事來!你就跟他們走吧!你爹孃當年為救小梅村的瘟疫嘔心瀝血,早早地撒手人寰,他們可以這樣犧牲,你為什麼不可以呢?你也算是吃我們的百家飯長大的,現在該是你報恩的時候了!”
“你閉嘴!”樓首月一腳踹翻村長,世上竟真有這般厚顏無恥之人,可他最該痛恨的難道不該是自己嗎?要不是因為他,這些人怎麼會找到溫杏?他怎麼就能天真地以為,只要沒讓蘇葉跟來,他們一時半會兒就不會找到這裡來?四海之內,皆是皇帝耳目,一旦有了頭緒,想要達成目的不過是時間問題。他們進入小梅村後,只需問近日有無外來客,若有,又是同誰走得親近,溫杏又能藏到幾時?
他強迫自己暫時忘卻即將溢位的心疼,集中注意力替溫杏擋住一次又一次的攻擊。當敵方的劍尖沒入他的左臂時,他的第一反應竟是去偏頭安慰溫杏。然而,他看見他的小姑娘在哭,她的唇一張一合,說的好像是“別打了,我跟他們走就是”,他因失血過多而冰冷的手重新握緊了劍——怎麼能讓她走?怎麼能不打?
他要為她戰至最後一刻。
“少宗主,停手吧,想想您臥病在床的父親,藥王宗上百條性命都握在您手裡啊!您不是什麼小九,您叫樓首月,您怎麼能忘記自己的責任?”蘇葉從人群中躥出,語聲淒厲,宛如寒鴉嘶鳴。樓首月咬緊牙,一手將溫杏按入懷中捂住耳朵,一手揮劍出鞘,刀刀飛快,將一撥撥來者逼退。
突破重圍的代價,是他身上添了數道傷口,血染白裳,灼人眼目,看得溫杏喉頭心頭一齊發燙。他們逃進劍子嶺,天地空曠,無處可容身,溫杏回身去看她的小九,他眼角殷紅一身傷痛,如果再不醫治,必定無法活著走出這裡。側頰貼上他的鼻子,她小心地蹭了蹭,別怕啊,小九,她說,換我來保護你啦。
他們躲進半山腰的一間破屋,溫杏敲了火石才發現,這兒原是一座廢棄的廟宇。佛祖拈花而笑,而佛信徒此刻卻遍體鱗傷地倒在佛的腳下。溫杏盯著佛像慈祥的眉目許久,伸手拂去上面蛛網,再轉頭看向已沉沉睡去的樓首月,眼睛發酸,臉上卻笑了。她的佛,在這裡。
她輕輕晃醒樓首月,往他嘴裡塞了一粒藥,哄孩子似的拍拍他的頭:“我爹孃走得早,醫書藥經卻留了不少。我學了這十幾年,總也有些長進。這藥是療傷聖品,自從那天遇見你,我便將它時刻帶在身上,今日可算派上用場了。”他朝她勉力笑了笑,右臂撐起,想要擁住她,卻發覺自己使不出半點兒力氣。
“這藥唯一的壞處,就是你會在接下來的一個時辰裡全身麻痺,”她撫上他的臉,流著淚笑,“現在,你聽我說。我孑然一身,可你不能不顧及你的全家性命,大月國縱使日後會分崩離析,但此時此刻,這天下依舊是皇帝的天下,我們逃不掉的。這本來就是我一個人的事,何苦拖累你。”
樓首月渾身發抖,徒然地張大嘴,可即使額頭青筋暴突,依然發不出任何聲響。
她細心地為他清理傷口,極力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輕快:“皓丹可以和你劍穗上的東西相互感應,對嗎?傻小九,我早就知道了。”
要不然,她怎麼能在大雨中那樣順利地找到他並且救下他?每一次的感應帶來的戰慄,她都知道,每一次他內心的掙扎她都明白,甚至在一開始,他在意識到皓丹所在後,對她曾起過的殺心,她也無比清楚。可是那又怎樣?她更相信,後來他對她無微不至的關心愛護,都是真的。
溫杏慢慢探出手,將那塊藥爐碎片摘下:“這樣,你就不會再感應到我了。”
7
山道狹長,溫杏沒有走出多遠,就被一位老者攔下。她眨去淚,月光下看清了他的輪廓,樓首月與他長得真像啊。她心下了然,卻仍是問了:“你是誰?”
那老者輕嘆一聲:“樓家家主,他的……父親。”
溫杏深吸一口氣:“你看上去身體很好,可你的手下說你臥病在床,所以,你騙了小九?”
老宗主快步行至她跟前:“溫姑娘,我是適才抄了近路,窮追不捨才找到你們的。趁現在追兵未至,算我這個做長輩的求你……”
溫杏的眼神柔和下來:“您是來幫我們逃跑的嗎?”
老宗主默了默,竟跪了下去;“求你,交出皓丹。”
溫杏的身子晃了晃:“師伯,你既是藥王宗的人,我便喚你一聲師伯,你應該比誰都清楚,皓丹是怎麼來的,又有什麼用處!它並非不死藥,而是保命藥,我先天不足,若不是有它護持,根本活不到今時今日,如果沒有它,我會死的!師伯若想用它換取高官厚祿,這算盤卻是打錯了!爹孃曾留下遺言,皓丹自被我服用後,便與我融為一體,除非我自己願意,否則誰也無法得到它!”
老宗主咚咚磕頭,臉上已是老淚縱橫:“如若我的這條殘命可以換你周全,做師伯的死千次萬次都可以,可是溫姑娘,你以為每次與你產生感應的是什麼藥爐碎片嗎?十餘年前的藥爐,怎會留到今日?那只是我隨意找來騙月兒的物什,真正相互吸引的,是皓丹啊!”
溫杏聞言一震,險些站立不穩。
原來,溫杏的父母正是老宗主的師弟師妹,二人醫術卓絕,尤其溫父,更是百年一遇的神醫妙手,因此,他雖非樓氏子弟,宗主之位原本也會由他來繼承。可溫父溫母嚮往閒雲野鶴的生活,只想隱居避世。樓氏歷代子息單薄,樓首月自出生起便體弱多病,隱有早夭之兆,溫杏父母殫精竭慮,才研製出兩份皓丹,臨走前喂樓首月吃了一份。當時溫母已有身孕,因為耗損過重而早產,所以溫杏的身體比之當日的樓首月尤有不及,幸好有剩下的一份皓丹,這才堪堪護住她的性命。
“如果從你這兒取不到皓丹,陛下遲早會查到月兒身上,樓家九代單傳,他不能出事啊!”老宗主仍在苦苦哀求,溫杏抬頭望著天上月,想的卻都是她的心上人。她背過身,肩膀輕輕聳動:“起來吧,師伯。其實,即便你不來找我,我也本就打算回小梅村。”
村民們待她不好,她斷學不會對他們以德報怨。可老宗主說得對,小九不能出事。她必須回去,她心甘情願。
樓首月是在小梅村村頭的那間舊祠堂裡找到溫杏的,他來不及深想為什麼沒有那塊碎片,他依然能在這麼短的時間裡找到她,便匆匆上前,攬過她細看。還好,看上去,她除了面無血色之外,好像並沒有受什麼皮外傷。
溫杏靠在他的肩頭,微微地喘:“小九,這便是我同你說過的老神仙。”
樓首月瞄了那神像一眼,笑著刮她的鼻子:“這是月老。阿杏,你我果然有緣。”他心情大好,破天荒地說了好些話,無一不是憧憬他們本該擁有的美好未來。
溫杏撐著眼皮聽著,語聲漸小:“我困了,先睡會兒。小九,等我醒了,就帶我回家吧,我們的小兔子我還沒喂呢。”
他忙說好,拍著她的背哄她入睡,直到她的呼吸漸漸湮滅。
他忍了許久的淚終於滴落下來。
藥王宗的少宗主,怎會瞧不出什麼是油盡燈枯。
阿杏,我們回不了家了。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