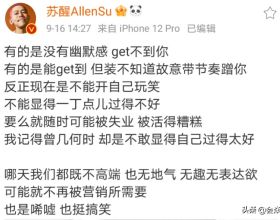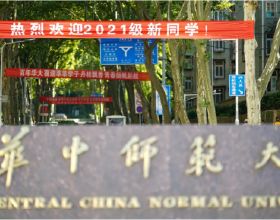一,血染河西
我所在的紅四方面軍經過三次爬雪山,三次過草地,吃盡了張國燾錯誤路線帶來的苦頭。
一九三六年九月下旬,我們到達了甘肅南部的會寧境內,即將與中央紅軍會師了,大家那股高興勁兒就沒法說了。
但是,張國燾不顧抗日大局,假借中央的名義,令紅五軍、九軍、三十軍二萬餘人組成紅西路軍,於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從黃河上游甘肅靖遠縣西南15公里的虎豹口強渡黃河,進入河西走廊。我們頂著寒風吹起的漫天飛沙,踏上了艱苦悲壯的西征之路。
剛開到靖遠虎豹口的黃河岸邊,一看,黃河水很深,很急,河底下盡是泥沙,徒步涉水根本不能透過。
沒有木船,牛皮筏子也搞不到,只有砍樹扎木排,這樣搞了三天三夜,連眼都沒合一下。
河對岸有馬匪的兩個碉堡守著渡口,兩岸地勢陡峭,黃河波濤洶湧,很難渡過,其他地方又不能過,只有在這個渡口強渡,但白天強渡是不行的,只有晚上才能強渡。
第一天晚上十二點,我軍開始強渡黃河。由於馬匪地勢居高臨下,加上碉堡堅固,裝備好,火力很強,打了三、四個鐘頭,都沒把這兩個碉堡拿下來。快天亮時,我軍只好暫時撤下來。
部隊傷亡很大,光我們連一百多人,這次戰鬥就犧牲、掛彩三、四十人,只剩下四、五十人,打得排不成排,班不成班。
第二天晚上,總部又調來善於夜戰的我軍“夜老虎團”——紅三十軍八十八師二六五團。他們一過去,就把碉堡給摸了,其實碉堡的敵人不多,只一個排。
一過黃河,我軍要後方沒後方,要給養沒給養,陷入四面受敵的局面。剛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徵的紅四方面軍,還沒得到休整,沒得到補充,就匆忙開進河西進行西征。
戰士們要棉衣沒棉衣,要子彈沒子彈,要槍沒槍,連大刀、矛子也在雪山草地搞得差不多了。
當時我是班長,身上也只有一排(五粒)子彈,其他戰士有的只有一、二粒子彈,有的戰士根本就沒有子彈,打一粒少一粒,子彈甚至比性命還珍貴。
主力部隊一個連是有兩挺輕機槍,但也只有百把發子彈,動都不敢動一下,一旦打光了,關鍵時候怎麼辦?
部隊戰鬥力明顯下降,但面對數倍於我的馬匪,我們的戰士還是精神抖擻,同敵人進行了殊死的戰鬥。
經過反覆的進攻,這樣左衝右突的戰鬥,部隊傷亡幾乎過半了。
我們由於沒有後方給養,部隊是傷亡一個,就少一個。沒有醫院,部隊還要打仗呀!傷了,沒有藥,也只能用衣服一紮,把傷口包住堵住血。戰士都說:寧死也不能受傷。
馬匪非常兇殘,只要抓到我傷員,不是砍頭就是活埋。我們沒有補充的,沒吃的,沒子彈,傷病員也就沒法管。人,一天天的減少,看到這種情況,戰士們都感到寒心,士氣也就一天天低落。
部隊打的又是拉鋸戰,在高臺,臨澤的沙河堡,永昌,山丹,倪家營子,梨園口一帶攻過來,打過去。
隊伍這麼拖來拖去,沒有子彈,槍還不如一根燒火棍,槍也就撂完了,根本就沒戰鬥力了。
特別是倪家營子一仗,馬匪出動幾個旅一萬多人的騎兵,都是白馬隊,黑馬隊,黃馬隊,花馬隊,鋪天蓋地的衝壓過來,我們的隊伍被這麼一衝就亂了,收不攏來了。
不管傷兵能不能走,願不願走,不走就完蛋。紅西路軍到河西幾個月,最後終於全部失敗了。我們進行了歷時半年之久的浴血苦戰,在經過了大小百餘仗之多的慘烈拼殺後,終因肩負戰略任務複雜多變、敵眾我寡、天寒地凍、地形不利、彈盡糧絕而兵敗河西、血染祁連山。
剩下的,一部分突圍到了新疆,一部分進了祁連山的深山老林,戈壁灘,一部分老弱病傷員被俘了,我也不幸被俘了。
河西征戰失利後,據說我們西路軍將士共有12000多人被俘,除了在武威、張掖、酒泉等地關押以外,押往青海西寧就有7000多人。
二,逃出虎口
被俘後,我想,就只有死這一條路。我們總共有四百多人關在張掖的一座監獄裡。剛開始還過堂審問一下。
一天,我被帶到審訊室。一個軍官模樣的人問到:
“你是不是共產黨員?你們裡面當官的是誰?說出來有賞。”
我怎麼能殘害戰友?!
我答: “過雪山、草地長征後,連長、營長、團長都是戰士,沒有當官的。”
他見問不出什麼東西,就打我一頓,又把我送回牢房。
在監獄裡,我們吃不飽,整天喝的是菜湯,油無油,鹽無鹽,淡不拉嘰的,簡直就是白開水,只是水面上漂了幾片菜葉,像餵豬似的。偶爾菜湯哩有幾點豬皮子,我還開玩笑地說:“嗬,還有豬皮吃,夠一輩子了。過草地還只有草根嚼呢!”
就這樣,我們在監獄裡關了三個多月,後來敵人把我們編了一個集中營,開到了武威。我們住在這個鎮的一個廟裡,這個廟是個四合院,周圍都是他們的人守著,真是十步一崗,五步一哨。
白天我們要被押著,走一個多小時,到一個叫六山裡的地方去挖山,據說這是修通往新疆的一條馬路,白天挖山乾重活,晚上就睡在廟裡的地上。
挖山是個重體力活,早上天不亮就出去幹活,晚上天黑了才能回到廟裡睡覺。幹活時,你稍微伸起腰喘口氣,敵人就用鞭子抽,還不許說話。
他們怕我們拿起鋤頭跟他們幹,周圍山上都是敵人荷槍實彈的哨兵,真是插翅難逃呀。
我們每天干那麼重的活,生活比監獄稍強一點,也不過都是摻了很多麥麩子蒸的黑饅頭,再搞點什麼青菜湯一灌,只能吃個半飽,還不能講“這黑傢伙不好吃”,說了就捱打,而且他們自己不打,強迫我們自己人打。假如其他人都不打,就大家一起捱打。這叫什麼日子喲,我決定逃跑,反正是死,在戰場上死,也比在這裡累死強得多。
我們天晴就挖山,下雨時就在廟裡。這樣,我就留心周圍的環境,挖山時,周圍都是哨兵,住在廟裡也有哨兵,要跑只有在晚上了。
我經常晚上不睡覺,細心觀察敵人哨兵的動靜,觀察了好幾天,基本上摸清了敵哨兵的規律。
一個多月後的一天晚上,天很黑,我想這是個機會。凌晨兩點多鐘的樣子,我起身一看,敵哨兵抱著槍正在打瞌睡,就輕手輕腳地溜到了門口。
當時我想,假如敵人發現,就說是解便,沒發現就溜。當我跨過哨兵時,敵哨兵還在打呼嚕哩。
我出了門,直撲門前的河邊。白天,地形我都看清了,岸上有敵哨兵,不能走,只有從河裡走。
岸很陡,不在河裡走不行。當時是寒冬天氣,河水很涼,冰冷的河水象鋼針扎骨。我就從河裡摸著,磕磕絆絆走了一會,過了河爬上岸時,不小心碰動一塊石頭, “卟咚”一聲,石頭掉進河裡。敵哨兵發現了我,就大叫“抓住他!”還亂打一通槍。
我一看情況不對,撒腿就往大山裡飛跑。不知跑了多長時間,一直跑到天亮,我才跑到深山裡。我實在跑不動了,累倒在大樹下,又餓得不行了,就昏昏沉沉靠著大樹睡著了。
三,找親人
這一覺睡得真香,一直睡到十點多鐘了,一醒來,那肚子個餓呀,攪得人整個腸子真受不了,站起來眼裡金星直冒,又不敢下去,山下到處都還有馬家軍的匪兵啦。
一直到下午四、五點鐘,我才慢慢下山,等太陽就要落山,夜色快暗時,找到一個小村子,跑進一個老頭子家裡去了,我說:
“大爺呀,討點吃的吧!”
那大爺看了我一眼,冷冷地說: “我哪有吃的? ”
我看那大爺慈眉善眼的,斷定是個好人,就說: “我是紅軍呀,沒得吃的了。”
大爺還是不放心: “沒有噢,現在也沒到吃飯的時候呀。”
“那,大爺,有沒有爛衣服讓我換一換吧。”
我身上的爛衣服還是監獄裡的號衣,下山後會引起敵人的懷疑。
大爺看見我懇切的樣子,拿出一件爛棉褲給我換上。他看我餓得實在不行了,又給我吃了兩碗小米飯。
他看著我狼吞虎嚥地吃完飯,又說:
“給你一些小米你怎麼吃呢?這樣吧,我給你一個藥罐子吧。”
說著他給我一個煨藥的沙罐, “這個可以,餓了可以煮著吃。”
當時我真不知趣: “我沒火。”
“沒有火?我給你呀。”
他給了我半盒火柴。當時我不知怎麼感謝他才好,他卻進了屋把門關上了,其實我知道他怕被馬匪發現受牽連。
我離開老大爺家時,竟不知該到哪裡去,找部隊?部隊已失敗了,回四川?家裡也沒有人了,回去也還是討飯,受地主壓迫,我覺得真是舉目無親了。
過雪山草地時,我沒有悲傷;河西失敗,我沒悲傷;即使在敵人監獄裡,我也沒有悲傷。相反,在我能自由行動時,反而悲傷了。舉目無親,沒有親人的滋味,脫離部隊的滋味,比失去親孃還難受。
忽然,我想到,我們紅四方面軍五個軍,過河西時,只過來三個軍,還有兩個軍在,紅一、二方面軍也在,只要能活一天,就討一天飯,就找一天部隊。主意一定,心裡就鬆快了,人也精神了,就上路了。
白天,馬匪部隊經常亂竄,地主保長又到處橫行,我不敢走大路,就專揀大山走,晚上就下山要飯,就趕路。每天要的飯和米,就找點柴火一燒,用藥罐煮著吃。
甘肅的黃土高原,到處都是光禿禿的山嶺,村落稀少,很少見到人,討飯漸漸困難了。山上滿目荒涼,連草根都找不到,簡直比過草地還艱難。
出了草地,又在河西打了幾個月的仗,在監獄裡折磨四個多月,現在又這樣折騰,腿都挪不動了。但這時,我已從當地老鄉那裡打聽到西安事變的事了。
聽到這個訊息,我確實很高興,總算知道我們部隊的確實的訊息了,所以更是信心百倍。
雖然藥罐幾天沒東西煮了,我還是紮好爛棉襖,柱著一根棍子,把穀草紮成一排,披在身上,累了穀草還可鋪在地上睡一睡,實在冷,就找點柴,燒一燒。就這樣走一走,歇一歇,我一天也要走幾十裡,我心裡想,只要能找到紅軍大部隊,再大的苦,我也吃得了。
我就這樣要了三、四個月的飯,慢慢走到了黃河邊。我見敵人把守著渡口,盤查很嚴,不敢過。
怎麼辦?左思右想,只有上山再想辦法。一天,碰到一個老鄉,我便問道:
“老鄉,你知不知道哪裡能過河?'”
老鄉說: “沒船,不能過,我們都是在渡口上過的。”他指了指敵人把守的渡口。
不能過黃河,就到不了西安,我在渡口山邊的周圍的村莊裡要了十幾天飯。一天又碰到那個老鄉,他問:
“你怎麼又回來了? ”
“我過不去呀。”
後來,旁邊一個老頭子見我可憐,就把我帶到他看瓜的窩棚裡,對我說:
“你白天去要飯,晚上就到我的窩棚來睡。”
他問我到底是幹什麼的,我說我是四川人,遭了災,出來要口飯吃。他也信了。
我這樣每天出去要飯,探聽訊息,晚上和這個好老頭做伴。
搞了幾天,老頭子可能看出我不象一個要飯的,我見他十分善良,就把我的情況全部告訴了他,我說我要到西安去找部隊。他非常同情我,拍著我的肩膀說:
“我幫你想辦法。”
等了幾天,他把我帶到河邊,看見一個駕船的就喊: “夥計,一個要飯的遭了災,你幫幫忙帶過去吧。”
那駕船的看看我,面有難色。
老頭子拍著他的肩膀,塞給他幾個錢: “幫幫忙。”
駕船的看看手裡的錢,點了點頭。
當時我感動得眼淚在眼框裡直轉,這些錢,是老頭子好不容易積攢起來的啊!
四,西安尋找黨組織
一過黃河,我就不害怕了,在河西那邊是甘肅馬匪的地方,話也聽不懂。到了陝西這邊,話好懂的多了,可以大搖大擺地走大路了。餓了就討飯吃,這樣又討了一百多里才到西安。
雖然到了西安,但還是國民黨的地盤啊,又不敢亂問,晚上我就在西安火車站票房或候車室裡睡。那裡沒人管。西安的晚上真冷,我就捂著爛衣服靠著牆腳睡。
西安這麼老大,到那裡去找?白天就邊討飯,邊慢慢地打聽。
一天,我問一個火車站的扳道工:
“你知不知道八路軍辦事處呀? ”
他說:“只有一個十八集團軍辦事處。”
“就是紅軍。”我說。
他“哦”了一聲: “你就在附近找,辦事處的人也經常來買票。”
這樣,我在西安討了十幾天的飯,才找到一個象機關樣子的大門,門口站著一個穿著老百姓衣服的人,我問:
“老鄉,原來的紅軍辦事處在什麼地方?”
他把我渾身上下打量,說: “你一個要飯的,問這些幹什麼?',
我說: “你管我要飯不要飯,我問一問不行?你知道就告訴我。”
他想一想: “哦,你怎麼要飯要到這裡來了?”
我看他話裡有話,就說: “我哪裡是要飯的喲,我是四川逃荒來的。”
他說: “那我不管。”
我從他的話裡聽出了一點名堂,就趕緊說: “同志,我是河西過來找組織的。”
他一聽: “啊,你等等,你是哪個部隊? ”我就把部隊番號告訴了他。
他把我叫到傳達室裡,就進去了。不一會兒,他拿來兩套衣服說:
“先理理髮,洗洗澡。”
我說: “我什麼錢也沒有哇!到哪裡去洗澡? ”
他笑了笑說: “我領你去,不要錢。”
洗完澡,我穿上一套單衣,丟掉穿了半年鄉的爛棉衣,還有那跟我一起到西安的藥罐和討飯棍,真正象個人了。
這樣,經過半年多時間,幾千裡行程,我終於討飯找到了部隊,找到了親人,找到了家。
王勇同志,四川省渠縣人,1919年生,1933年10月參加紅軍。1935年隨紅四方面軍長征。1938年6月入黨。曾任戰士、排長、連長、管理科長。1950年在漢口辦事處、中南二公司、華鋼公司、武銅大型廠等先後任材料員、副科長、支部書記、廠監委副書記等職。